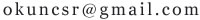[三国/司马师夏侯徽]结发(短篇/已完结)
写在文前的话:这个本来是复习期间的一个脑洞,因为偶然百度到夏侯徽妹子的凄惨经历,就想为她写一个故事。
文章简介:文中的女主角名叫夏侯徽,字媛容,是夏侯玄的妹妹,大将军曹真的外甥女。大约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嫁给了司马师,也就是司马懿的长子,司马昭的哥哥。两人成婚七年左右,共生有五个女儿。而且夏侯妹子非常聪明,总能帮助司马师出谋划策。
但是,她毕竟是夏侯氏的女儿,老曹家的外甥女,因为司马家和老曹家的关系……总之司马师对出身曹魏的夏侯徽非常忌惮,最终在她24岁那年,将其毒死。
另附史书原文:景怀夏侯皇后,讳徽,字媛容,沛国谯人也。父尚,魏征南大将军。母曹氏,魏德阳乡主。后无男,生五女。后雅有识度,帝每有所为,必豫筹画。魏明帝世,宣帝居上将之重,诸子并有雄才大略。后知帝非魏之纯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青龙二年,遂以鸩崩,时年二十四,葬峻平陵。
本文为根据史书展开的脑洞。
【正文】
“夫人,张先生来了,才请公子出去呢。”
“这么晚还来啊。”
“夫人乐夫人的,不必管他们。”汉时女子都喜把曲裾袍裁成鱼尾样式,走起路来袅袅娉婷,颇有韵致。一个侍女晃着鼗鼓,扑嗒扑嗒发响,往后退去,逗弄着眼前的稚女跟过来。那姑娘方一岁出头,正是学走路的年纪,看过去便是一个晃悠悠的肉团子,逗得满屋人一片笑语:“五姑娘实在可爱,连学爬学走都利索些。”
她也便笑了一下。只是那笑也是浮在茶上的叶子,沉不到底下去。侍女当她是累了。连年的生育早已磨折了她的身体,近来下红之症越显,她也越来越懒怠动弹,早不是从前还能出门跑马的姑娘。自屏退了旁人,上来傍依着她,说话也是极亲近的口气:“夫人早时安睡吧,别等公子了。”
她否认了。“我不累。”她仰头看过去。梨木榻,竹布胡床,玉屏,箱笥,铜镜台,朱漆折枝描金的妆奁盒……她忽然想到了大女儿。侍女一听她问起,满面春风地报喜:“蘅姑娘自然是聪慧的。正跟着女师学《国风》,听傅姆说,比二公子家的男孩还伶俐。”
她应了一声,一张脸低埋在烛光里,霜冻似的没有表情:“女儿没有用。”侍女的笑冻在嘴唇上,她抬头迎上去:“葛覃,我要生个儿子。我一定要生个儿子。”侍女一顿,僵着的笑容很快蔓延成宽慰:“夫人才二十四,哪里担心没有儿子。将养好身体,才是要紧。”
她仿佛失了凭依,向后靠去,只木肤肤盯着楼板。铜鎏金薰里的香雾飘成一个篆字,虚虚笼笼地散化在上头。她道:“已经是第五个女儿了。有时我真的想,我是不是真的命中无子。子元虽然不说,可我知道他心里总是不圆满的。阿母也是,一心想要长孙……”
葛覃听的触动了几分软处,鼻头发酸:“会有的。”她把手合在她的手上,紧紧握住了,好似能借此传达些坚韧过去:“会有的,一定会有的。”
“将军刚随大将军自渭水兵退回朝,某深夜拜门,实在打搅。”
眼前的都尉张蠡乃是父亲提拔的后生,自家心腹门客,如今有事,却越过父亲夤夜而来,他心里不得不先存个疑影。
“先生客气。有事相谈,只管直言相告。”
张蠡自在宾位坐定,深深一揖:“将军久不在朝中,可知邵陵侯近日频频出入宫闱,似与陛下有要事相商?”
他眼色微变,不想他一来便说起此事。只是对着亲信之人,他也无需藏掩,冷哼一声便托盘叙来:“昔日他父亲在时,因我父亲与其同为文帝托孤,又屡掌兵权,委实深忌我父子兄弟。如今他儿子袭爵,我父子于前抵御西蜀,他在后方又来掣肘。只是量尔斗筲之辈,处节任事不过如此,何足为惧。”
门客边为自己斟酒边觑着他的神色:“将军所说极是,只万不可轻敌。”
他挑眉:“如何?”他自幼才勇过人,言语间便不自觉会生出许多轻蔑。张蠡道:“将军,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方无患。今蜀丞相诸葛亮已死,我辈少一心腹之患,将军也需细思朝中之事了。邵陵侯曹爽自幼便与陛下交好,且曹氏夏侯氏一族随太祖创业,乃世胄之后。数年来举荐后才,提拔亲贵,如今满朝皆为其世家子弟。而今朝中暂且平稳,是因陛下明察事理。只是我观陛下……”他将手笼在嘴边,声音低下去,“陛下现今耽于享乐,昼夜沉溺于后庭声色之中,万一陛下哪日……将军,需早做良图。”
他早知其意了。只是父亲差他来与自己说,又是为甚?“先生之见若何?”
张蠡揸开案上的葡萄枝子,慢条斯理地拧下一颗,循循道来:“依愚之见,将军何不与吴氏结交?振威将军吴质乃尊父旧友,先帝近臣,又辅弼陛下治理朝事多年。其虽身死,子孙与故吏尚存,不可小视。”
他耐性回想朝中旧事。“从前吴侍中与我父亲共辅先帝,又曾向陛下力荐父亲。只他仙去后,我家与吴氏情分也渐渐淡了。我欲结交,只恨没有门路。”张蠡唇角慢慢上抬,几颗葡萄在嘴里掀腾着,带着灰白胡子上下移动:“而今有个现成的门路,只恐将军不允。”
他愈是惊疑:“还请先生指教。”张蠡缓声道:“吴侍中有一女,年方及笄,若是将军娶之……”
“先生,”他语气沉寒,果决打断,“我已娶夏侯氏女多年。况我司马师堂堂七尺男儿,莫非靠妇人裙带保身?勿复再言。”张蠡早料如此,他受托于其父,只是耐下性子劝告:“将军,夫丈夫者,成事不拘小节。难道将军以为有比姻亲更牢靠的关系?况将军与夏侯族人……”他回绝:“我与夏侯氏曹氏再如何,与我妻女不相干。”他陪笑道:“将军与夫人结发情深,某感佩之至。只是血缘之情,又怎可忽视?夫人乃夏侯氏女儿,夏侯玄之妹,更是曹氏甥女,又向来聪慧识度。她既为您枕边人,对将军之心岂会不知?若是将来……将军,某斗胆言之,便是不为今朝,也需防患未然。”
他沉默了。张蠡见爵中酒水已尽,持壶又为自己倒了一杯,水咕溜溜地在面上打起几个泡,前仆后继地爆裂开。他终于开了口:“……且容我……细思。”
他一笑道:“某知将军心中已有分寸。今再多言一劝。将军与夏侯一族情分虽不比从前,但面子尚在,还未到揭破之时。将军断不可使夫人下堂而去。只不过……便是不遣其归家,也有别的法子。”
“你……”他素来机敏,一下便反应过来,霎时额头青筋暴起,拍案起身:“你这是何意!”
张蠡见他如此,知他是动了真怒,只他是他父亲器重的门客,又在朝中浸淫多年,自有一派镇定如仪。只缓缓悠悠将酒一口饮尽了,方道:“将军,某受托于司马大将军,又冒疏不间亲之讳,前来劝告于您。夫人出自魏族,若不早除,必后患无穷。昔日平原君赵胜为留贤士而杀美妾,楚庄王为成霸业而赦唐狡,此皆舍妇人而成大业者。将军素有吞天吐地之心,怎可因一妇人而留恋不前?”他沉默着听完,张蠡趁势道,“何况将军胸怀远志,将来将军之子必要承袭您之大业,若此子出自魏氏甥女……”他拱手道,“将军,某言尽于此。”
葛覃去添一斛香的功夫,她已经躺在地上打起了盹。她恐她受寒,要去叫醒她到榻上睡,忽见一个身影近前,葛覃愣了一愣,赶忙致礼:“公子。”
他不曾言语,只打了个手势,葛覃识趣,快步退下了。他看出她装睡,横抱起她往前放于榻上坐下:“生了蘅儿就恶风,还不知道保重自己,又着凉了该怪谁?”她咬住嘴唇不让自己笑出来,只闷在他怀里不说话。他待要起身,她忽而伸出手臂攀住他脖颈,附耳缓言道:“子元……我们生个儿子吧。”他身子一僵,似是意外她突然提起这事,片刻方道:“我们这么年轻,当然会有儿子。”
她撇一撇嘴:“这话你从蘅儿生下就开始讲,已经七年了。”两眼一睇,瞧见他眉眼倦怠,竟是少见的疲惫,惊异道:“那张先生给你说了什么烦心事?累的这样?”他道:“无妨,不外乎朝政。”她隐隐觉得不止如此,却也不知从何问起。因岔开话头:“本来拿了些麦饼来等你的。你既累了,叫她们来收了吧。”便要去叫人。他一把拦住了,浮上温吞的笑意:“夫人的心意,怎么好浪费。”她嗔笑一声,下榻与他整碗递箸。他吃着觉得不错,将东西也递到她跟前,她下意识别过脸去:“你用吧,我胃口不好。”
他听了便放下箸筷,关切道:“怎么又胃口不好?”她不应声,用筷子拨着碗里的饼饵,外皮的黄白沫子窸窸窣窣地掉下来。“你不在时,家里常做这些样式的糕点,我也吃腻了。又不是羌煮貊炙之类,许久不吃,倒新鲜一些。”她自嫁他以来,七年生五女,为保胎儿康健,已是许久不吃这些辛热血肉之物。如今随口一提,倒也有些怃然。他沉默一刻,忽的起身:“我去给你做。”她大惊:“你说什么?别胡闹了。”眼见他往外而去,她两步上前扯住他袍袖:“哪有大晚上吃那些的。我不过随口一说。”他道:“便是偶然一次,又有何碍?”她恐他遭累,只推辞:“别费周章了。晚上吃那些,也是腻味。”他回过身,笑着审视她一眼,轻点了点她的鼻头:“口是心非。”
她见他看穿,脸一红,有些赧然地低下头去。倒也不推却了:“那,快去快回。”他了然一笑,抽袖离开。她眼看他移开屋门,外头寒丝丝的,是一口幽深的井。风剔开枝叶子,簌簌地裹到身上来,像井里的冷水。
他去了约有饭熟功夫,回来时还带了食盒,里头烟香缭绕的躺着几串肉食,泛黄熟色。隔几寸便是一指来长的裂口,隐约透着肉粉,葱白洒上去,油汪汪的。她早已迫不及待,拿起一串,他见了轻握住她的手腕:“小心烫。”
她点头,略尝一口,“啊”了一声:“怎么这样辣?”他没忍住笑了出来:“加了蜀椒。”她素不吃辣,作势要动气,他忙换了不辣的递到她手上:“只一串加了椒,你就中彩了。”她回嗔作喜,强压着嘴角不叫他发现,嘴上只道:“朝中上将还下厨做庖人,若要别人知道了可要笑你呢。”他道:“我讨我夫人开心,随他们笑去。”他二人近年聚少离多,他刚回来又如此体贴,她也渐停下动作,心里有说不出的软触。抬眼忽见他接袖处沾了油污,忙执了绢帕要去替他拭:“瞧瞧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他蓦然握住她持绢帕的手,缓缓移到心口的位置,两眼定定瞧着她。她出乎意料,怔忪地没有反应。烛火左右跳晃,在墙上投下一个小人舞动的影子,上跳下摆,恣意张扬。她依稀看见他眼底水溶溶的,握着她的手温声道:“媛容,对不起。”
她嗔怪:“好好的,道什么歉?”脑中细想近来景况,以为他要为这些年的少伴致歉,因笑道:“你总是离家也是迫不得已,怪不得你的。”要把手抽回来,无奈他不放,她也只好作罢,寻别的话头:“你既为这道歉,今年可在家里过年么?”
他终放开了她,轻轻点头。她展颜:“那便好。我闻西蜀诸葛亮已死,想来蜀汉短时内也不会再犯我疆界。你以后好好补偿着我和孩子们就是。对了,近来,二姑娘也渐渐大了,总嚷着要出去玩,今年年下,你带她们姊妹几个到她舅舅家玩去。”她说起孩子们,眉眼间更溢满柔和,晚香玉的白骨嘟旁笼了一圈光晕。他喜欢听她说女儿们。母亲谈起孩子,那实在有说不完的话,又见他爱听,便尽拣幼童有趣的事说来,两人一递一声,她说什么他应什么,短时一片笑谈生风。
末了,她静默下来。盒中没吃完的肉也凉了。她叹一声:“我晓得你与哥哥……不过,都看孩子的面上吧。”他仰面躺着,不知道在想什么,只淡淡道:“你放心。”她不知何应,张了张口,终也没有刨根究底。于是回身去铺床:“早该睡了,怨你闹的这么晚。”
她来到床榻边,揭开被褥,上下掀覆着。他撑着脑袋侧卧看她。多角扁足青铜灯上涎着火舌子,她身子活动在这明灭不定的光前,影子映在地上,画影模糊,像池水里的倒像。裙尾如一匹织锦软缎子,恍惚直接铺到了他跟前。
她感到他从背后抱住了她,哑声道:“媛容。”她不待说什么,已是一阵重压的倾颓,她的身影没在皱褶成川的褥被之间。他覆上来,呈保护的姿势,轻车熟路地摸到直裾袍右边解她的系带。她一时不知如何,只下意识将手放在他两肩。交领半掩半敞,他的束发黑魆魆的,正在她眼皮底下。
她逼迫自己去抗拒:“子元。”
他不理睬。她细喘着,抬高声调:“子元……不要。医者说了……这一月不能行房。”
他停下动作。她将头别过去,没有看他。
他平复着呼吸,有些粗声:“为何?”
她缩了缩肩膀:“是血漏证。”他一愣:“什么时候开始的?”她偏着头,好像那边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生了兰泽之后。本来是好了,如今又发了,已一月有余了。”
她无从得知他的表情,只听得到彼此的呼吸,绵长静谧,延伸在一个令两人都尴尬的境地。
他终究没有让她发现他的恼怒。只是在她身边侧卧下来,以双臂圈着她,两手合卧住她的,叹息一声:“媛容,苦了你了。”她缩在他怀里,鼻子一涩。女人怀孕生子是天经地义,她从来只是认命罢了:“……我没事。”她忽然想起从前在母家时,常听姊妹母亲们说邻里家长的事。她听说过,有丈夫纵容妾媵欺侮正妻,有夫妻面和心不和,一年到头竟不曾同床几次。她轻轻一笑。她的丈夫待她这样好,她何其幸,何其幸。
她的丈夫还在说话。他的脸颊贴着她的,毛毵毵的胡子有些扎脸。她极少听见他这样低微懊丧的语气:“媛容,我没用,叫你受苦了。我……对不住你。你嫁给我这些年,我没让你过上好日子。近年,西蜀履犯边境,总也是聚少离多。母亲她……又是那样的性子。你虽不说,我晓得你有时是受委屈了。我对不住你……徽儿,我对不住你……你便是怨我,我也认了。”
她两眼涌上热意。罗帐四角垂着玄红香袋,吊下麦黄的穗子,一摆一摆,在顶上呆瞪瞪地望着她。她嫁了他七年……这七年里,婆母姑舅虽未太过苛待于她,可数年琐碎,岂能一夕道尽。无非是吐出来无人理会,咽下去如鱼骨刺喉。她瑟缩着,想把眼泪忍住,她不知道自己今天是怎么了。数年来,她以为自己早已习惯。可是今日她才发现,在自己这一生所依面前,她竟然这样软弱委屈:“又说傻话了,我怨你什么。”
他没搭腔。她用手背抹了抹脸:“好了。叫人来把剩下的收了吧,这么摆在房里,也不是样子。”于是从他怀里挣开,叫声:“葛覃。”他起身,走到她跟前:“慢着。”他为她斟了一杯酒水:“这是从渭水几郡带回的枣酒。我听下人说你夜里总睡不好,这酒有安神助眠之效,不妨试试。”她失笑,接过酒盅:“可真是傻子。我睡不安稳不过是心里有事,也罢,难为你有这心了。”刚要仰脖喝尽,他忽而紧抓住她的手,她诧异望过去,见他在一片幽暗中静静瞧着自己。须臾,终于慢慢放开:“慢些,仔细呛了。”她一笑,将一盅喝光,叫下人进来收拾停当。方走至榻前,偎依在他肩头:“睡吧,明日一起去看孩子。”
她是在隔日薨逝的。娘家人接到讣闻赶到时,人已入殓了。而整备六礼,迎娶新妇,不过是数月后的事。请期已完,眼看着便到了年前亲迎之日。府中备下猪羊牲醴,红缎聘资,竟毫无旧人离世之哀。
这是他自己的决定。他注定对不起她了。可她嫁了他,便是司马家的人,她也应该愿意为他牺牲吧。
他是欠了她了,可他也是迫不得已。在朝堂相争之下,便是男儿,也会成为一条微不足道的命。
他坐下,瞧着自己的衣袖。连婚袍都是与七年前一样的玄色直裾。他眼底一阵滚烫,又硬生生逼了回去。
屋中极是辉丽锦绣,红罗帐顶各挂着香囊福袋,四角齐全,用金线绣满如意花样,瓜瓞绵绵。半圆相结的同心苣缠绕在缎面上,层层排叠,难言的喜庆照人。那上头的意思也是好的:“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
外边传来闲话声。“好你们几个忘八端的,新夫人眼看要过门,大家都在忙活,你们还在这躲懒吃饼。”随即一阵嬉笑,唯有一人的声音训练有素,舔着脸笑道:“还求您宽宏大量些。吉时将到,早该忙活的差不多了。倒是您,做婚仪的管事,倘有半点不好,小心新夫人不放你回家过年。”话刚说完,外头便是一片哄笑声。那管事无奈道:“我处事能有不周?你还是担心着你自个儿,节下事多,你总这样晚回家,仔细你媳妇查问。”几个人外头你来我往,又是一片笑语闲谈。
乐师已至,零零散散地吹打着喜乐。他恍惚想到军营的画角声,呜呜呜地一声一声,越过山川营楼,交叠了十年百年的时光。要进军了,要渡水了,要休整开火仓了。他犹记得撤兵的时候,夜晚他们安营扎寨,军士们围拢在一起生炊,火光把他们每个人的脸都映的亮扑扑的。他们往火里丢着柴,乞乞缩缩地议论回家的盼头。归家之喜是地上团团转的黑蚁,急于找一个出口倾吐——将帅自然是不能在人前显露思家心绪的,他也只敢在单独一人时悄悄想她,想她在家做什么。她在织素,她在裁衣,她在教女儿写字……可无论在做什么,她总会在他一入家门时便提着裙摆小跑迎上来,望着他粲然浅笑:“子元。”
管事推开屋门进来。“公子,吉时已到,该去迎新妇过门了。”
他从漫漫思绪中回过神来。“知道了,备车。”
一片红绸光影中,他默默走了出去。
绛旓細姝ゅ悗鐨勬暟鍗佸勾鍐咃紝铚姹夎钁涗寒銆佸缁村娆$巼鍐涘寳浼愭浌榄忥紝浣嗗缁堟湭鑳芥敼鍙樹笁瓒抽紟绔嬬殑鏍煎眬銆傛浌榄忓悗鏈熺殑瀹炴潈娓愭笎琚徃椹嚳鎺屾帶銆263骞达紝鏇归瓘鐨勫徃椹槶鍙戝姩榄忕伃铚涔嬫垬锛岃渶姹夌伃浜°備袱骞村悗鍙搁┈鏄梾姝伙紝鍏跺瓙鍙搁┈鐐庡簾榄忓厓甯濊嚜绔嬶紝寤哄浗鍙蜂负鈥滄檵鈥濓紝鍙茬О瑗挎檵銆傚叕鍏280骞达紝瑗挎檵鐏笢鍚达紝缁熶竴涓浗锛岃嚦姝涓夊浗鏃舵湡缁撴潫锛岃繘鍏...
绛旓細涓滄眽鏈勾鍒涓夊浗銆傞瓘铚鍚 涓夊浗鏃剁殑榄忓浗(鍏厓220骞-265骞)锛屽浜庨瓘鏂囧笣鏇逛笗锛岄瓘鍏冨笣鏇瑰锛屾浌涓曚箣鐖舵浌鎿嶈櫧鏈О甯濓紝浣嗘浌涓曠О甯濆悗杩藉皝浠栦负榄忓お绁栵紝榄忔湞锛岃鏇规搷鍏6甯濄傞瓘鏄笁鍥芥椂鏈熸渶涓哄己澶х殑鍥藉銆備笢姹夋湯骞达紝鍦版柟璞己鍔垮姏杩呴熷寮猴紝鍚勫湴璞己绾风悍璧峰叺鍓叉嵁鑷珛锛屼竴鏃堕棿鍏ㄥ浗鍙堥櫡鍏ュ唴鎴樻贩涔变箣涓傛浌鎿嶅垵鎹湁...
绛旓細涓夊浗灏辨槸涓涓湞浠c備笁鍥斤紙220骞达紞280骞达級鏄腑鍥芥眽鏈濅笌鏅嬫湞涔嬮棿鐨勪竴娈靛巻鍙叉椂鏈燂紝鍒嗕负鏇归瓘銆佽渶姹夈佷笢鍚翠笁涓斂鏉冦220骞达紝姹夋湞涓炵浉鏇逛笗绡℃眽绉板笣锛屽畾閮芥礇闃筹紝鍥藉彿鈥滈瓘鈥濓紝鍙茬О鏇归瓘锛屾眽鏈濇寮忕粨鏉熴221骞村垬澶囩О甯濓紝瀹氶兘鎴愰兘锛屽彶绉拌渶姹夈229骞村瓩鏉冪О甯濓紝瀹氶兘寤洪偤锛屽浗鍙封滃惔鈥濓紝鍙茬О涓滃惔銆263骞达紝鏇归瓘鐨勫徃椹...
绛旓細銆涓夊浗婕斾箟銆嬬殑鍏告晠锛氫笁椤捐寘搴愩佽崏鑸瑰熺銆佺伀鐑ц丹澹併佺┖鍩庤銆佺叜閰掕鑻遍泟銆佹鍥粨涔夈佷笁鑻辨垬鍚曞竷銆佽垖鎴樼兢鍎掋侀殕涓銆佸崟楠戞晳涓汇佷竷鎿掑瓱鑾风瓑銆1銆佷笁椤捐寘搴 鍏厓207骞村啲鑷冲叕鍏208骞存槬锛屽綋鏃跺悲鍏垫柊閲庯紙浠婃渤鍗楁柊閲庯級鐨勫垬澶囧甫鐫澶у皢鍏崇窘銆佸紶椋烇紝涓夋鍒板崡闃抽儭閭撳幙闅嗕腑锛堜粖瑗勯槼闅嗕腑锛夎钁涜崏搴愯璇歌憶浜嚭灞辫緟浣愮殑...
绛旓細銆涓夊浗婕斾箟銆嬪唴瀹规杩帮細涓滄眽鐏靛笣鏃讹紝鏃跺父渚嶄笓鏉冿紝鏈濇斂鑵愯触锛屽紶瑙掑彂鍔ㄩ粍宸捐捣涔夈傚垬澶囦笌鍏崇窘銆佸紶椋炴鍥笁缁撲箟锛屽弬涓庨晣鍘嬮粍宸惧啗銆傜伒甯濇锛屽ぇ灏嗗啗浣曡繘鎵剁珛灏戝笣锛岃瘡澶栧叺鍏ヤ含锛岃皨璇涘瀹樸傚瀹樻潃姝讳綍杩涳紝琚佺粛绛夊敖鐏瀹樸傝懀鍗撹秮鏈烘嫢鍏靛叆浜紝搴熷皯甯濓紝绔嬬尞甯濓紝鎶婃寔鏈濇斂銆傛浌鎿嶈皨鍒鸿懀鍗撲笉鎴愶紝鑱斿悎璇镐警鍏辫钁e崜銆傚垬銆佸叧...
绛旓細涓夊浗鏃舵湡缁忓巻浜60骞淬備笁鍥斤紙220骞达紞280骞达級鏄笂鎵夸笢姹変笅鍚タ鏅嬬殑涓娈靛巻鍙叉椂鏈燂紝鍒嗕负鏇归瓘銆佽渶姹夈佷笢鍚翠笁涓斂鏉冦傝丹澹佷箣鎴樻椂锛屾浌鎿嶈瀛欏垬鑱斿啗鍑昏触锛屽瀹氫簡涓夊浗榧庣珛鐨勯洀鍨嬨220骞达紝鏇逛笗绡℃眽绉板笣锛屽浗鍙封滈瓘鈥濓紝鍙茬О鏇归瓘锛屼笁鍥藉巻鍙叉寮忓紑濮嬨傛骞村垬澶囧湪鎴愰兘寤剁画姹夋湞锛屽彶绉拌渶姹夈222骞村垬澶囧湪澶烽櫟涔嬫垬澶辫触锛...
绛旓細涓夊浗缁撳眬鏄檵鐏笢鍚达紝缁熶竴涓浗銆190骞达紝姹夋湞鐨勪腑澶泦鏉冨埗搴﹀穿婧冿紝鍐涢榾鍥涜捣锛屽ぉ涓嬪ぇ涔便傚埌208骞寸殑璧ゅ涔嬫垬鏃讹紝鏇规搷琚瓩鍒樿仈鍐涘嚮璐ワ紝浠庢锛屽瀹氫簡涓夊浗榧庣珛鐨勯洀鍨嬨傛鍚庣殑鏁板崄骞村唴锛岃渶姹夎钁涗寒銆佸缁村娆$巼鍐涘寳浼愭浌榄忥紝浣嗗缁堟湭鑳芥敼鍙樹笁瓒抽紟绔嬬殑鏍煎眬銆傛浌榄忓悗鏈熺殑瀹炴潈娓愯鍙搁┈鎳挎帉鎺с263骞达紝鏇归瓘鐨勫徃椹槶鍙戝姩...
绛旓細涓夊浗锛堝叕鍏220骞磣280骞达紝鍙︽湁184骞淬190骞存垨208骞磋捣濮嬭锛夛紝鏄腑鍥藉巻鍙蹭笂涓滄眽涓庤タ鏅嬩箣闂寸殑鍒嗚瀵瑰硻鏃舵湡锛屾湁榄忥紙鏇归瓘锛夈佽渶锛堣渶姹夛級銆佸惔锛堜笢鍚达級涓変釜鏀挎潈銆備笁鍥界殗甯濆垪琛 榄忓浗 涓夊浗鏃剁殑榄忓浗锛堝叕鍏220骞-265骞达級锛屽浜庨瓘鏂囧笣鏇逛笗锛岄瓘鍏冨笣鏇瑰锛屾浌涓曚箣鐖舵浌鎿嶈櫧鏈О甯濓紝浣嗘浌涓曠О甯濆悗杩藉皝浠栦负榄忓お绁...
绛旓細1銆佹浌鎿 鏇规搷锛155骞达紞220骞3鏈15鏃 [1] 锛夛紝瀛楀瓱寰凤紝涓鍚嶅悏鍒╋紝灏忓瓧闃跨瀿锛屾矝鍥借隘鍘匡紙浠婂畨寰戒撼宸烇級浜恒備笢姹夋湯骞存澃鍑虹殑鏀挎不瀹躲佸啗浜嬪銆佹枃瀛﹀銆佷功娉曞锛涓夊浗涓浌榄忔斂鏉冪殑濂犲熀浜恒傛浌鎿嶆浘鎷呬换涓滄眽涓炵浉锛屽悗鍔犲皝榄忕帇锛屽瀹氫簡鏇归瓘绔嬪浗鐨勫熀纭銆傚幓涓栧悗璋ュ彿涓烘鐜嬨傚叾瀛愭浌涓曠О甯濆悗锛岃拷灏婁负姝︾殗甯濓紝搴欏彿...
绛旓細涓夊浗鏄笢姹夋湯骞淬傚湪涓滄眽鏈勾锛屾斂娌昏厫璐ュ拰绀句細鍔ㄨ崱瀵艰嚧浜嗗湴鏂瑰壊鎹拰鍐涢榾娣锋垬銆傚湪杩欎釜鑳屾櫙涓嬶紝鏇规搷銆佸垬澶囧拰瀛欐潈鍒嗗埆鍦ㄥ寳鏂广佽タ鍗楀拰涓崡寤虹珛浜嗚嚜宸辩殑鍔垮姏銆傞氳繃涓嶆柇鐨勬垬浜夊拰鑱旂洘锛岃繖涓変釜鍔垮姏閫愭笎澹ぇ锛屾渶缁堝舰鎴愪簡榄忋佽渶銆佸惔涓変釜鍥藉锛屽嵆鎵璋撶殑涓夊浗銆傝繖涓変釜鍥藉涔嬮棿杩涜浜嗛暱鏈熺殑鎴樹簤鍜屽浜よ仈鐩燂紝鏈缁堝湪鍏厓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