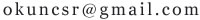余光中沙田山居的原文 余光中的沙田山居是属于哪本散文集?
\u6c99\u7530\u5c71\u5c45\u9605\u8bfb \u4f59\u5149\u4e2d1\uff0c\uff081\u30012\uff09\u5199\u6c99\u56ed\u5c71\u5c45\u7684\u5916\u56f4\u666f\u8272\uff083\u20266\uff09\u5199\u5c71\u5c45\u7684\u751f\u6d3b\u611f\u53d7\uff087\uff09\u5199\u5c71\u5c45\u98ce\u666f\u8054\u60f3\u5230\u5c71\u5916\u7684\u751f\u6d3b
2\uff0c\u4ee5\u5c71\u5c45\u751f\u6d3b\u4e3a\u7ebf\u7d22\uff0c\u4ee5\u542b\u84c4\u7684\u611f\u60c5\u548c\u4f18\u7f8e\u7684\u8bed\u8a00\u5199\u6c99\u56ed\u5c71\u5c45\u5468\u56f4\u7684\u7fa4\u5c71\u53ca\u6d77\u6c34\u7684\u72ec\u7279\u7684\u98ce\u666f\uff0c\u4ee5\u53ca\u5c71\u5c45\u751f\u6d3b\u7684\u5fc3\u60c5\u611f\u53d7\uff0c\u4ee5\u65e0\u4e00\u5b57\u5199\u4e61\u6101\uff0c\u5374\u901a\u7bc7\u90fd\u6709\u6de1\u6de1\u7684\u4e61\u6101\uff0c\u8868\u73b0\u51fa\u4e61\u6101\u7684\u4e3b\u9898
3\uff0c\u4ee5\u8bd7\u7ed3\u5c3e\uff0c\u7167\u5e94\u5f00\u5934\uff0c\u4f7f\u542b\u84c4\u5728\u6574\u7bc7\u6587\u7ae0\u4e2d\u7684\u601d\u60f3\u611f\u60c5\u660e\u6717\u5316\uff0c\u4eca\u8bfb\u8005\u56de\u5473\u5168\u6587\uff0c\u4e0e\u4f5c\u8005\u4ea7\u751f\u611f\u60c5\u5171\u9e23\u3002
\u5c31\u662f\u51fa\u81ea\u4ed6\u7684\u6563\u6587\u96c6\u300a\u6c99\u7530\u5c71\u5c45\u300b\u3002\u671b\u91c7\u7eb3\u3002
沙田山居 作者:余光中书斋外面是阳台,阳台外面是海,是山,海是碧湛湛的一弯,山是青郁郁的连环。山外有山,最远的翠微淡成一袅青烟,忽焉似有,再顾若无,那便是,大陆的莽莽苍苍了。日月闲闲,有的是时间与空间。一览不尽的青山绿水,马远夏圭的长幅横披,任风吹,任鹰飞,任渺渺之目舒展来回,而我在其中俯仰天地,呼吸晨昏,竟已有十八个月了。十八个月,也就是说;重九的陶菊已经两开;中秋的苏月已经圆过两次了。
海天相对,中间是山;即使是秋晴的日子,透明的蓝光里;也还有一层轻轻的海气,疑幻疑真,像开着一面玄奥的迷镜;照镜的不是人,是神。海与山绸缪在一起;分不出,是海侵入了山间,还是山诱俘了海水;只见海把山围成了一角角的半岛,山呢,把海围成了一汪汪的海湾。山色如环,困不住浩渺的南海,毕竟在东北方缺了一口,放墙桅出去,风帆进来。最是晴艳的下午,八仙岭下,一艘白色渡轮,迎着酣美的斜阳悠悠向大埔驶去,整个吐露港平铺着千顷的碧蓝;就为了反衬那一影耀眼的洁白。起风的日子,海吹成了千亩蓝田,无数的百合此开彼落。到了深夜,所有的山影黑沉沉都睡去,远远近近,零零落落的灯全睡去,只留下一阵阵的潮声起伏;永恒的鼾息,撼人的节奏撼我的心血来潮。有时十几盏渔火赫然,浮现在阒黑的海面;排成一弯弧形,把渔网愈收愈小,围成一丛灿灿的金莲。
海围着山,山围着我。沙田山居,峰回路转。我的朝朝暮暮,日起日落,月望月朔,全
在此中度过,我成了山人。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山已经代我答了。其实山并未回答;是鸟代山答了;是虫,是松风代山答了。山是禅机深藏的高僧,轻易不开口的。人在楼上倚栏杆,山列坐在四面如十八尊罗汉叠罗汉;相看两不厌。早晨,我攀上佛头去看日出,黄昏,从联合书院的文学院一路走回来,家,在半山腰上等我;那地势,比佛肩要低,却比佛肚子要高些。这时,山什么也不说,只是争噪的鸟雀泄漏了他愉悦的心境。等到众鸟栖定,山影茫然,天籁便低沉下去,若断若续,树间的歌者才歇一下,草间的吟哦又四起。至于山坳下面那小小的幽谷;形式和地位都相当于佛的肚脐,深凹之中别有一番谐趣。山谷是一个爱音乐的村女,最喜欢学舌拟声,可惜太害羞。技巧不很高明。无论是鸟鸣犬吠,或是火车在谷口扬笛路过,她也要学叫一声,落后半拍,应人的尾音。
从我的楼上望去,马鞍山奇拔而峻峭,屏于东方,使朝晖姗姗其来迟。鹿山巍然而逼近,魁梧的肩曾遮去了半壁西天;催黄昏早半个小时来临,一个分神,夕阳便落进他的僧袖里去了。一炉晚霞,黄铜烧成赤金又化作紫灰与青烟,壮哉崦嵫的神话,太阳的葬礼。阳台上;坐看晚景变幻成夜色;似乎很缓慢,又似乎非常敏捷,才觉霞光烘颊,余曛在树,忽然变生咫尺,眈眈的黑影已伸及你的肘腋,夜,早从你背后袭来。那过程,是一种绝妙的障眼法,非眼睫所能守望的。等到夜色四合,黑暗已成定局,四周的山影,重甸甸阴森森的,令人肃然而恐。尤其是西屏的鹿山,白天还如佛如增,蔼然可亲,这时竟收起法相,庞然而踞,黑毛茸蒙如一尊暗中伺人的怪兽,隐然,有一种潜伏的不安。
千山磅礴的来势如压,谁敢相撼?但是云烟一起,庄重的山态便改了。雾来的日子,山变成一座座的列屿,在白烟的横波回澜里,载浮载沉。八仙岭果真化作了过海的八仙,时在波上,时在弥漫的云间。有一天早晨,举目一望,八仙和马鞍和远远近近的大小众峰,全不见了,偶尔云开一线,当头的鹿山似从天隙中隐隐相窥,去大埔的车辆出没在半空。我的阳台脱离了一切;下临无地;在汹涌的白涛上自由来去。谷中的鸡犬从云下传来,从辽远的人间。我走去更高处的联合书院上课,满地白云,师生衣袂飘然,都成了神仙。我登上讲坛说道,烟云都穿窗探首来旁听。
起风的日子,一切云云雾雾的朦胧氤氲全被拭净,水光山色,纤毫悉在镜里。原来对岸的八仙岭下,历历可数,有这许多山村野店,水浒人家。半岛的天气一日数变,风骤然而来,从海口长驱直入;脚下的山谷顿成风箱,抽不尽满壑的咆哮翻腾。躁蹲着罗汉松与芦草,掀翻海水,吐着白浪,风是一群透明的猛兽,奔踹而来;呼啸而去。
海潮与风声,即使撼天震地,也不过为无边的静加注荒情与野趣罢了。最令人心动而神往的,却是人为的骚音。从清早到午夜,一天四十多个班,在山和海之间。敲轨而来,鸣笛而去的,是九广铁路的客车,货车,猪车。曳着黑烟的飘发,蟠婉着十三节车厢的修长之躯,这些工业时代的元老级交通工具,仍有旧世界迷人的情调,非协和的超音速飞机所能比拟、山下的铁轨向北延伸;延伸着我的心弦。我的中枢神经,一日四十多次,任南下又北上的千只铁轮轮番敲打,用钢铁火花的壮烈节奏,提醒我,藏在谷底的并不是洞里桃源;住在山上,我亦非桓景,即使王粲,也不能不下楼去:
栏杆三面压人眉睫是青山
碧螺黛迤逦的边愁欲连环
叠嶂之后是重峦,一层淡似一层
湘云之后是楚烟,山长水远
五千载与八万万,全在那里面……
作者简介
余光中(1928-),台湾著名诗人、散文家、批评家、翻译家。祖籍福建永春,生于江苏南京 ,曾就读于金陵大学外 语系(后转入厦门大学 ),1948年随父母迁香港,次年赴台。195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 外文系。1953年,与覃子豪、钟鼎文等共创“蓝星”诗社。1959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LOWA)艺术硕士。先后任教台湾东吴大学、师范大学、台湾大学、政治大学,现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 长。曾获得包括《吴三连文学奖》、《中国时报奖》、《金鼎奖》、《国家文艺奖》等台湾所有重要奖项,已出版诗文及译著共40 余种。 2012年4月,84岁的余光中受聘为北京大学“驻校诗人”。
书斋外面是阳台,阳台外面是海,是山,海是碧湛湛的一弯,山是青郁郁的连环。山外
有山,最远的翠微淡成一袅青烟,忽焉似有,再顾若无,那便是,大陆的莽莽苍苍了。日月
闲闲,有的是时间与空间。一览不尽的青山绿水,马远夏圭的长幅横披,任风吹,任鹰飞,
任渺渺之目舒展来回,而我在其中俯仰天地,呼吸晨昏,竟已有十八个月了。十八个月,也
就是说;重九的陶菊已经两开;中秋的苏月已经圆过两次了。
海天相对,中间是山;即使是秋晴的日子,透明的蓝光里;也还有一层轻轻的海气,疑
幻疑真,像开着一面玄奥的迷镜;照镜的不是人,是神。海与山绸缪在一起;分不出,是海
侵入了山间,还是山诱俘了海水;只见海把山围成了一角角的半岛,山呢,把海围成了一汪
汪的海湾。山色如环,困不住浩渺的南海,毕竟在东北方缺了一口,放墙桅出去,风帆进
来。最是晴艳的下午,八仙岭下,一艘白色渡轮,迎着酣美的斜阳悠悠向大埔驶去,整个吐
露港平铺着千顷的碧蓝;就为了反衬那一影耀眼的洁白。起风的日子,海吹成了千亩蓝田,
无数的百合此开彼落。到了深夜,所有的山影黑沉沉都睡去,远远近近,零零落落的灯全睡
去,只留下一阵阵的潮声起伏;永恒的鼾息,撼人的节奏撼我的心血来潮。有时十几盏渔火
赫然,浮现在阒黑的海面;排成一弯弧形,把渔网愈收愈小,围成一丛灿灿的金莲。
海围着山,山围着我。沙田山居,峰回路转。我的朝朝暮暮,日起日落,月望月朔,全
在此中度过,我成了山人。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山已经代我答了。其实山并未回
答;是鸟代山答了;是虫,是松风代山答了。山是禅机深藏的高僧,轻易不开口的。人在楼
上倚栏杆,山列坐在四面如十八尊罗汉叠罗汉;相看两不厌。早晨,我攀上佛头去看日出,
黄昏,从联合书院的文学院一路走回来,家,在半山腰上等我;那地势,比佛肩要低,却比
佛肚子要高些。这时,山什么也不说,只是争噪的鸟雀泄漏了他愉悦的心境。等到众鸟栖
定,山影茫然,天籁便低沉下去,若断若续,树间的歌者才歇一下,草间的吟哦又四起。至
于山坳下面那小小的幽谷;形式和地位都相当于佛的肚脐,深凹之中别有一番谐趣。山谷是
一个爱音乐的村女,最喜欢学舌拟声,可惜太害羞。技巧不很高明。无论是鸟鸣犬吠,或是
火车在谷口扬笛路过,她也要学叫一声,落后半拍,应人的尾音。
从我的楼上望去,马鞍山奇拔而峻峭,屏于东方,使朝晖姗姗其来迟。鹿山巍然而逼
近,魁梧的肩曾遮去了半壁西天;催黄昏早半个小时来临,一个分神,夕阳便落进他的僧袖
里去了。一炉晚霞,黄铜烧成赤金又化作紫灰与青烟,壮哉崦嵫的神话,太阳的葬礼。阳台
上;坐看晚景变幻成夜色;似乎很缓慢,又似乎非常敏捷,才觉霞光烘颊,余曛在树,忽然
变生咫尺,眈眈的黑影已伸及你的肘腋,夜,早从你背后袭来。那过程,是一种绝妙的障眼
法,非眼睫所能守望的。等到夜色四合,黑暗已成定局,四周的山影,重甸甸阴森森的,令
人肃然而恐。尤其是西屏的鹿山,白天还如佛如增,蔼然可亲,这时竟收起法相,庞然而
踞,黑毛茸蒙如一尊暗中伺人的怪兽,隐然,有一种潜伏的不安。
千山磅礴的来势如压,谁敢相撼?但是云烟一起,庄重的山态便改了。雾来的日子,山
变成一座座的列屿,在白烟的横波回澜里,载浮载沉。八仙岭果真化作了过海的八仙,时在
波上,时在弥漫的云间。有一天早晨,举目一望,八仙和马鞍和远远近近的大小众峰,全不
见了,偶尔云开一线,当头的鹿山似从天隙中隐隐相窥,去大埔的车辆出没在半空。我的阳
台脱离了一切;下临无地;在汹涌的白涛上自由来去。谷中的鸡犬从云下传来,从辽远的人
间。我走去更高处的联合书院上课,满地白云,师生衣袂飘然,都成了神仙。我登上讲坛说
道,烟云都穿窗探首来旁听。
起风的日子,一切云云雾雾的朦胧氤氲全被拭净,水光山色,纤毫悉在镜里。原来对岸
的八仙岭下,历历可数,有这许多山村野店,水浒人家。半岛的天气一日数变,风骤然而
来,从海口长驱直入;脚下的山谷顿成风箱,抽不尽满壑的咆哮翻腾。躁蹲着罗汉松与芦
草,掀翻海水,吐着白浪,风是一群透明的猛兽,奔踹而来;呼啸而去。
海潮与风声,即使撼天震地,也不过为无边的静加注荒情与野趣罢了。最令人心动而神
往的,却是人为的骚音。从清早到午夜,一天四十多个班,在山和海之间。敲轨而来,鸣笛
而去的,是九广铁路的客车,货车,猪车。曳着黑烟的飘发,蟠婉着十三节车厢的修长之
躯,这些工业时代的元老级交通工具,仍有旧世界迷人的情调,非协和的超音速飞机所能比
拟、山下的铁轨向北延伸;延伸着我的心弦。我的中枢神经,一日四十多次,任南下又北上
的千只铁轮轮番敲打,用钢铁火花的壮烈节奏,提醒我,藏在谷底的并不是洞里桃源;住在
山上,我亦非桓景,即使王粲,也不能不下楼去:
书斋外面是阳台,阳台外面是海,是山,海是碧湛湛的一弯,山是青郁郁的连环。山外有山,最远的翠微淡成一袅青烟,忽焉似有,再顾若无,那便是,大陆的莽莽苍苍了。日月闲闲,有的是时间与空间。一览不尽的青山绿水,马远夏圭的长幅横披,任风吹,任鹰飞,任渺渺之目舒展来回,而我在其中俯仰天地,呼吸晨昏,竟已有十八个月了。十八个月,也就是说;重九的陶菊已经两开;中秋的苏月已经圆过两次了。
海天相对,中间是山;即使是秋晴的日子,透明的蓝光里;也还有一层轻轻的海气,疑幻疑真,像开着一面玄奥的迷镜;照镜的不是人,是神。海与山绸缪在一起;分不出,是海侵入了山间,还是山诱俘了海水;只见海把山围成了一角角的半岛,山呢,把海围成了一汪汪的海湾。山色如环,困不住浩渺的南海,毕竟在东北方缺了一口,放墙桅出去,风帆进来。最是晴艳的下午,八仙岭下,一艘白色渡轮,迎着酣美的斜阳悠悠向大埔驶去,整个吐露港平铺着千顷的碧蓝;就为了反衬那一影耀眼的洁白。起风的日子,海吹成了千亩蓝田,无数的百合此开彼落。到了深夜,所有的山影黑沉沉都睡去,远远近近,零零落落的灯全睡去,只留下一阵阵的潮声起伏;永恒的鼾息,撼人的节奏撼我的心血来潮。有时十几盏渔火赫然,浮现在阒黑的海面;排成一弯弧形,把渔网愈收愈小,围成一丛灿灿的金莲。海围着山,山围着我。沙田山居,峰回路转。我的朝朝暮暮,日起日落,月望月朔,全在此中度过,我成了山人。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山已经代我答了。其实山并未回答;是鸟代山答了;是虫,是松风代山答了。山是禅机深藏的高僧,轻易不开口的。人在楼上倚栏杆,山列坐在四面如十八尊罗汉叠罗汉;相看两不厌。早晨,我攀上佛头去看日出,黄昏,从联合书院的文学院一路走回来,家在半山腰上等我;那地势,比佛肩要低,却比佛肚子要高些。这时,山什么也不说,只是争噪的鸟雀泄漏了他愉悦的心境。等到众鸟栖定,山影茫然,天籁便低沉下去,若断若续,树间的歌者才歇一下,草间的吟哦又四起。至于山坳下面那小小的幽谷;形式和地位都相当于佛的肚脐,深凹之中别有一番谐趣。山谷是一个爱音乐的村女,最喜欢学舌拟声,可惜太害羞。技巧不很高明。无论是鸟鸣犬吠,或是火车在谷口扬笛路过,她也要学叫一声,落后半拍,应人的尾音。从我的楼上望去,马鞍山奇拔而峻峭,屏于东方,使朝晖姗姗其来迟。鹿山巍然而逼近,魁梧的肩曾遮去了半壁西天;催黄昏早半个小时来临,一个分神,夕阳便落进他的僧袖里去了。一炉晚霞,黄铜烧成赤金又化作紫灰与青烟,壮哉崦嵫的神话,太阳的葬礼。阳台上;坐看晚景变幻成夜色;似乎很缓慢,又似乎非常敏捷,才觉霞光烘颊,余曛在树,忽然变生咫尺,眈眈的黑影
伸及你的肘腋,夜,早从你背后袭来。那过程,是一种绝妙的障眼法,非眼睫所能守望的。等到夜色四合,黑暗已成定局,四周的山影,重甸甸阴森森的,令人肃然而恐。尤其是西屏的鹿山,白天还如佛如增,蔼然可亲,这时竟收起法相,庞然而踞,黑毛茸蒙如一尊暗中伺人的怪兽,隐然,有一种潜伏的不安。
千山磅礴的来势如压,谁敢相撼?但是云烟一起,庄重的山态便改了。雾来的日子,山变成一座座的列屿,在白烟的横波回澜里,载浮载沉。八仙岭果真化作了过海的八仙,时在波上,时在弥漫的云间。有一天早晨,举目一望,八仙和马鞍和远远近近的大小众峰,全不见了,偶尔云开一线,当头的鹿山似从天隙中隐隐相窥,去大埔的车辆出没在半空。我的阳台脱离了一切;下临无地;在汹涌的白涛上自由来去。谷中的鸡犬从云下传来,从辽远的人间。我走去更高处的联合书院上课,满地白云,师生衣袂飘然,都成了神仙。我登上讲坛说道,烟云都穿窗探首来旁听。
起风的日子,一切云云雾雾的朦胧氤氲全被拭净,水光山色,纤毫悉在镜里。原来对岸的八仙岭下,历历可数,有这许多山村野店,水浒人家。半岛的天气一日数变,风骤然而来,从海口长驱直入;脚下的山谷顿成风箱,抽不尽满壑的咆哮翻腾。躁蹲着罗汉松与芦草,掀翻海水,吐着白浪,风是一群透明的猛兽,奔踹而来;呼啸而去。
海潮与风声,即使撼天震地,也不过为无边的静加注荒情与野趣罢了。最令人心动而神往的,却是人为的骚音。从清早到午夜,一天四十多个班,在山和海之间。敲轨而来,鸣笛而去的,是九广铁路的客车,货车,猪车。曳着黑烟的飘发,蟠婉着十三节车厢的修长之躯,这些工业时代的元老级交通工具,仍有旧世界迷人的情调,非协和的超音速飞机所能比拟、山下的铁轨向北延伸;延伸着我的心弦。我的中枢神经,一日四十多次,任南下又北上的千只铁轮轮番敲打,用钢铁火花的壮烈节奏,提醒我,藏在谷底的并不是洞里桃源;住在山上,我亦非桓景,即使王粲,也不能不下楼去:
栏杆三面压人眉睫是青山
碧螺黛迤逦的边愁欲连环
叠嶂之后是重峦,一层淡似一层
湘云之后是楚烟,山长水远
五千载与八万万,全在那里面……
书斋外面是阳台,阳台外面是海,是山,海是碧湛湛的一弯,山是青郁郁的连环。山外有山,最远的翠微淡成一袅青烟,忽焉似有,再顾若无,那便是,大陆的莽莽苍苍了。日月闲闲,有的是时间与空间。一览不尽的青山绿水,马远夏圭的长幅横披,任风吹,任鹰飞,任渺渺之目舒展来回,而我在其中俯仰天地,呼吸晨昏,竟已有十八个月了。十八个月,也就是说;重九的陶菊已经两开;中秋的苏月已经圆过两次了。
海天相对,中间是山;即使是秋晴的日子,透明的蓝光里;也还有一层轻轻的海气,疑幻疑真,像开着一面玄奥的迷镜;照镜的不是人,是神。海与山绸缪在一起;分不出,是海侵入了山间,还是山诱俘了海水;只见海把山围成了一角角的半岛,山呢,把海围成了一汪汪的海湾。山色如环,困不住浩渺的南海,毕竟在东北方缺了一口,放墙桅出去,风帆进来。最是晴艳的下午,八仙岭下,一艘白色渡轮,迎着酣美的斜阳悠悠向大埔驶去,整个吐露港平铺着千顷的碧蓝;就为了反衬那一影耀眼的洁白。起风的日子,海吹成了千亩蓝田,无数的百合此开彼落。到了深夜,所有的山影黑沉沉都睡去,远远近近,零零落落的灯全睡去,只留下一阵阵的潮声起伏;永恒的鼾息,撼人的节奏撼我的心血来潮。有时十几盏渔火赫然,浮现在阒黑的海面;排成一弯弧形,把渔网愈收愈小,围成一丛灿灿的金莲。海围着山,山围着我。沙田山居,峰回路转。我的朝朝暮暮,日起日落,月望月朔,全在此中度过,我成了山人。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山已经代我答了。其实山并未回答;是鸟代山答了;是虫,是松风代山答了。山是禅机深藏的高僧,轻易不开口的。人在楼上倚栏杆,山列坐在四面如十八尊罗汉叠罗汉;相看两不厌。早晨,我攀上佛头去看日出,黄昏,从联合书院的文学院一路走回来,家在半山腰上等我;那地势,比佛肩要低,却比佛肚子要高些。这时,山什么也不说,只是争噪的鸟雀泄漏了他愉悦的心境。等到众鸟栖定,山影茫然,天籁便低沉下去,若断若续,树间的歌者才歇一下,草间的吟哦又四起。至于山坳下面那小小的幽谷;形式和地位都相当于佛的肚脐,深凹之中别有一番谐趣。山谷是一个爱音乐的村女,最喜欢学舌拟声,可惜太害羞。技巧不很高明。无论是鸟鸣犬吠,或是火车在谷口扬笛路过,她也要学叫一声,落后半拍,应人的尾音。从我的楼上望去,马鞍山奇拔而峻峭,屏于东方,使朝晖姗姗其来迟。鹿山巍然而逼近,魁梧的肩曾遮去了半壁西天;催黄昏早半个小时来临,一个分神,夕阳便落进他的僧袖里去了。一炉晚霞,黄铜烧成赤金又化作紫灰与青烟,壮哉崦嵫的神话,太阳的葬礼。阳台上;坐看晚景变幻成夜色;似乎很缓慢,又似乎非常敏捷,才觉霞光烘颊,余曛在树,忽然变生咫尺,眈眈的黑影
伸及你的肘腋,夜,早从你背后袭来。那过程,是一种绝妙的障眼法,非眼睫所能守望的。等到夜色四合,黑暗已成定局,四周的山影,重甸甸阴森森的,令人肃然而恐。尤其是西屏的鹿山,白天还如佛如增,蔼然可亲,这时竟收起法相,庞然而踞,黑毛茸蒙如一尊暗中伺人的怪兽,隐然,有一种潜伏的不安。
千山磅礴的来势如压,谁敢相撼?但是云烟一起,庄重的山态便改了。雾来的日子,山变成一座座的列屿,在白烟的横波回澜里,载浮载沉。八仙岭果真化作了过海的八仙,时在波上,时在弥漫的云间。有一天早晨,举目一望,八仙和马鞍和远远近近的大小众峰,全不见了,偶尔云开一线,当头的鹿山似从天隙中隐隐相窥,去大埔的车辆出没在半空。我的阳台脱离了一切;下临无地;在汹涌的白涛上自由来去。谷中的鸡犬从云下传来,从辽远的人间。我走去更高处的联合书院上课,满地白云,师生衣袂飘然,都成了神仙。我登上讲坛说道,烟云都穿窗探首来旁听。
起风的日子,一切云云雾雾的朦胧氤氲全被拭净,水光山色,纤毫悉在镜里。原来对岸的八仙岭下,历历可数,有这许多山村野店,水浒人家。半岛的天气一日数变,风骤然而来,从海口长驱直入;脚下的山谷顿成风箱,抽不尽满壑的咆哮翻腾。躁蹲着罗汉松与芦草,掀翻海水,吐着白浪,风是一群透明的猛兽,奔踹而来;呼啸而去。
海潮与风声,即使撼天震地,也不过为无边的静加注荒情与野趣罢了。最令人心动而神往的,却是人为的骚音。从清早到午夜,一天四十多个班,在山和海之间。敲轨而来,鸣笛而去的,是九广铁路的客车,货车,猪车。曳着黑烟的飘发,蟠婉着十三节车厢的修长之躯,这些工业时代的元老级交通工具,仍有旧世界迷人的情调,非协和的超音速飞机所能比拟、山下的铁轨向北延伸;延伸着我的心弦。我的中枢神经,一日四十多次,任南下又北上的千只铁轮轮番敲打,用钢铁火花的壮烈节奏,提醒我,藏在谷底的并不是洞里桃源;住在山上,我亦非桓景,即使王粲,也不能不下楼去:
栏杆三面压人眉睫是青山
碧螺黛迤逦的边愁欲连环
叠嶂之后是重峦,一层淡似一层
湘云之后是楚烟,山长水远
五千载与八万万,全在那里面……
绛旓細1锛鍘熸枃锛氫功鏂嬪闈㈡槸闃冲彴锛岄槼鍙板闈㈡槸娴凤紝鏄北锛屾捣鏄ⅶ婀涙箾鐨勪竴寮紝灞辨槸闈掗儊閮佺殑杩炵幆銆傚北澶栨湁灞憋紝鏈杩滅殑缈犲井娣℃垚涓琚呴潚鐑燂紝蹇界剦浼兼湁锛屽啀椤捐嫢鏃狅紝閭d究鏄紝澶ч檰鐨勮幗鑾借媿鑻嶄簡銆傛棩鏈堥棽闂诧紝鏈夌殑鏄椂闂翠笌绌洪棿銆備竴瑙堜笉灏界殑闈掑北缁挎按锛岄┈杩滃鍦殑闀垮箙妯姭锛屼换椋庡惞锛屼换楣伴锛屼换娓烘负涔嬬洰鑸掑睍鏉ュ洖锛岃屾垜鍦...
绛旓細娌欑敯灞卞眳锛屽嘲鍥炶矾杞紝鎴戠殑鏈濇湞鏆毊锛屾棩璧锋棩钀斤紝鏈堟湜鏈堟湐锛屽叏鍦ㄦ涓害杩囷紝鎴戞垚浜嗗北浜銆傞棶浣欎綍浜嬫爾纰у北锛岀瑧鑰屼笉绛旓紝灞卞凡缁忎唬鎴戠瓟浜嗐傚叾瀹炲北骞舵湭鍥炵瓟锛屾槸楦熶唬灞辩瓟浜嗭紝鏄櫕锛屾槸鏉鹃浠e北绛斾簡銆傚北鏄鏈烘繁钘忕殑楂樺儳锛岃交鏄撲笉寮鍙g殑銆備汉鍦ㄦゼ涓婂氭爮鏉嗭紝灞卞垪鍧愬湪鍥涢潰濡傚崄鍏皧缃楁眽鍙犵綏姹夛紝鐩哥湅涓や笉鍘屻...
绛旓細涓嶅睘浜庛傘娌欑敯灞卞眳銆嬫槸浣欏厜涓鍐欑殑鏂囩珷锛岃妭閫夋湁涔︽枊澶栭潰鏄槼鍙帮紝闃冲彴澶栭潰鏄捣锛屾槸灞憋紝娴锋槸纰ф箾婀涚殑涓寮紝灞辨槸闈掗儊閮佺殑杩炵幆锛屾槸涓绡囨濅埂鐨勬枃绔狅紝涓嶅睘浜庢父璁般傛父璁版槸鎸囦互璁拌堪娓歌缁忓巻鍜屽湴鏂归鍏変负涓荤殑鏂囧鏍峰紡锛屾槸鏁f枃鐨勪竴涓被鍨嬨
绛旓細鍘熸潵锛岃繖閲岃兘閬ユ湜鈥滃ぇ闄嗙殑鑾借幗鑻嶈媿鈥濓紝浣滆呮墍鍜忓徆鐨勨滄箻浜戜箣鍚庢槸妤氱儫锛屽北姘撮暱杩/ 浜斿崈杞戒笌鍏竾涓囷紝鍏ㄥ湪閭i噷闈⑩︹︹濇鏄尌涔嬩笉鍘荤殑涔℃剚缁欎粬鐨勫北灞呯敓娲诲钩娣讳簡鍑犺蹇ц檻銆傚彲瑙侊紝鍏ㄦ枃浠娌欑敯灞卞眳涓烘姃鎯呯殑濂戞満锛屾櫙涓惈鎯咃紝鎯呰暣鏅腑锛屾濅埂涔嬫儏娌圭劧鑰岀敓锛屼娇鏈枃鐨勪富鏃ㄨ〃杩板惈鑰屼笉闇诧紝绮惧鐫挎櫤銆傛枃涓瑷鍙ら泤...
绛旓細楂樹腑璇炬湰鎵閫夌殑浣欏厜涓殑鏁f枃銆娌欑敯灞卞眳銆嬶紝浠ュ叾鐗规湁鐨勭瑪娉曪紝鍐欎簡浠栧湪棣欐腐鈥滃北灞呪濋槼鍙颁笂娆h祻鍒扮殑鏅壊鐗圭偣锛屽鍛ㄥ洿鐨勬櫙鐗╄繘琛屼簡绮惧績鐨勬弿鎽癸紝鏃㈠啓浜嗗鍦ㄦ櫙瑙傦紝鍙堝啓浜嗗唴蹇冪殑鎰熷彈锛屾儏鏅氦铻嶃傛枃绔犳繁鍘氱殑鏂囧寲鍐呮兜锛岃瘲涓鏍风殑璇█锛岃〃鐜颁簡浣滆呭绁栧浗鍙婄鍥芥枃鍖栫殑鐑埍锛岄偅娣辨繁鐨勪埂鎰佹洿璁╀汉闅句互蹇樻銆備笅闈㈠氨浠庝綔鑰...
绛旓細娌欑敯灞卞眳涓〃鐜颁埂鎰佺殑鍦版柟 鈥滆棌鍦ㄨ胺搴曠殑骞朵笉鏄礊閲屾婧愶紝浣忓湪灞变笂锛屾垜浜﹂潪妗撴櫙锛屽嵆浣跨帇绮诧紝涔熶笉鑳戒笉涓嬫ゼ鍘烩濃憼鈥滀笅妤煎幓鈥濇殫绀鸿嚜宸卞仛涓嶅緱鈥滃北浜衡濓紝蹇樹笉浜嗗皹涓栵紝鍓蹭笉鏂晠鍥戒箣鎯咃紝瑕佷粠鈥滀粰澧冣濇姇鍏ョ幇瀹炩憽杩欒〃杈句簡浣滆呮复鐩肩鍥界粺涓鐨勬濇兂鎰熸儏 1974骞达紝浣欏厜涓鍒伴娓腑鏂囧ぇ瀛︿换鏁欙紝灞呬綇鍦ㄩ娓節榫欏崐宀涙矙鐢...
绛旓細娌欑敯灞卞眳 浣欏厜涓 姣斿柣鍙ワ細1銆佹捣澶╃浉瀵癸紝涓棿鏄北锛屽嵆浣挎槸绉嬫櫞鐨勬棩瀛愶紝閫忔槑鐨勮摑鍏夐噷锛屼篃杩樻湁涓灞傝交杞荤殑娴锋皵锛岀枒骞荤枒鐪燂紝鍍忓紑鐫涓闈㈢巹濂ョ殑杩烽暅锛岀収闀滅殑涓嶆槸浜猴紝鏄銆2銆佸北鏄鏈烘繁钘忕殑楂樺儳锛岃交鏄撲笉寮鍙g殑銆備汉鍦ㄦゼ涓婂氭爮鏉嗭紝灞卞垪鍧愬湪鍥涢潰濡傚崄鍏皧缃楁眽鍙犵綏姹夛紝鐩哥湅涓や笉鍘屻傚北璋锋槸涓涓埍闊充箰鐨...
绛旓細涓銆併娌欑敯灞卞眳銆嬬殑涓昏鍐呭 鍑犲崄骞村墠浣欏厜涓鍏堢敓鏉ュ埌涓枃澶у鎵ф暀锛岄潰瀵归娓編涓界殑鑷劧椋庡厜锛屽啓涓嬩簡澶氱瘒鍒叿闊靛懗鐨勬暎鏂囷紝鎶掑彂瀵归娓編鏅殑鎰熷徆銆傛棤瑷鐨勫北姘达紝鍔ㄩ潤璧锋锛屽湪鐩哥煡鐨勪綔鑰呯溂涓紝閮芥湁鍒牱鐨勫崜瓒婇濮匡紝閮芥湁娉㈡緶澹様鐨勫ぇ鍔ㄤ綔銆傛棤璁洪浜戞祦鍔紝杩樻槸姘存尝璧峰叴锛屼綔鑰呬笉鏂彂鐜拌嚜鐒跺够鍖栧嚭鐨勭濂囥傛矙鐢扮殑...
绛旓細琛ㄨ揪浜嗕綔鑰呮复鐩肩鍥界粺涓鐨勬濇兂鎰熸儏绐佸嚭涓婚锛堟垨琛墭銆佺収搴旓級 鐞嗙敱锛氣滄垚浜嗕富浜衡濓紝璇存槑鑷繁濡傚湪浠欏涓敓娲伙紝鎸夊父鐞嗗簲甯屾湜姘歌繙杩欐牱鐢熸椿涓嬪幓锛屽彲浣滆呭嵈鏈夋洿楂樿繙鐨勮拷姹傦紝鈥滀笅妤煎幓鈥濈淮鎶ょ鍥界粺涓銆傜涓閮ㄥ垎锛堢1娈碉級鎬诲啓娌欑敯灞卞眳鐨鎯呭喌锛岄忛湶鍑轰埂鎰佷箣鎯呫傜涓灞傦紙绗2娈碉級鍐欏洿鐫灞辩殑娴凤紝鏄鍥达紝鏄繙瑙傘
绛旓細娌欑敯灞卞眳 銆婃矙鐢板北灞呫嬫槸鍙版咕鐭ュ悕浣滃浣欏厜涓鎵浣滅殑涓绡囦紭缇庢暎鏂囥備綑鍏堢敓鐨勮繖绡囨暎鏂囨枃濡傚叾棰橈紝鍐欑殑鏄綔鑰呬换鏁欓娓腑鏂囧ぇ瀛︽椂娌欑敯灞卞眳鐨缇庢櫙鍜屾劅鎮熴傚湪鏂囦腑锛屼綔鑰呯嫭鍏锋収鐪硷紝闂逛腑鍙栭潤锛屽璇繁鎯咃紝浠璇椾汉鐨勮瑙掋佺函绮圭殑绗斿ⅷ鍜屾偁娣辩殑鎰忓涓烘垜浠弿缁樹簡涓骞呴兘甯備箣涓殑涓栧妗冩簮锛屽鍝嶄簡涓鏇插皹鍤d箣闂寸殑绌鸿胺缁濆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