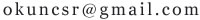你在圣弗兰西斯科做什么怎么样
这是什么歌? “如果你来到圣弗兰西斯科…夏天是最好的…”
\u641c\uff0c\u4f60\u5728\u5723\u5f17\u5170\u897f\u65af\u79d1\u505a\u4ec0\u4e48\uff0c\u7684\u7535\u5b50\u4e66
\u8981\u4e0d\u8981\u6211\u76f4\u63a5\u63a8\u8350\u4f60\u4e00\u4e2a\u514d\u8d39\u4e0b\u8f7d\u5404\u7c7b\u7535\u5b50\u4e66\u7684\u7f51\u7ad9\uff1f
\u8fd9\u6837\u4f60\u60f3\u770b\u4ec0\u4e48\u5c31\u4e0b\u8f7d\u4ec0\u4e48\u3002
\u3000\u3000\u6253\u5f00\u767e\u5ea6\u9996\u9875\uff0c\u5728\u8f93\u5165\u6846\u9876\u90e8\u7684\u83dc\u5355\u4e2d\u70b9\u51fb\u3010\u97f3\u4e50\u3011\u3002
\u3000\u3000\u5982\u679c\u6211\u4eec\u77e5\u9053\u7684\u6b4c\u8bcd\u662f\uff1a
\u3000\u3000\u3010Kimi\uff1a\u7238\u7238\u4f60\u4f1a\u4e0d\u4f1a\u5531\u300a\u5c0f\u661f\u661f\u300b\u554a\uff1f
\u3000\u3000\u6797\u5fd7\u9896\uff1a\u4e0d\u4f1a\u554a...Kimi\uff1a\u90a3\u6211\u6559\u4f60\u54e6\uff1f\u6797\u5fd7\u9896\uff1a\u597d\u554a\uff01\u3011
\u3000\u3000\u90a3\u4e48\u6211\u4eec\u5c31\u5728\u97f3\u4e50\u7684\u767e\u5ea6\u8f93\u5165\u6846\u4e2d\u8f93\u5165\u8fd9\u4e9b\u6b4c\u8bcd\u641c\u7d22\u3002
\u3000\u3000\u8fd9\u65f6\u6211\u4eec\u5c31\u4f1a\u5f97\u51fa\u641c\u7d22\u7ed3\u679c\u4e86\uff0c\u4e0d\u8fc7\u6709\u65f6\u5019\u5f97\u51fa\u7684\u6b4c\u66f2\u6bd4\u8f83\u591a\uff0c\u6211\u4eec\u4e00\u4e2a\u4e00\u4e2a\u8fdb\u884c\u8bd5\u542c\u5c31\u77e5\u9053\u4e86\u3002
\u3000\u3000\u70b9\u51fb\u6b4c\u66f2\u540d\u79f0\u4fe1\u606f\u540e\u9762\u7684\u90a3\u4e2a\u64ad\u653e\u6309\u94ae\u5c31\u53ef\u4ee5\u8bd5\u542c\u4e86\uff0c\u8bd5\u542c\u540e\u5c31\u80fd\u77e5\u9053\u662f\u4e0d\u662f\u81ea\u5df1\u8981\u627e\u7684\u6b4c\u4e86\u5427\uff01\uff01
《关于写作》 雷蒙德.卡佛 雷蒙德.卡佛 还是在六十年代中期,我发现我对长篇的叙事小说失去了兴趣。在一段时间里,别说是写,我连读完一篇长篇都感到吃力。我的注意力很难持久,不再有耐心写长篇小说。至于为什么会这样,说来话长,我不想在这儿多罗嗦了。但我知道,这直接导致了我对诗和短篇小说的爱好。进去,出来,不拖延,下一个。也许我在二十大几岁的时候就失去了雄心大志。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倒是件好事了。野心和一点运气对一个作家是有帮助的,但野心太大又碰上运气不好的话,会把一个作家置于死地。另外,没有才华也是不行的。 有些作家有很多才华,我还真不知道一点才华都没有的作家。但是,对事物独特而准确的观察,再用恰当的文字把它表叙出来,则又另当别论了。《加普的世界》其实是欧文(John Irving)自己不可思议的世界。对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而言,存在着另外一个世界。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和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有他们自己的世界。对奇佛(Cheever), 厄普代克(Updike), 辛格(Singer), 埃尔金(Stanley Elkin), 贝蒂(Ann Beattie), 奥齐克(Cynthia Ozick), 巴塞尔姆(Donald Barthelme), 罗宾森(Mary Robison), 基特里奇(William Kittredge), 汉纳(Barry Hannah)和勒奎恩(Ursula K. LeGuin)来说,都存在着一个与他人完全不同的世界。每一个伟大的作家,甚至每一个还可以的作家,都是根据自己的规则来构造世界的。 以上所说的和所谓的风格有点关系,但也不尽然。它像签名一样,是一个作家独特的、不会与他人混淆的东西。它是这个作家的世界,是把一个作家与另一个作家区分开来的东西,与才华无关。这个世界上才华有的是,但一个能持久的作家必须有自己独到的观察事物的方法,并能很艺术地对所观察到的加以叙述。 黛因生(Isak Dinesen)曾说过,她每天写一点。不为所喜,不为所忧。我想有一天我会把这个抄在一张三乘五寸的卡片上,并贴在我写字台正面的墙上。我已在那面墙上贴了些三乘五的卡片,“准确的陈述是写作的第一要素” --庞德(Ezra Pound),就是其中一张。我知道,写作不仅仅是这一点。但如能做到‘准确的陈述’,你的路子起码是走对了。 我墙上还有张三乘五寸的卡片,上面有我从契可夫(Chekov)的一篇小说里摘录的一句话:“...突然,一切都变得清晰起来。”我发现这几个字充满奇妙和可能性。我喜欢它们的简洁以及所暗示的一种启示。另外,它们还带着点神秘色彩。过去不清楚的是什么?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变得清晰了?什么原因?还有个最关键的问题--然后呢?这种突然的清晰必然伴随着结果,我感到一种释然和期待。 我曾无意听到作家沃尔夫(Geoffrey Wolff)对他的学生说:“别耍廉价的花招” 这句话也该写在一张卡片上。我还要更进一步:“别耍花招” 句号。我痛恨花招,在小说中,我一看见花招或小技巧,不管是廉价的还是精心制作的,我都不想再往下看。小手腕使人厌烦,而我又特别容易感到厌烦,这大概和我注意力不能长时间集中有关。和愚蠢的写作一样,那些自以为聪明和时髦夸张的写作也使我昏昏欲睡。作家不需要靠耍花招和卖弄技巧,你没必要是个聪明绝顶的家伙。尽管你有可能被人看成傻子,一个作家要有面对一些简单的事物,比如落日或一只旧鞋子,而惊讶得张口结舌的资质。 几个月前,巴思(John Barth)在纽约时报的书评专栏里曾提到,十年前,参加他写作短训班的学生,大多对‘形式创新’ 着迷。而现在不太一样了。那些自由开放的实验小说不再时髦,他担心八十年代的人又开始写那些老生常谈的小说。每当听见人们在我面前谈论小说的‘形式创新 ’,我总会感到不太自在。你会发现,很多不负责任、愚蠢和模仿他人的写作,常常是以‘实验’为借口的。这种写作往往是对读者的粗暴,使他们和作者产生隔阂。这样的写作不给人们带来与世界有关的任何新信息,只是描述一幅荒凉的景象,几个小沙丘,几只蜥蜴,没有任何人和与人有关的东西。这是个只有少数科学家才会感兴趣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真正的实验小说必须是原创的,它是艰苦劳动的回报。一味地追随和模仿他人对事物的观察方法是徒劳的。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巴塞尔姆,另一个作家如果以‘创新’ 的名义,盗用巴塞尔姆特有的灵感或表达方式,其结果只会是混乱,失败和自欺欺人。真正的实验小说应该是全新的,如庞得所说。而且,不能为创新而创新。如果一个作家还没有走火入魔的话,他的世界和读者的世界是能够沟通的。 在一首诗或一篇短篇小说里,我们完全可以用普通而精准的语言来描述一些普通的事,赋予一些常见的事物,如一张椅子,一扇窗帘,一把叉子,一块石头,或一付耳环以惊人的魔力。纳博科夫(Nabokov)就有这样的本事,用一段看似无关痛痒的对话,让你读后脊背发凉,并感受到一种艺术享受。我对这样的作品才感兴趣。我讨厌杂乱无章的东西,不管它是打着实验小说的旗号还是以现实主义的名义。在巴别尔(Isaac Babel)的那部绝妙的小说《盖 61 德 61 莫泊桑》里,叙述者有这么一段有关小说写作的话:“没有什么能比一个放在恰当位子上的句号更能打动你的心。”这句话同样应该写在一张三乘五的卡片上。 康奈尔(Connell)在谈论小说修改时说,当他开始删除一些逗号,随后又把这些逗号放回原处时,他知道这部小说差不多写完了。我喜欢这种认真的工作方式。我们作为作家,唯一拥有的只是些字和词。只有把它们连同标点符号一起,放在恰当的位子上,才能最好地表达我们想说的东西。如果词句因为作者自己的情绪失控而变得沉重,或由于某种原因而不能够准确,读者的艺术感官就不会被你写的东西所触动,从而无法对它感兴趣。詹姆士(Henry James)称这一类不幸的写作为“微弱的陈述。” 我有朋友曾对我说,因为需要钱,他不得不赶着写完一本书。编辑和老婆都在后面催着呢,说不定哪天就会弃他而去,等等。对自己写得不好的另一个借口是:“如果再花点时间的话,我会写得更好。”当我听见我的一个写长篇的朋友说这句话时,我简直有点目瞪口呆了,直到现在我还有这种感觉。虽然这不关我什么事,但是,在写一部作品时,你如果不把全部的能力都用上,你为什么要写它呢?说到底,一个尽自己最大能力写出的作品,以及因写它而得到的满足感。是我们唯一能够带进棺材里的东西。我想对我的那位朋友说,看在老天的份上,您干点别的什么吧。这个世界上总还有些既容易又能保持诚实的赚钱方法吧。或者,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写,写完就完了,不要找借口,不要抱怨,更不要解释。 在一篇叫做《短篇写作》的文章里,奥康纳把写作比作发现。她说当她准备写一部小说时,常常不知道她到底要写些什么。她怀疑大多数作家在一开始就知道小说的走向。她用《善良的乡村人》这部小说作为例子,来说明她的写作过程。她常常是在小说快写完时才知道该怎样结尾。 ‘我开始写那部小说时,并不知道里面会有一个有一条木腿的博士。有天早上,我在写两个我较熟悉的女人。我给其中的一个安排了一个有条木腿的女儿,我又加了个推销圣经的人物,我当时并不知道他在小说中会干些什么。我不知道他会去偷那条木腿,直到我写了十几行后才有了这个主意。但这个主意一形成,一切都变得那么必然。’ 有一次,我坐下来写最终成为一部很不错的小说。开始,我只有开头的一句话:“当电话铃响起的时候,他正在吸尘。”接下来的几天里,这句话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我知道有一个故事在那儿跃跃欲试,我能从骨子里面感到那句话是一个故事的开头,如果我能有时间,那怕只有十几个小时,我会写出个很好的故事。我终于在一个早上坐了下来,并写下了那句开头。很快,其他句子接踵而至。就像我写诗时那样,一句接着一句。不一会儿,一个短篇就成形了。我知道我终于写出了一个我一直想写的故事。 我喜欢小说里有些恐慌和紧张的气氛,起码它对小说的销售有帮助。好的故事里需要一种紧张的气氛,某件事马上就要发生了,它在一步一步地逼近。小说里的这种气氛,是靠实实在在的词创造出来的一种视觉上的效果。同时,那些没写出来的,暗示性的东西,那些隐藏在平滑(或微微有点起伏)的表层下面的东西,也会起到同样的效果。普里切特(V. S. Pritchett)给短篇小说的定义是:“眼角闪过的一瞥。”请注意这‘一瞥’。先是有‘一瞥’,再给这‘一瞥’赋予生命,,将这‘一瞥’转化成对当前一刻的阐明,如果运气好的话,还能进一步对事情的结果和意义加以延伸。短篇小说家的使命就是充分地利用这‘一瞥’,用智慧和文学手法来展现作者的才华,尺寸感,适度感,以及对外界事物的看法――我强调与众不同的看法。而这一切,是要通过清晰准确的语言的应用来实现的。靠语言赋予细节以生气,使故事生辉。为了让细节具体传神,语言必须精准。为了准确地描述,你甚至可以用一些通俗的词。只要运用得当,它们同样可以起到一字千斤的效果。 <On Writing> Raymond Carver --------------------------- ◎ 雷蒙德·卡佛:你在圣弗兰西斯科做什么? 【七寸】发表于2006-1-3 13:38:01 这件事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它和一对年轻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孩子有关。去年夏季的第一天,他们搬进我那条投递线上的一座房子。我再想到他们,是我拿起上星期的报纸,看见上面一个年轻人的照片,他因为用棒球棍杀死了他妻子和她的男友而被监禁在圣·弗兰西斯科。当然,不是同一个人,只不过他们的胡子让他们看着很像。不过,由于情形十分相似,我想了很多。 我叫亨利·罗宾逊,是邮递员--联邦公民的公务员,我从1947年起干这工作。我一辈子都住在西部,除了战争时在军队服役的那三年。我离婚已经二十年了,有两个孩子,也几乎有二十年没见过面了。我不是个轻薄的人,平心而论,我也不是个严肃的人。我的信条是:一个男人在现在这个时代就该二者兼备。我还相信工作的价值--越辛苦越好。不工作的人时间充裕,因此就会有太多的时间沉溺于自己和自己的烦恼。 我相信这一点,部分由于住这儿的一个年轻人--他就不工作。不过我认为她也有责任,--那女人,她纵容了他。 "夸掉的一代"--我想你们如果见了他们就会这样叫他们的。那男的下巴上长着密密麻麻的褐色胡髭,好像他急需坐下来好好吃顿饭,再抽根烟。那女的挺迷人,一头长长的黑发,皮肤细润,一看就知道是个美人。不过请记住我的话,她可不是个贤妻良母。她是个画家。那年轻人,我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可能也干这行。他们两个人都不工作,但他们付房租,而且也能勉勉强强过下去--至少那个夏天是这样。 我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一个星期六的上午,十一点左右,十一点一刻。我已经跑完我那条邮线三分之二,到他们房前,发现院里停着一辆福特56轿车,后面一辆U型拖车正敞着门。松树街上只有三栋住宅,他们是最后一户,另外还有默契森一家--他们来阿卡塔快一年了,格兰特一家--他们住这儿快两年了。默契森在辛普森·瑞德伍德公司工作,吉恩·格兰特是邓尼公司的早班厨师。两所住宅,先开始是空地,是属于科尔家的,后来盖成了住宅。 那年轻人站在院中那辆拖车的后面。她正打前门走出来,嘴上叼着烟,穿一条紧身白色牛仔裤和一件男式白汗衫。她看见我,就站住,停在那儿看我从便道上走过去。尽管我拿着他们的信箱,我还是放慢脚步,朝她点点头。 "收拾妥当了吗?"我问。 "快了,"她说,把额前一缕头发撩开一边仍继续抽着烟。 "这很好,"我说,"欢迎你们到阿卡塔来。" 说完这话,我感到有些窘迫。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在这个女人旁边,都发现自己很窘迫。这也是让我从一开始就反感她的原因之一。 她对我淡淡一笑,我转身要走,那年轻人--他名叫马斯顿--从那辆拖车后面走过来,手里提着一大纸盒玩具。现在,阿卡塔不是个小镇了,倒也不是什么大城市,尽管我想你可能不得不说它还是属于小镇之列。可无论如何,阿卡塔不是世界末日,大多数住在这儿的人不是在锯木场干活,就是和渔业打交道,再不然就是在商业区的某家商店里工作。这儿的人不习惯看见男人留胡子--或留胡子而不做工。 "你好,"我说。当他把纸盒放在前挡泥板上,我伸出手。"我叫亨利·罗宾逊。你们刚到是吗? "昨天下午,"他说。 "这趟旅行真够受的!从圣·弗兰西斯科到这儿用了14个小时,"那女人在走廊上说道。 "他妈的拉住那辆拖车。" "我来吧,我来吧,"我边说,还边摇着头。"圣·弗兰西斯科?我刚还在圣·弗兰西斯科呆过。让我想想,是去年四月或三月。" "是吗?"她说,"你到圣·弗兰西斯科做什么?" "噢,不做什么,真的。每年我都要去一两趟。到渔夫码头走走,或看看巨人戏剧。就这些。" 片刻的停顿。马斯顿在草地里寻找着什么。我准备走了。就在这时,孩子们从前门飞跑过来,吵吵嚷嚷地狂奔到走廊尽头。当那扇屏风门哐地一声打开时,我想马斯顿一定吃了一惊,而她只是抱着胳膊站在那儿,十分冷静,脸眼睛都没眨一下。他看上去很糟糕。每次他准备做点儿什么,总会快速地痉挛一下。他的眼睛--一会儿盯着你,一会儿滑向一边,一会儿又盯住你。 那边有三个孩子,两个四、五岁左右的卷头发的小姑娘,还有一个小点儿的男孩儿紧跟在后面。 "可爱的孩子,"我说,"好吧,我要走了。你们得换换这信箱上的名字吧。" "当然,"他说,"当然。一两天内我就换过来。不过最近我们不会有什么信的。" "你不知道,"我说,"你不知道这只老邮袋里会钻出个什么来。准备准备无碍的。"我转身正要走。"对了,如果你想到工厂找活儿干,我可以告诉你到辛普森·瑞德伍德公司找谁。我的一个朋友是那儿的领班。他可能有。。。。。。"我发现他们不太感兴趣,声音 就低下来。 "不必了,谢谢。"他说。 "他不用找工作,"她插话道。 "那好吧。再见。" "再见,"马斯顿说。 她再没说什么。 我刚才说过,那天是星期六,烈士纪念日的前一天。我们星期一休息,直到星期二,我才又去那儿。见那台U型拖车还在前院,我并不吃惊。不过,他还没卸完车却挺让我吃惊的。我得说,有四分之一的东西已经搬到前廊上--一把装满东西的椅子,一把明黄色的餐椅以及一大纸盒的衣服,有些还耷拉在纸盒外面。另有四分之一的东西一定已经搬进房了,其余的都还在拖车里呆着呢。孩子们正拿着小木棍,敲打拖车的车帮,还从尾门那儿爬上爬下。他们的妈妈和爸爸却连影子也看不见。 星期四我又在院子里看见他,提醒他别忘换信箱的名字。 "我正准备换呢,"他说。 "抓紧时间,"我说,"搬到一个新地方,总有好多事要操心。原来住这儿的人,科尔一家,你来的两天前才搬出去。他要到尤瑞卡工作。给一家捕鱼和猎兽公司干。" 马斯顿摸摸胡子,眼睛看着别处,好像在想什么事。 "再见吧,"我说。 "再见。" 总之,他还是没换信箱上的名字。不久我又来过,带来一封写着那个地址的信,他说了句:"马斯顿?是的,是我们的,马斯顿。。。。。。这几天我就把信箱上的名字换了。我得找一桶油漆,把那个名字。。。。。。科尔,把科尔涂掉。"他的眼睛一直东张西望。然后他从眼角斜视着我,敲了敲下巴。但他还是没更换信箱上的名字。过了一阵儿,我也就耸耸肩,忘了这回事。 人们听到了一些传言。我不止一次地听说他是个被假释的囚犯;他到阿卡塔来是为了摆脱圣·弗兰西斯科不健康的环境。据这种传说讲,那女人是他妻子,但那几个孩子却没一个是他的。另一种说法是,他犯了罪,在这儿隐藏。不过没多少人相信这种说法。他看上去不像哪种确实做了什么有罪的事的样子。大多数人看来都相信了那些至少是传得最广的说法,这种说法也是最可怕的。那是说,那女人有毒瘾,她丈夫把她带到这儿,是要帮助她戒掉恶习。作为旁证,萨莉·威尔逊的来访总是被提起--萨莉·威尔逊是从"旅行车招待站"来的。一天下午,她碰巧拜访了他们家。后来她说,不是瞎说,那儿确实有些很有意思的事--尤其那女人。刚刚那女人还坐在那儿听萨莉说个不停--似乎是全神贯注--不久她就站起身,尽管萨莉还在说话,她竟开始画她的画,好像萨莉根本不在那儿一样。同样地,她刚刚还抚摩亲吻着孩子们,一会儿突然就开始对他们大喊大叫,而且没有任何理由。萨莉还说,如果你离她很近,就会发现她眼睛看人的方式也很特别。不过,萨莉·威尔逊在"旅行车招待站"的掩护下,干了不少年管闲事、打探人家秘密 的事。 "你不明白,"碰上谁提这事,我就说,"如果他现在就去工作的话,谁还会说什么呢?"同样,依我看,他们在圣·弗兰西斯科也招惹了不少麻烦,不管那麻烦的性质如何,他们是想从那些麻烦中摆脱出来。不过他们为什么挑上来阿卡塔安家,就很难说了;因为他们肯定不是来找工作的。最初的几个星期,根本谈不上有什么邮件,只有几张《老年》、《西部汽车》之类的订 报单。而后开始有信来了,大概一周一两封的样子。我来时,有时能看见他们中的一个在屋外散步,有时则见不到任何人。不过孩子们倒是总在那儿,屋里屋外的跑出跑进,又在旁边的一块空地上玩耍。当然,不可能一开始就是模范家庭;可他们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以后,草开始发芽了,可那是什么草啊,又枯又黄。谁也不会愿意看见这种东西的。我知道杰西老头来过一两次给它们浇浇水,而他们却说买不到水管。于是他给他们留了一根。后来我发现孩子们拿着那根管子在院子里玩儿,它的结局就是这样。有两次我看见一辆白色的小运动车停在房前,那车不是从这附近开来的。 我和那女人直接打交道只有一次。有一封信欠资,我就带着信走到她家门口。两个女孩子中的一个让我进去,然后跑去找她妈妈。屋里堆满了零零散散的旧家具,衣服也扔得到处都是,只是还不至说很脏。可能不够整齐,但不是脏。起居室里,一把旧躺椅和一把扶手椅靠墙摆着。窗户下有一只用砖和木板搭成的书箱,里面塞满了平装书。犄角处,堆着许多画,都反扣着,另一侧有一幅画还搁在画架上,上面盖着布。我把邮袋换了肩,想站得更稳些;不过我开始觉得还不如我自己付了那笔钱呢。我一边等一边看着那画架,正想侧身走过去掀掉盖布看看,这时我听见了脚步声。 "我能帮你什么忙?"她说道,人出现在门厅里,一点儿也不友好。 我碰了碰帽檐,说道:"如果你不介意,这儿有封欠资的信。" "让我看看。谁来的?噢,是杰!这个傻瓜。给我们寄了封没邮票的信。利!"她叫道。 "杰瑞来信了!"马斯顿走进来,不过他看上去不是很高兴。我等在那儿,两条腿换着站。 "我来付钱,"她说,"看在老杰瑞来信的分上。给。再见。" 就是那种样子--可以说根本没什么样子。我不能说这附近的人已经习惯了他们--他们不是那种你能真正适应的人。不过过了一阵,没人再注意他们了。如果人们在塞夫威超市碰上他推着货车,可能会瞧瞧他的胡子,除此之外就不会注意他什么了。再也听不到别的故事了。 有一天他们消失了。向两个方向。后来我发现一星期前她和一个人--一个男的--先离开了,过了几天,他带着孩子们去了瑞汀,他母亲家。从星期四到第二周星期三的六天里,他们的邮件就呆在信箱里。窗帘全挂着,没人确切知道他们是否把它打开过。但那个星期三,我看见那辆福特车又停在院中,窗帘仍挂着,但邮件没了。 从第二天起,他每天都呆在信箱边等着我把信递给他,要不 他就坐在前廊的楼梯上抽烟,很显然,他是在等什么。他一看见我来,就站起身来掸掸屁股上的裤子,朝信箱这边走过来。如果我有邮件给他,他发现我几乎还没递给他,他的目光就已经急不可待地扫到了发信人的地址。我们很少交谈,哪怕是一句话;如果我们恰巧目光相遇,也只是彼此点点头,可连这种时候都很少。他很痛苦--谁都能看出来--如果我能,我真想帮帮这孩子,但我又不知说什么才好。 大约是他走回来一星期后的一个早晨,我看见他双手插在后兜里,在信箱前走来走去,我下决心跟他说点什么。说什么,我还不知道,但我肯定会说点儿什么。我走上便道时,他的背正对着我。我走近他时,他猛然转过身,他脸上的表情使我要说的话僵住了。 我手中拿着他的邮件立在那儿。他朝我跑了两步,我把它递过去,看也没看。他盯着它像在发楞。 "占有人,"他说。 那时洛杉矶寄来的一份医疗保险计划的广告单,那天上午我至少投送了七十五张。他把它对叠起来,走回屋去。 第二天,他又在外面等。他脸上的表情老成了,好像比前一天能自制多了。这一次我有种预感,我带来了他正盼着的东西。那天早晨在邮站装邮袋的时候,我仔细看过了那封信。那是个普通的信封,地址是一个女人手写的花体字,占去了大半个封皮。邮戳是波特兰的,发信人地址上有姓名的缩写JD和波特兰街区的地址。 "早上好,"我说,把信拿出来。 他一言不发地从我手上接过信,脸刷地就白了。他摇晃了一下,然后朝屋里走去,冲着光举着那封信。 我大叫道:"孩子,她不是好人。我一见到她就敢断定。为什么你不忘了她?为什么你不去工作而忘了她?我当年处在你这种境地时,是工作,白天黑夜的工作,让我忘掉一切的;那会儿正打仗,我在。。。。。。"打那以后,他不再在外面等我了,他在那儿只是再呆了五天。每天,我都能瞥见他仍在等我,不过是站在窗后,透过窗帘向我张望。我走以后他才出来,我能听见屏风门的响声。如果我回头看看,他就显出不紧不慢的样子,朝信箱走去。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他正站在窗户边,神情平静、安闲。窗帘都放了下来,百叶窗收起来,我当时就看出他收拾好东西要离开。不过,从他的脸色我能看出,他这次不是在等我。他的目光扫过我,越过我,落在了南方的房顶和树上。甚至当我离开了房子,又走下便道以后,他仍然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回头望了望。我能看见他仍呆在窗边。那种感觉是那么强烈,我只能转过身去,顺着他的目光的那个方向望过去。不过,正像你能猜到的,除了还是那片古老的森林、山峦、天空外,我什么也没看见。 第二天他就走了。他没有留下任何转投的地址。时而还会有些邮件,是寄给他或他妻子或他们两人的。如果是甲级邮件,我们就保留一天,然后退还寄信人。不是很多。而我也不在意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工作,而我总是高兴有事做。 ------------------------------------ 雷蒙德·卡佛:我父亲的一生 译:丁丽英 我爹名叫克利夫·雷蒙德·卡弗。家里人都叫他雷蒙德,朋友则叫他克利夫·雷蒙德。而我的名字却是小雷蒙德·克利夫·卡弗。我讨厌那个“小”字。在我小时候,爹总是管我叫弗罗格,那倒不错。可后来,他也开始像家里人那样,叫我小雷蒙德了。这样叫,一直叫到我十三四岁,那时我就扬言说了,谁要再这么叫我,就不睬他,爹只好改叫我道克。从此,直到他1967年6月17日去世,他都叫我道克,要么管我叫儿子。 爹死了,母亲打电话来报丧,是我妻子接的电话,当时我不在家,正打算一边工作一边到尹阿华大学的图书馆管理系就读。妻子一拿起电话,母亲就脱口而出:“雷蒙德死了!”一瞬间,妻子以为是我死了,后来母亲才讲清楚自己指的是谁,妻子便说:“感谢上帝,我还以为是我的雷蒙德呐!” 1934年他离开阿肯色去华盛顿州找工作,一路步行,搭便车,还要乘坐载货列车的空车厢,我不知道是否有一个梦想在推动他。我很怀疑。我觉得他并没有什么梦想,他上华盛顿州,只不过为了找一份待遇不错的稳定工作。稳定的工作,才是有意义的工作。他摘了一段时间苹果后,才在大峡谷水坝找到一份建筑工人的体力活,安顿下来。然后,存了一小笔钱买了一辆车,开回阿肯色去帮他的家人,我的祖父祖母搬家,举家迁往西部。他后来说,他们在原来的地方差不多要饿死了,这可不是瞎说的。也就在他回到阿肯色,那个镇叫利昂纳,很短的一段时间内,遇到了我母亲。他们是在人行道旁遇见的,那时他刚从一家小酒店出来。 “他是个酒鬼,”母亲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听他说话。他的眼睛一闪一闪的。如果当时我有一颗水晶球就好了。”他们曾在一年前或别的时候的一次舞会上见过。母亲告诉我,他在她之前有过女朋友。“你父亲总是有女朋友的,甚至在我们结婚以后也有。而他是我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我从来没有其他男人。我也没有失去过什么。” 就在他们去华盛顿州的当天,一个治安法官为他们举行了婚礼,于是,这个高高大大的乡村姑娘,和原来的农场工人,现在的建筑工人结了婚。新婚之夜,我母亲是在阿肯色公路旁的帐篷里,和我父亲家的人一起度过的。 在华盛顿州的奥马克,我父母住的地方比窝棚大不了多少。祖父母住在隔壁。爹仍然在水坝工作,后来,巨大的涡轮机发出了电,并途经几百英里,把水倒灌进加拿大,弗兰克林·罗斯福来建筑工地演讲,当时爹就站在人群中听。我爹说:“他一句也没提为了造水坝而死去的人。”他有几个朋友死在那里,他们有的来自阿肯色,有的来自俄克拉荷马,有的来自密苏里。 然后,他在克拉斯卡宁的锯木厂里找了一份工作,那个小镇在俄勒冈州,紧靠着哥伦比亚河。我就是在那儿出生的,母亲还保留着一张照片,上面,我爹自豪地抱着我,站在那家工厂的门前,脸冲着镜头。我的帽子歪斜着,差不多快要掉下来了,而我爹反戴着帽子,帽檐向后,正咧开嘴大笑。他是去上班,还是已经下了班?看来都不重要了,反正他有一份工作,还有一个家庭,这就是他血气方刚的青年时代。 1941年,我们搬到华盛顿州的雅基马,爹找到的活儿是当锯木工,锯木工的技术还是在克拉斯卡宁时学会的。战争爆发后,并没有叫他去服役,因为他的工作对战争来说十分重要。军队需要加工好的木材,他就把自己的锯条弄得非常锋利,甚至能锯掉你手臂上的汗毛。
缇庡浗鍗鏃ч噾灞鏃呮父鏅偣浠嬬粛 鏃ч噾灞辨梾娓告櫙鐐硅缁嗕粙缁
绛旓細缇庡浗鏃ч噾灞鏈钁楀悕鐨勪簲澶ф梾娓告櫙鐐规槸浠涔 缇庡浗鏃ч噾灞辨槸钁楀悕鐨勬梾娓稿煄甯,涓夐潰鐜按,鏅壊浼樼編,鐜浼樼編,鏄竴搴у北鍩,鑰屼笖姘斿欏啲鏆栧鍑,闃冲厜鍏呰冻,琚獕涓衡滄渶鍙楃編鍥戒汉娆㈣繋鐨勫煄甯傗濄傛瘡骞撮兘鏈夋暟浠ヤ竾璁$殑涓栫晫鍚勫浗鐨勬父瀹㈠幓鏃ч噾灞辨梾娓,鍘绘棫閲戝北鏃呮父杩樻湁涓嶅彲閿欒繃鐨勪簲澶ц憲鍚嶇殑鏃呮父鏅偣,鎮鐭ラ亾鏈夊摢鍑犱釜鍚? 1銆侀噾闂ㄥぇ妗 閲戦棬澶фˉ鏄...
浜烘暀鐗堜節骞寸骇鑻辫unit5鐭ヨ瘑鐐
绛旓細鏃犺浣犱拱浠涔,浣犱細璁や负閭d簺浜у搧鏄湪閭d簺鍥藉鍒堕犵殑銆 4. The international kite festival is held in April every year. 鍥介檯椋庣瓭鑺傛槸鍦ㄦ瘡骞寸殑鍥涙湀涓捐銆5. Laura didn鈥檛 know that kite flying could be so exciting.鍔虫媺涓嶇煡閬撴斁椋為绛濆彲鑳戒細濡傛浠や汉鍏村銆 浜烘暀鐗堜節骞寸骇鑻辫unit5 璇嶆眹绮捐 1. everyday...
杩囧害鏀句换瀛╁瓙鐨勪緥瀛
绛旓細涓哄瀛愯兘鍒楀叆浼樼瓑鐢熻屾枟浜,浠ヤ究涓轰粬杩涘叆甯告槬钘ゅ悕鏍¢摵璺湁浠涔閿欏憿?瀹堕暱浠繀椤昏嚜宸辨巶閲忚繖浜涗簨鎯,浣嗘垜鍙互纭畾鍦板憡璇変綘浠斺旂壒鏉冣斺斿皢浼氫娇浣犵殑瀛╁瓙鍙楀埌浼ゅ銆 棣栧厛涓涓嵄瀹虫槸瀛╁瓙涓嶅啀鐩镐俊浣犲拰浣犵殑璧炴壃,澶氭暟瀛╁瓙寰堟竻妤氫簨瀹炴槸鎬庝箞鍥炰簨銆備粬浠氬父鐭ラ亾鑷繁鍜屽悓榫勪汉鐩告瘮宸窛鍦ㄥ摢閲屻傚効绔ュ皧鏁佷俊浠昏瀹炶瘽鐨勫ぇ浜,浠栦滑鏈変竴绉...
宸存嬁椹煄鏈鍝簺璁╀綘鍗拌薄娣卞埢鐨勬櫙鐐?
绛旓細宸存嬁椹浗瀹跺墽闄紙Teatro Nacional de Panama锛夛細杩欏骇瀹忎紵鐨勫墽闄㈠缓浜20涓栫邯鍒濓紝鏄反鎷块┈鏈閲嶈鐨勬枃鍖栧満鎵涔嬩竴銆傚墽闄㈢殑寤虹瓚椋庢牸铻嶅悎浜嗘柊鍙ゅ吀涓讳箟鍜屽反娲涘厠鍏冪礌锛屽唴閮ㄨ楗板崕涓斤紝鎷ユ湁涓娴佺殑闊冲搷鏁堟灉銆傚湪杩欓噷锛屼綘鍙互娆h祻鍒板悇绉嶉煶涔愪細銆佹垙鍓у拰鑸炶箞琛ㄦ紨銆鍦e紬鏈楄タ鏂鏁欏爞锛圛glesia de San Francisco锛夛細杩欏骇鍝ョ壒寮忔暀鍫...
缈昏瘧,ENG---CHN
绛旓細绗4瀛f槑鏄撅紝浣犺涔版槬瑁咃紝澶忚锛屽啲瑁呫備笉涔犳儻鐨勪汉瀹规槗鐢熺梾鐨勶紒鏉冨埄銆傚濡圭幇鍦ㄦ槸浣忓湪鏃ч噾灞Francisco.And鏄潪甯稿瘨鍐穞here.And鏈夋椂鎰熷埌闈炲父lonely.Foods鍜屼汉姘戜箣闂寸殑鍏崇郴浜烘皯鏈夊緢澶х殑涓嶅悓Myanmar.Sister蹇呴』鍋氱殑宸ヤ綔锛屽苟鍦ㄥ悓涓鏃堕棿瀛︿範University.And濮愬娌℃湁鑷繁鐨勭數鑴戜笂鍐欎俊缁欎綘寮熷紵always.I璁や负鍙互鍘熻皡me.And...
鐣呮父缇庡埄鍧,甯︿綘浜嗚В缇庡浗鍗佸ぇ鍩庡競,浣犳渶鎯冲幓鐨勬槸鍝釜鍩庡競
绛旓細鐣呮父缇庡埄鍧,甯︿綘浜嗚В缇庡浗鍗佸ぇ鍩庡競,浣犳渶鎯冲幓鐨勬槸鍝釜鍩庡競绗崄鍚:浜氱壒鍏板ぇ浜氱壒鍏板ぇ浣嶄簬缇庡浗涓滈儴,鍧愯惤鍦ㄦ捣鎷350绫崇殑闃垮反鎷夊浜氬北楹撶殑鍙板湴涓,鏄編鍥戒笁澶ч珮鍦板煄甯備箣涓,鏄瘜灏旈】鍘跨殑鍘挎斂搴滈┗鍦,鏄編鍥界9澶ч兘甯傚尯,
钀ㄥ皵鐡﹀鏈鍝簺璁╀綘鍗拌薄娣卞埢鐨勬櫙鐐?
绛旓細绉戣儭鐗规媺鍙ゅ煄锛圝oya de Cer茅n锛夛細杩欎釜鑰冨彜閬楀潃琚涓烘槸涓編娲叉渶閲嶈鐨勮冨彜鍙戠幇涔嬩竴銆傚畠灞曠ず浜嗕竴涓彜浠g帥闆呮潙搴勭殑鐢熸椿鍦烘櫙锛屽寘鎷埧灞嬨侀櫠鍣ㄥ拰鍏朵粬鐢熸椿鐢ㄥ搧銆傛父瀹㈠彲浠ュ湪杩欓噷鎰熷彈鍒板彜鐜涢泤鏂囨槑鐨勯瓍鍔涖鍦e紬鏈楄タ鏂鏁欏爞锛圛glesia y Convento de San Francisco锛夛細杩欏骇鏁欏爞浣嶄簬鍦h惃灏旂摝澶氬競涓績锛屾槸涓搴у巻鍙叉偁涔呯殑...
鐣呮父缇庡埄鍧,甯︿綘浜嗚В缇庡浗鍗佸ぇ鍩庡競,浣犳渶鎯冲幓鐨勬槸鍝釜鍩庡競
绛旓細浜氱壒鍏板ぇ(Atlanta)浣嶄簬缇庡浗涓滈儴,鍧愯惤鍦ㄦ捣鎷350绫崇殑闃垮反鎷夊浜氬北楹撶殑鍙板湴涓,鏄編鍥戒笁澶ч珮鍦板煄甯備箣涓,鏄瘜灏旈】鍘跨殑鍘挎斂搴滈┗鍦,鏄編鍥界9澶ч兘甯傚尯,浜︽槸缇庡浗浣愭不浜氬窞棣栧簻鍜屾渶澶х殑宸ュ晢涓氬煄甯傘備綔涓轰竴涓搧璺灑绾,浜氱壒鍏板ぇ鐨勫彂灞曞浜19涓栫邯鏃╂湡銆20涓栫邯,瀹冩槸缇庡浗姘戞潈杩愬姩鐨勪腑蹇,骞朵妇鍔炰簡1996骞村瀛eゥ鏋楀尮鍏嬭繍鍔ㄤ細銆備簹鐗瑰叞澶ф槸...
缇庡浗钁楀悕鐨勫煄甯傛湁鍝簺
绛旓細闂涓:缇庡浗鏈鍝簺钁楀悕鐨勫煄甯? 缇庡浗钁楀悕鐨勫煄甯傛湁:绾界害(涓栫晫閲戣瀺涓績),鍗庣洓椤(缇庡浗棣栭兘),娲涙潐鐭(濂借幈鍧炵數褰变箣鍩),鑺濆姞鍝(浠呮绾界害鐨勭浜屽ぇ鍩庡競),浜氱壒鍏板ぇ(濂ヨ繍浼氫妇鍔炲湴),鏃ч噾灞(娌挎捣鏃呮父澶у煄),浼戞柉椤(鑸ぉ涔嬪煄),鎷夋柉缁村姞鏂(涓栫晫璧屽煄),搴曠壒寰(姹借溅鍩),杩樻湁璐瑰煄銆佽繄闃垮瘑銆佸湥璺槗鏂佹尝澹】,杩欎簺缇庡浗鍩庡競閮芥槸寰堣憲鍚嶇殑...
闀挎矙鍗庤皧鐢靛奖灏忛晣涓冨鑺傛湁浠涔娲诲姩鍚2020
绛旓細8鏈25鏃18:00鍦ㄥ湥寮楁湕瑗挎柉绉鍩庡牎寮鍚紝鏉ュ弬鍔犵殑灏忎紮浼翠滑锛屽彲浠ュ湪鐜板満棰嗗彇褰╄壊鎵嬬幆绾㈣壊=鏈夊璞$豢鑹=鍗曡韩榛勮壊=淇濆瘑娲惧涓婇櫎浜嗘湁鐑荆鐨勬瓕鑸炪佺簿褰╃殑涔愰槦琛ㄦ紨鍦―JSHOW鍚庤繕鍑嗗浜嗚秴澶氭父鎴忕幆鑺傦紝瓒e懗鍔犲嶏紝蹇箰涓嶇疮!鍒繕浜嗕綘鐨勫績鎰垮崱鎶藉绠卞湪鎵嬶紝鍙涓嶆槸鎽樻槦鏄熶笂鏈堢悆浣犵殑蹇冩効璇翠笉瀹氬氨浼氳鎶戒腑瀹炵幇鍝!
扩展阅读:
西斯科机油靠谱吗 ...
电影《弗兰兹》 ...
卡夫丽斯真的能治病吗 ...
伊卡洛斯的坠落的故事 ...
电影《弗朗西斯》 ...
《弗兰西斯》在线观看 ...
奥纳西斯让杰奎琳怀孕 ...
弗兰西斯1982译制片 ...
弗兰西斯 麦克多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