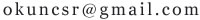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中的一段话 在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中,文末有这样一句话,见下↓
\u60f3\u77e5\u9053\u53f2\u94c1\u751f\u300a\u6211\u4e0e\u5730\u575b\u300b\u4e2d\u7684\u4e00\u53e5\u8bdd\u3002\u5728\u7ebf\u7b49\uff0c"\u8fd9\u6837\u60f3\u4e86\u597d\u51e0\u5e74\uff0c\u6700\u540e\u4e8b\u60c5\u7ec8\u4e8e\u5f04\u660e\u767d\u4e86\uff1a\u4e00\u4e2a\u4eba\uff0c\u51fa\u751f\u4e86\uff0c\u8fd9\u5c31\u4e0d\u518d\u662f\u4e00\u4e2a\u53ef\u4ee5\u8fa9\u8bba\u7684\u95ee\u9898\uff0c\u800c\u53ea\u662f\u4e0a\u5e1d\u4ea4\u7ed9\u4ed6\u7684\u4e00\u4e2a\u4e8b\u5b9e\uff1b\u4e0a\u5e1d\u5728\u4ea4\u7ed9\u6211\u4eec\u8fd9\u4ef6\u4e8b\u5b9e\u7684\u65f6\u5019\uff0c\u5df2\u7ecf\u987a\u4fbf\u4fdd\u8bc1\u4e86\u5b83\u7684\u7ed3\u679c\uff0c\u6240\u4ee5\u6b7b\u662f\u4e00\u4ef6\u4e0d\u5fc5\u6025\u4e8e\u6c42\u6210\u7684\u4e8b\uff0c\u6b7b\u662f\u4e00\u4e2a\u5fc5\u7136\u4f1a\u964d\u4e34\u7684\u8282\u65e5\u3002\u8fd9\u6837\u60f3\u8fc7\u4e4b\u770b\u6211\u5b89\u5fc3\u591a\u4e86\uff0c\u773c\u524d\u7684\u4e00\u5207\u4e0d\u518d\u90a3\u4e48\u53ef\u6015\u3002"
\u662f\u8fd9\u53e5\u5427.
\u662f\u5fc3\u6001\uff0c\u60f3\u6cd5\u4e0d\u540c\u4e86\uff0c\u5c31\u79f0\u4e3a\u4e0d\u662f\u6211\u4e86\uff01
我与地坛我与地坛
史铁生
我与地坛
一
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
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四百多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它不远的地方——五十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它周围,而且是越搬离它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
它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四百多年里,它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圮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
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它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
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它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我在那篇小说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园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过后便沉寂下来。”“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溜荫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撅一杈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蜂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窸窸窣窣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
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呆过。有时候呆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呆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
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一次性能够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所以,十五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它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十五年中,这古园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东西的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它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它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它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了你的时候;譬如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灼烈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事件;譬如秋风忽至,再有一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散着熨帖而微苦的味道。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写只能闻,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所以我常常要到那园子里去。
作者:asahorse 2009-3-7 21:22 回复此发言
--------------------------------------------------------------------------------
2 回复:我与地坛
二
现在我才想到,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
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她知道我心里的苦闷,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呆在家里结果会更糟,但她又担心我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地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母亲知道有些事不宜问,便犹犹豫豫地想问而终于不敢问,因为她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她料想我不会愿意她跟我一同去,所以她从未这样要求过,她知道得给我一点独处的时间,得有这样一段过程。她只是不知道这过程得要多久,和这过程的尽头究竟是什么。每次我要动身时,她便无言地帮我准备,帮助我上了轮椅车,看着我摇车拐出小院;这以后她会怎样,当年我不曾想过。
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想起一件什么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待她再次送我出门的时候,她说:“出去活动活动,去地坛看看书,我说这挺好。”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听出,母亲这话实际上是自我安慰,是暗自的祷告,是给我的提示,是恳求与嘱咐。只是在她猝然去世之后,我才有余暇设想。当我不在家里的那些漫长的时间,她是怎样心神不定坐卧难宁,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现在我可以断定,以她的聪慧和坚忍,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后的黑夜,在那不眠的黑夜后的白天,她思来想去最后准是对自己说:“反正我不能不让他出去,未来的日子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真的要在那园子里出了什么事,这苦难也只好我来承担。”在那段日子里——那是好几年长的一段日子,我想我一定使母亲作过了最坏的准备了,但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你为我想想”。事实上我也真的没为她想过。那时她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她有一个长到二十岁上忽然截瘫了的儿子,这是她唯一的儿子;她情愿截瘫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可这事无法代替;她想,只要儿子能活下去哪怕自己去死呢也行,可她又确信一个人不能仅仅是活着,儿子得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这条路呢,没有谁能保证她的儿子终于能找到。——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
有一次与一个作家朋友聊天,我问他学写作的最初动机是什么?他想了一会说:“为我母亲。为了让她骄傲。”我心里一惊,良久无言。回想自己最初写小说的动机,虽不似这位朋友的那般单纯,但如他一样的愿望我也有,且一经细想,发现这愿望也在全部动机中占了很大比重。这位朋友说:“我的动机太低俗了吧?”我光是摇头,心想低俗并不见得低俗,只怕是这愿望过于天真了。他又说:“我那时真就是想出名,出了名让别人羡慕我母亲。”我想,他比我坦率。我想,他又比我幸福,因为他的母亲还活着。而且我想,他的母亲也比我的母亲运气好,他的母亲没有一个双腿残废的儿子,否则事情就不这么简单。
在我的头一篇小说发表的时候,在我的小说第一次获奖的那些日子里,我真是多么希望我的母亲还活着。我便又不能在家里呆了,又整天整天独自跑到地坛去,心里是没头没尾的沉郁和哀怨,走遍整个园子却怎么也想不通:母亲为什么就不能再多活两年?为什么在她儿子就快要碰撞开一条路的时候,她却忽然熬不住了?莫非她来此世上只是为了替儿子担忧,却不该分享我的一点点快乐?她匆匆离我去时才只有四十九岁呀!有那么一会,我甚至对世界对上帝充满了仇恨和厌恶。后来我在一篇题为“合欢树”的文章中写道:“我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闭上眼睛,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溯的我听见了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似乎得了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小公园,指的也是地坛。
作者:asahorse 2009-3-7 21:23 回复此发言
--------------------------------------------------------------------------------
3 回复:我与地坛
只是到了这时候,纷纭的往事才在我眼前幻现得清晰,母亲的苦难与伟大才在我心中渗透得深彻。上帝的考虑,也许是对的。
摇着轮椅在园中慢慢走,又是雾罩的清晨,又是骄阳高悬的白昼,我只想着一件事:母亲已经不在了。在老柏树旁停下,在草地上在颓墙边停下,又是处处虫鸣的午后,又是鸟儿归巢的傍晚,我心里只默念着一句话: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把椅背放倒,躺下,似睡非睡挨到日没,坐起来,心神恍惚,呆呆地直坐到古祭坛上落满黑暗然后再渐渐浮起月光,心里才有点明白,母亲不能再来这园中找我了。
曾有过好多回,我在这园子里呆得太久了,母亲就来找我。她来找我又不想让我发觉,只要见我还好好地在这园子里,她就悄悄转身回去,我看见过几次她的背影。我也看见过几回她四处张望的情景,她视力不好,端着眼镜像在寻找海上的一条船,她没看见我时我已经看见她了,待我看见她也看见我了我就不去看她,过一会我再抬头看她就又看见她缓缓离去的背影。我单是无法知道有多少回她没有找到我。有一回我坐在矮树丛中,树丛很密,我看见她没有找到我;她一个人在园子里走,走过我的身旁,走过我经常呆的一些地方,步履茫然又急迫。我不知道她已经找了多久还要找多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决意不喊她——但这绝不是小时候的捉迷藏,这也许是出于长大了的男孩子的倔强或羞涩?但这倔只留给我痛侮,丝毫也没有骄傲。我真想告诫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羞涩就更不必,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
儿子想使母亲骄傲,这心情毕竟是太真实了,以致使“想出名”这一声名狼藉的念头也多少改变了一点形象。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且不去管它了罢。随着小说获奖的激动逐日暗淡,我开始相信,至少有一点我是想错了:我用纸笔在报刊上碰撞开的一条路,并不就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年年月月我都到这园子里来,年年月月我都要想,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到底是什么。母亲生前没给我留下过什么隽永的哲言,或要我恪守的教诲,只是在她去世之后,她艰难的命运,坚忍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随光阴流转,在我的印象中愈加鲜明深刻。
有一年,十月的风又翻动起安详的落叶,我在园中读书,听见两个散步的老人说:“没想到这园子有这么大。”我放下书,想,这么大一座园子,要在其中找到她的儿子,母亲走过了多少焦灼的路。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
作者:asahorse 2009-3-7 21:23 回复此发言
--------------------------------------------------------------------------------
4 回复:我与地坛
五
我也没有忘记一个孩子——一个漂亮而不幸的小姑娘。十五年前的那个下午,我第一次到这园子里来就看见了她,那时她大约三岁,蹲在斋宫西边的小路上捡树上掉落的“小灯笼”。那儿有几棵大梨树,春天开一簇簇细小而稠密的黄花,花落了便结出无数如同三片叶子合抱的小灯笼,小灯笼先是绿色,继尔转白,再变黄,成熟了掉落得满地都是。小灯笼精巧得令人爱惜,成年人也不免捡了一个还要捡一个。小姑娘咿咿呀呀地跟自己说着话,一边捡小灯笼;她的嗓音很好,不是她那个年龄所常有的那般尖细,而是很圆润甚或是厚重,也许是因为那个下午园子里太安静了。我奇怪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一个人跑来这园子里?我问她住在哪儿?她随便指一下,就喊她的哥哥,沿墙根一带的茂草之中便站起一个七八岁的男孩,朝我望望,看我不像坏人便对他的妹妹说:“我在这儿呢”,又伏下身去,他在捉什么虫子。他捉到螳螂,蚂蚱,知了和蜻蜒,来取悦他的妹妹。有那么两三年,我经常在那几棵大梨树下见到他们,兄妹俩总是在一起玩,玩得和睦融洽,都渐渐长大了些。之后有很多年没见到他们。我想他们都在学校里吧,小姑娘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必是告别了孩提时光,没有很多机会来这儿玩了。这事很正常,没理由太搁在心上,若不是有一年我又在园中见到他们,肯定就会慢慢把他们忘记。
那是个礼拜日的上午。那是个晴朗而令人心碎的上午,时隔多年,我竟发现那个漂亮的小姑娘原来是个弱智的孩子。我摇着车到那几棵大栾树下去,恰又是遍地落满了小灯笼的季节;当时我正为一篇小说的结尾所苦,既不知为什么要给它那样一个结尾,又不知何以忽然不想让它有那样一个结尾,于是从家里跑出来,想依靠着园中的镇静,看看是否应该把那篇小说放弃。我刚刚把车停下,就见前面不远处有几个人在戏耍一个少女,作出怪样子来吓她,又喊又笑地追逐她拦截她,少女在几棵大树间惊惶地东跑西躲,却不松手揪卷在怀里的裙裾,两条腿袒露着也似毫无察觉。我看出少女的智力是有些缺陷,却还没看出她是谁。我正要驱车上前为少女解围,就见远处飞快地骑车来了个小伙子,于是那几个戏耍少女的家伙望风而逃。小伙子把自行车支在少女近旁,怒目望着那几个四散逃窜的家伙,一声不吭喘着粗气。脸色如暴雨前的天空一样一会比一会苍白。这时我认出了他们,小伙子和少女就是当年那对小兄妹。我几乎是在心里惊叫了一声,或者是哀号。世上的事常常使上帝的居心变得可疑。小伙子向他的妹妹走去。少女松开了手,裙裾随之垂落了下来,很多很多她捡的小灯笼便洒落了一地,铺散在她脚下。她仍然算得漂亮,但双眸迟滞没有光彩。她呆呆地望那群跑散的家伙,望着极目之处的空寂,凭她的智力绝不可能把这个世界想明白吧?大树下,破碎的阳光星星点点,风把遍地的小灯笼吹得滚动,仿佛暗哑地响着无数小铃铛。哥哥把妹妹扶上自行车后座,带着她无言地回家去了。
无言是对的。要是上帝把漂亮和弱智这两样东西都给了这个小姑娘,就只有无言和回家去是对的。
谁又能把这世界想个明白呢?世上的很多事是不堪说的。你可以抱怨上帝何以要降请多苦难给这人间,你也可以为消灭种种苦难而奋斗,并为此享有崇高与骄傲,但只要你再多想一步你就会坠人深深的迷茫了: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么?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幸运?要是没有了恶劣和卑下,善良与高尚又将如何界定自己又如何成为美德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会否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腻烦和乏味呢?我常梦想着在人间彻底消灭残疾,但可以相信,那时将由患病者代替残疾人去承担同样的苦难。如果能够把疾病也全数消灭,那么这份苦难又将由(比如说)相貌丑陋的人去承担了。就算我们连丑陋,连愚昧和卑鄙和一切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和行为,也都可以统统消灭掉,所有的人都一样健康、漂亮、聪慧、高尚,结果会怎样呢?怕是人间的剧目就全要收场了,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条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
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看来上帝又一次对了。
于是就有一个最令人绝望的结论等在这里: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又有谁去体现这世间的幸福,骄傲和快乐?只好听凭偶然,是没有道理好讲的。
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
那么,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
设若智慧的悟性可以引领我们去找到救赎之路,难道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这样的智慧和悟性吗?
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氓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
作者:asahorse 2009-3-7 21:27 回复此发言
--------------------------------------------------------------------------------
5 回复:我与地坛
七
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它们不能变成语言,它们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它们了。它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它们的领地只有两处:心与坟墓。比如说邮票,有些是用于寄信的,有些仅仅是为了收藏。
如今我摇着车在这园子里慢慢走,常常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一个人跑出来已经玩得太久了。有—天我整理我的旧像册,一张十几年前我在这圈子里照的照片—一那个年轻人坐在轮椅上,背后是一棵老柏树,再远处就是那座古祭坛。我便到园子里去找那棵树。我按着照片上的背景找很快就找到了它,按着照片上它枝干的形状找,肯定那就是它。但是它已经死了,而且在它身上缠绕着一条碗口粗的藤萝。有一天我在这园子碰见一个老太太,她说:“哟,你还在这儿哪?”她问我:“你母亲还好吗?”“您是谁?”“你不记得我,我可记得你。有一回你母亲来这儿找你,她问我您看没看见一个摇轮椅的孩子?……”我忽然觉得,我一个人跑到这世界上来真是玩得太久了。有一天夜晚,我独自坐在祭坛边的路灯下看书,忽然从那漆黑的祭坛里传出—阵阵唢呐声;四周都是参天古树,方形祭坛占地几百平米空旷坦荡独对苍天,我看不见那个吹唢呐的人,唯唢呐声在星光寥寥的夜空里低吟高唱,时而悲怆时而欢快,时面缠绵时而苍凉,或许这几个词都不足以形容它,我清清醒醒地听出它响在过去,响在现在,响在未来,回旋飘转亘古不散。
必有一天,我会听见喊我回去。
那时您可以想象—个孩子,他玩累了可他还没玩够呢。心里好些新奇的念头甚至等不及到明天。也可以想象是一个老人,无可质疑地走向他的安息地,走得任劳任怨。还可以想象一对热恋中的情人,互相一次次说“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又互相一次次说“时间已经不早了”,时间不早了可我—刻也不想离开你,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可时间毕竟是不早了。
我说不好我想不想回去。我说不好是想还是不想,还是无所谓。我说不好我是像那个孩子,还是像那个老人,还是像一个热恋中的情人。很可能是这样:我同时是他们三个。我来的时候是个孩子,他有那么多孩子气的念头所以才哭着喊着闹着要来,他一来一见到这个世界便立刻成了不要命的情人,而对一个情人来说,不管多么漫长的时光也是稍纵即逝,那时他便明白,每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
但是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辉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
当然,那不是我。
但是,那不是我吗?
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
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氓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
http://baike.baidu.com/view/344077.html?wtp=tt
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氓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
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氓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
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氓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
绛旓細1銆佸厛鍒幓姝伙紝鍐嶈瘯鐫娲讳竴娲荤湅銆傝祻鏋愶細浜哄缁堣蹇冩甯屾湜锛屽彧瑕佸績搴曟湁鍧氭寔锛岄偅涔堢敓娲诲氨鏈夋棤闄愬鐨勫彲鑳姐2銆佹鏄竴浠舵棤椤讳箮鐫鎬ュ幓鍋氱殑浜嬶紝鏄竴浠舵棤璁烘庢牱鑰芥悂涔熶笉浼氶敊杩囦簡鐨勪簨锛屼竴涓繀鐒朵細闄嶄复鐨勮妭鏃ャ傝祻鏋愶細杩欐槸涓涓湪鍥板褰撲腑鐨勪汉瀵规浜$殑鐞嗚В锛屾垜瑙夊緱鏄潪甯告繁鍒荤殑锛岀敓涓庢瀵逛汉涓涓汉鏉ヨ锛屼粠鏉...
绛旓細4.涓鍒讳篃涓嶆兂绂诲紑浣鈥濓紝鍙堜簰鐩镐竴娆℃璇粹滄椂闂村凡缁忎笉鏃╀簡鈥濓紝鏃堕棿涓嶆棭浜嗗彲鎴戜竴鍒讳篃涓嶆兂绂诲紑浣狅紝涓鍒讳篃涓嶆兂绂诲紑浣犲彲鏃堕棿姣曠珶鏄笉鏃╀簡銆鎴戣涓嶅ソ鎴戞兂涓嶆兂鍥炲幓銆鎴戣涓嶅ソ鏄兂杩樻槸涓嶆兂锛岃繕鏄棤鎵璋撱傛垜璇翠笉濂芥垜鏄儚閭d釜瀛╁瓙锛岃繕鏄儚閭d釜鑰佷汉锛岃繕鏄儚涓涓儹鎭嬩腑鐨勬儏浜恒傚緢鍙兘鏄繖鏍凤細鎴戝悓鏃舵槸浠栦滑涓変釜...
绛旓細鍋囧涓栫晫涓婃病鏈変簡鑻﹂毦 涓栫晫杩樿兘鏈変粈涔 瑕佹槸娌℃湁鎰氶挐 鏈烘櫤杩樻湁浠涔堝厜鑽e憿 瑕佹槸娌℃湁浜嗕笐闄 婕備寒鍙堟庝箞缁寸郴鑷繁鐨勫垢杩愬憿 瑕佹槸娌℃湁鎭跺姡鍜鍗戜笅 鍠勮壇涓庨珮灏氬張灏嗗浣曞浣曠晫瀹氳嚜宸卞浣曟垚涓虹編寰峰憿 瑕佹槸娌℃湁浜嗘畫鐤 鍋ュ叏鏄惁鍥犲徃绌鸿鎯屽彉寰楄吇鐑﹀拰涔忓懗鍛 鎴戝父姊︽兂鐫鍦ㄤ汉闂村交搴曟秷鐏畫鐤 浣嗗彲浠ョ浉淇 閭f椂灏嗙敱鎮g梾...
绛旓細1.涓涓汉锛屽嚭鐢熶簡锛岃繖灏变笉鍐嶆槸涓涓彲浠ヨ京璁虹殑闂锛岃屽彧鏄笂甯濅氦缁欎粬鐨勪竴涓簨瀹锛涗笂甯濆湪浜ょ粰鎴戜滑杩欎欢浜嬪疄鐨勬椂鍊欙紝宸茬粡椤轰究淇濊瘉浜嗗畠鐨勭粨鏋滐紝鎵浠ユ鏄竴浠朵笉蹇呮ヤ簬姹傛垚鐨勪簨锛屾鏄竴涓繀鐒朵細闄嶄复鐨勮妭鏃ャ2.澶氬勾鏉ユ垜澶翠竴娆℃剰璇嗗埌锛岃繖鍥腑涓嶅崟鏄澶勯兘鏈夎繃鎴戠殑杞﹁緳锛屾湁杩囨垜鐨勮溅杈欑殑鍦版柟涔熼兘鏈夎繃姣嶄翰...
绛旓細銆婃垜涓庡湴鍧涖嬪ソ鍙ユ憳鎶勮祻鏋愬涓嬶細1銆佽繖鍙ゅ洯浠夸經灏辨槸涓轰簡绛夋垜锛岃屽巻灏芥钵妗戝湪閭e効绛夊緟浜嗗洓鐧惧骞銆傝祻鏋愶細鍦ㄤ綔鑰呯殑蹇冪洰涓紝鍙ゅ洯鍜屼粬鏄伅鎭浉閫氱殑锛屽彜鍥兘澶熸劅鍙椾粬鐨勭棝鑻︼紝鐞嗚В浠栫殑鎯呮劅锛屽苟缁欎粬浠ョ敓鍛界殑鍚ず銆傚彲浠ヨ锛岃嚜浠栨畫鐤句互鍚庡啀鏉ュ埌杩欓噷锛屽彜鍥氨鎴愪簡浠栫敓鍛界殑涓閮ㄥ垎銆2銆鍥瓙鑽掕姕浣嗗苟涓嶈“璐銆傝祻鏋...
绛旓細瀵艰锛氥婃垜涓庡湴鍧涖嬶紝闀跨瘒鍝叉濇姃鎯呮暎鏂囷紝涓浗褰撲唬钁楀悕浣滃鍙查搧鐢钁椼傛槸鍙查搧鐢熸枃瀛︿綔鍝佷腑锛屽厖婊″摬鎬濆張鏋佷负浜烘у寲鐨勪唬琛ㄤ綔涔嬩竴銆備笅闈㈡槸鎴戞敹闆嗘暣鐞嗙殑鍏充簬銆婃垜涓庡湴鍧涖嬩腑鐨浼樼編鍙ュ瓙锛屾杩庡ぇ瀹堕槄璇诲弬鑰!1銆 鍦ㄦ弧鍥讥婕殑娌夐潤鍏夎姃涓紝涓涓汉鏇村鏄撶湅鍒版椂闂达紝骞剁湅瑙佽嚜宸辩殑韬奖銆2銆 濂硅壈闅剧殑鍛借繍锛屽潥蹇嶇殑鎰忓織鍜屾...
绛旓細銆婃垜涓庡湴鍧涖鏄鍙查搧鐢熺殑涓绡囨姃鍐欎汉鐢熸劅鎮熺殑浼樼編鏁f枃銆傚畠浠ヨ嚜宸卞拰姣嶄翰涓哄璞★紝浠モ滄垜鈥濈殑鑲㈡畫涓虹紭璧凤紝灏嗕釜浜虹殑鐥涜嫤鍐欏緱娣嬫紦灏借嚧锛屽皢姣嶄翰鐨勮壈闅惧睍绀哄緱鏋佷负鍏呭垎銆傚湪琛ㄧ幇杩欎竴鍐呭鏃讹紝浣滆呭ぇ閲忓湴杩愮敤浜嗘伋鍒囦紭缇庣殑鏂囧瓧锛屽洜鑰屽瘜鏈夊摬鐞嗙殑璀﹁█浣冲彞鐢氬锛屽吂寮曞嚑渚嬭祻鏋愶細1.鍦ㄦ弧鍥讥婕殑娌夐潤鍏夎姃涓紝涓涓汉鏇村鏄...
绛旓細銆婃垜涓庡湴鍧涖鏄竴绡囬暱绡囧摬鎬濇姃鎯呮暎鏂囷紝涓浗褰撲唬浣滃鍙查搧鐢钁椼傝繖閮ㄤ綔鍝佹槸鍙查搧鐢熸枃瀛︿綔鍝佷腑锛屽厖婊″摬鎬濆張鏋佷负浜烘у寲鐨勪唬琛ㄤ綔涔嬩竴銆傚叾鍓嶇涓娈鍜岀浜屾琚撼鍏ヤ汉姘戞暀鑲插嚭鐗堢ぞ鐨勯珮涓鏁欐潗涓傛槸浣滆呭崄浜斿勾鏉ユ憞鐫杞鍦ㄥ湴鍧涙濈储鐨勭粨鏅躲傛暎鏂囦腑楗卞惈浣滆呭浜虹敓鐨勭绉嶆劅鎮燂紝瀵逛翰鎯呯殑娣辨儏璁存瓕銆傚湴鍧涘彧鏄竴涓浇浣擄紝鑰...
绛旓細銆婃垜涓庡湴鍧涖鏄鍙查搧鐢鍦ㄦ极闀跨殑鑹伴毦宀佹湀閲屽鍛借繍鐨勬濊冧笌鍙╅棶銆1 鐢熷懡鐨勪环鍊煎氨鍦ㄤ簬鑳藉闀囬潤鑰屾縺鍔ㄥ湴娆h祻杩欒繃绋嬬殑鎮插.鍜岀編涓斤紝浠庝笉灞堜腑鑾峰彇楠勫偛锛屼粠鑻﹂毦涓幏鍙栧垢绂忥紝浠庤櫄鏃犱腑鍒涢犳剰涔夈2 鍦ㄤ汉鐢熺殑姣忎釜闃舵锛屾垜浠兘瀵规极婕墠绋嬫姳鐫涓浠芥縺鍔ㄧ殑甯屾湜锛屼互涓哄杩瑰氨鍦ㄥ墠鏂广傜劧鑰岋紝浜虹敓鍙槸涓涓釜姊︽兂涓嶆柇鐮寸伃鐨勮繃绋...
绛旓細鎵规敞锛 杩欎竴娈垫槸鎴戦挓鐖鐨勪竴娈佃瘽銆傝繍鐢ㄦ瘮鍠伙紝鎷熶汉绛変慨杈炴墜娉曪紝灏嗛粍鏄忎笅缇庝附鐨鍦板潧瀹岀編鐨勫憟鐜板湪鎴戜滑鐪煎墠銆傝繖閲屾槸涓鐗囩敓鏈猴紝鍗充娇鏄湪鍌嶆櫄鍗佸垎銆 鑳借儗鍒欒儗锛侊紒锛佷竷銆佸湪婊″洯寮ユ极鐨勬矇闈欏厜鑺掍腑锛屼竴涓汉鏇村鏄撶湅鍒版椂闂达紝骞剁湅瑙佽嚜宸辩殑韬奖銆傛壒娉細1.鏂囩珷鍙嶅鍦扮敤鏃堕棿鐨勫嵃璁版潵鎻忕粯鍥炬锛屼竴骞村洓瀛g殑澹伴煶涓庡厜褰憋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