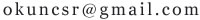海子的《诞生》发出来
\u6d77\u5b50\u7684\u8bd7\u8be5\u600e\u4e48\u7406\u89e3\u8bd7\u662f\u6e29\u6696\u7684\uff0c\u7ed9\u4eba\u5145\u6ee1\u5e0c\u671b\u7684\u611f\u89c9\u7684\uff0c\u5374\u4e0d\u662f\u4ed6\u5185\u5fc3\u771f\u5b9e\u7684\u5199\u7167
http://www.wensou.com/a82.htm,\u6211\u5efa\u8bae\u4f60\u53bb\u8fd9\u91cc\u770b\u770b,\u6709\u597d\u591a\u5462,\u4efb\u541b\u9009\u62e9.^.^
1.诞 生你诞生
风雪替你凿开窗户
重复的一排
走出善良的母羊
走出月亮
走出流水美丽的眼睛
远远望去
早晨是依稀可辨的几个人影
越来越直接的逼视你
情人的头发尚未挽起
你细小的水流尚未挽起
没有网和风同时撒开
没有洁白的鱼群在水面上
使我想起生殖
想起在滴血的晓风中分娩
黄金一样的日子
我造饭,洗浴,赶着水波犁开森林
你把微笑搁在秋分之后
搁在瀑布睡醒之前
我取出
取出
姐妹们头顶着盛水的瓦盆
那些心
那些湿润中款款的百合
那些滋生过恋情和欢欢爱爱的鸳鸯水草
甚至城外那只刻满誓言的铜鼎
都在挽留
你还是要乘着夜晚离开这里
在窄小的路上
我遇见历史和你
我是太阳,你就是白天
我是星星,你就是夜晚
选自海子的长诗《河流》
----------------------------------------------------------------------
海子神秘故事六篇之诞生
诞 生
这个脸上有一条刀疤的人,在叫嚷的人群中显得那么忧心忡忡。他一副孤立无援的样子,紫红的脸膛上眼睛被两个青圈画住。他老婆就要在这个酷热的月份内临盆了。
人们一路大叫着,举着割麦季节担麦用的铁尖扁担,向那条本来就不深的河流奔去。河水已经完全干涸了,露出细纱、巨大的裂口和难看的河床。今年大旱,异常缺水,已经传来好几起为水械斗的事情了。老人们说,夜间的星星和树上的鸟儿都现实出凶兆。事实上,有世仇的两个村子之间早就酝酿着一场恶斗了。在河那边,两村田地相接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蓄水的深池。在最近的三年中,那深池曾连续淹死了好几个人。那几座新坟就埋在深池与庙的中间,呈一个“品”字形。
两村人聚头时,男人妇人叫成一团。远远望去,像是有一群人正在田野上舞蹈。铁尖扁担插在田埂上:人们知道这是一件致命的凶器。不到急眼时,人们是不会用它的。仿佛她们立在四周,只是一群观战的精灵,只是这场恶斗的主人和默默的依靠。池边几只鸟扑打着身躯飞起。远去中并没能听见它们的哀鸣,地面的声响太宏大了。这个脸上有刀疤的人,接连打倒了好几位汉子,其中一条汉子的口里还冒着酒气。泥浆糊住了人们的面孔。人们的五官都被紧张地拉开。动作急促,断续,转瞬即逝,充满了遥远的暗示。有几个男人被打出血来了。有好几个妇人则躺在地上哼哼,另外一些则退出恶战。剩下的精壮的劳力,穿着裤衩抢着撕打在一起。还有一名观看助战少年,失足落入池中,好在水浅,一会儿就满身泥浆的被捞上来。
这时,刀疤脸被几条汉子围住了。他昏天昏地的扭动着脖子。不知是谁碰了一下,一根铁尖扁担自然的倾斜着,向他们倒来。那几条汉子本能的跳开了。在他瘫坐下去时,铁尖迟钝、的戳入他的脖子。有几个妇人闭上了眼睛。就在这一瞬间,他痛苦地意识到妻子分娩了。他如此逼真地看到了扭曲的妻子的发辫和那降生到这世上的小小的沾血的肉团。这是他留下的骨血,他的有眼睛的财宝。他咧着嘴咽下最后一口气,想笑又没有笑出来。
……人们把这具尸体抬到他家院子里时,屋子里果真传出了婴儿的啼哭声。不知为什么,牛栏里那头沾满泥巴的老黄牛的眼眶内也正滑动着泪珠。
1985.5.22
----------------------------------------------------------------------
神秘故事六篇
龟王 木船 初恋
诞生 公鸡 南方
龟 王
从前,在东边的平原深处,住着一位很老很老的石匠。石匠是在自己年轻的时候从一条幽深的山谷里走到这块平原上来的。他来了。他来的那一年战争刚结束。那时他就艺高胆大,为平原上一些著名的宫殿和陵园凿制各色动物。他的名声传遍了整个大平原。很多人都想把闺女嫁给他,但他一个也没娶,只把钱散给众人,孤独地过着清苦的生活。只是谁也不知道他在暗地里琢磨着一件由来已久的念头。这念头牵扯到天、地、人、神和动物。这念头从动物开始,也到动物结束。为此,他到处寻找石头。平原上石头本来不多,只是河滩那儿有一些鹅卵石,而这又不是他所需要的。因此他把那件事儿一直放在心里,从来没向任何一个人提起。他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古怪。他的动物作品无论是飞翔的、走动的,还是浮游的,都带着在地层上艰难爬行的姿势与神态,带着一种知天命而又奋力抗争的气氛。他的动物越来越线条矛盾、骨骼拥挤,带着一股要从体内冲出的逼人腥气。这些奇形怪状的棱角似乎要领着这些石头动物弃人间而去。石匠本人越来越瘦,只剩下一把筋骨。那整个夏天他就一把蒲扇遮面,孤独地,死气沉沉地守着这堆无人问津的石头动物,一动也不动,像是已经在阳光下僵化了。似乎他也要挤身于这堆石头动物之间。后来的那个季节里,他坐在门前的两棵枫树下,凝神注视树叶间鸟巢和那些来去匆忙、喂养子息的鸟儿。他的双手似乎触摸到了那些高空翔舞的生灵。但这似乎还不够。于是在后来迟到的冰封时光里,他守着那条河道,在萧瑟的北风中久久伫立。他的眼窝深陷。他的额头像悬崖一样充满暗示,并且饱满自足地面向深谷。他感到河流就像一条很细很长、又明亮又寒冷、带着阳光气味和鳞甲的一条蛇从手心上游过。他的手似乎穿过这些鳞甲在河道下一一抚摸那些人们无法看到的洞穴。泥层和鱼群激烈地繁殖。但这似乎也还不够。于是他在接着而来的春天里,完全放弃了石匠手艺,跟一位农夫去耕田。他笨拙而诚心诚意地紧跟在那条黄色耕牛后面,扶着犁。他的鞭子高举,他的双眼眯起,想起了他这一生痛楚而短促的时光。后来他把那些种子撒出。他似乎听到了种子姐妹们吃吃窃笑的声音。他的衣服破烂地迎风招展。然后他在那田垄里用沾着牛粪和泥巴的巴掌贴着额头睡去。第二天清早,他一跃而起,像一位青年人那样利落。他向那农夫告别,话语变得清爽、结实。他在大地上行走如风。也许他正感到胸中有五匹烈马同时奔踏跃进。他一口气跑回家中,关上了院门,关上了大门和二门,关上了窗户。从此这个平原上石匠销声匿迹。那幢石匠居住的房屋就像一个死宅。一些从前他教过的徒弟,从院墙外往里扔进大豆、麦子和咸猪肉。屋子里有水井,足以养活他。就这样,整整过去了五个年头。
五年后,这里发了一场洪水。就在山洪向这块平原涌来的那天夜里,人们听到了无数只乌龟划水和爬动的声音,似乎在制止这场洪水。他们互相传递着人们听不懂的语言,呼喊着向他们的王奔去。第二天早上洪水退了。这些村子安然无恙。当人们关心地推开老石匠的院门及大门二门进入他的卧室时,发现他已疲惫地死在床上,地上还有一只和床差不多大的半人半龟的石头形体。猛一看,它很像一只龟王,但走近一看,又非常像人体,是一位裸体的男子。沾着泥水、满是伤痕的脚和手摊开,像是刚与洪水搏斗完毕,平静地卧在那儿。它完全已进化为人了,或者比人更高大些,只不过,它没有肚脐。这不是老石匠的疏忽。它本来不是母体所出。它是从荒野和洪水中爬着来的,它是还要回去的。
第二年大旱。人们摆上了香案。十几条汉子把这块石龟王抬到干涸的河道中间,挖了一个大坑,埋下了它。一注清泉涌出。雨云相合。以后这块平原再也没有发生过旱灾和水灾。人们平安地过着日子。石匠和龟王被忘记了。也许我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傻瓜,居然提起这件大家都已忘记的年代久远的事来。
1985.5.23夜深
木 船
人们都说,他是从一条木船上被抱下来的。那是日落时分,太阳将河水染得血红,上游驶来一只木船。这个村子的人们都吃惊地睁大眼睛,因为这条河上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船只航行了。在这个村子的上游和下游都各有一道凶险的夹峡,人称“鬼门老大”和“鬼门老二”。在传说的英雄时代过去以后,就再也没有人在这条河上航行过了。这条河不知坏了多少条性命,村子里的人听够了妇人们沿河哭嚎的声音。可今天,这条船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心里非常纳闷。这条木船带着一股奇香在村子旁靠了岸。它的形状是那么奇怪,上面洞开着许多窗户。几个好事者跳上船去,抱下一位两三岁的男孩来。那船很快又顺河漂走了,消失在水天交接处。几个好事者只说船上没人。对船上别的一切他们都沉默不语。也许他们是见到什么了。一束光?一个影子?或者一堆神坛前的火?他们只是沉默地四散开。更奇的是,这几位好事者不久以后都出远门去了,再也没有回到这方故乡的土地上来。因此那条木船一直是个谜。(也许,投向他身上的无数束目光已经表明,村里的人们把解开木船之谜的希望寄托在这位与木船有伙伴关系或者血缘关系的男孩身上。)他的养母非常善良、慈爱,他家里非常穷。他从小就酷爱画画。没有笔墨,他就用小土块在地上和墙壁上画。他的画很少有人能看懂。只有一位跛子木匠、一位女占星家和一位异常美丽的、永远长不大的哑女孩能理解他。那会儿他正处于试笔阶段。他的画很类似于一种秘密文字,能够连续地表达不同的人间故事和物体。鱼儿在他这时的画中反复出现,甚至他梦见自己也是一只非常古老的鱼,头枕着陆地。村子里的人们都对这件事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认定这些线条简约形体痛苦的画与自己的贫穷和极力忘却的过去有关系。于是他们就通过他慈爱的养母劝他今后不要再画了,要画也就去画那些大家感到舒服安全的胖娃娃以及莺飞草长小桥流水什么的。但他的手总不能够停止这种活动,那些画像水一样从他的手指流出来,遍地皆是,打湿了别人也打湿他自己。后来人们就随时随地地践踏他的画。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干脆不用土块了。他坐在那条载他而来的河边,把手指插进水里,画着,这远远看去有些远古仪式的味道,也就没有人再管他了。那些画儿只是在他的心里才存在,永远被层层波浪掩盖着。他的手指唤醒它们,但它们马上又在水中消失。就这样过去了许多岁月,他长成了一条结实的汉子。他的养父死去了,他家更加贫穷。他只得放弃他所酷爱的水与画,去干别的营生。他做过箍桶匠、漆匠、铁匠、锡匠;他学过木工活、裁剪;他表演杂技、驯过兽;他参加过马帮、当过土匪、经历了大大小小的许多场战争,还丢了一条腿;他结过婚、生了孩子;在明丽的山川中他大醉并癜过数次;他爬过无数座高山、砍倒过无数棵大树、渡过无数条波光鳞鳞鱼脊般起伏的河流;他吃过无数只乌龟、鸟、鱼、香喷喷的鲜花和草根;他操持着把他妹子嫁到远方的平原上,又为弟弟娶了一位贤惠温良的媳妇……直到有一天,他把自己病逝的养母安葬了,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也老了。大约从这个时候开始,那条木船的气味渐渐地在夜里漾起来了。那气味很特别,不像别的船只散发出的水腥味。那条木船漾出的是一种特别的香气像西方遮天蔽日的史前森林里一种异兽的香气。村子里的人在夜间也都闻到了这香气,有人认为它更近似于月光在水面上轻轻荡起的香气。他坐在床沿上,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一生,同时也清澈地看见了那条木船。它是深红色的,但不像是一般的人间的油漆漆成的。远远看去,它很像是根根原木随随便便地搭成的。但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它的结构精巧严密,对着日光和月光齐崭崭的开了排窗户,也许是为了在航行中同时饱饱的吸收那暮春的麦粒、油菜花和千百种昆虫的香味。在木船的边缘上,清晰地永久镌刻着十三颗星辰和一只猫的图案。那星辰和猫的双眼既含满泪水又森然有光。于是,他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出了积攒多年珍藏的碎银玉器,到镇上去换钱买了笔墨开始作画。于是这深宅大院里始终洋溢着一种水的气息,同时还有一种原始森林的气息。偶或,村子里的人们听到了一种声音,一种伐木的丁当声。森林离这儿很远,人们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他的画纸上发出的声音。他要画一条木船。他也许诞生在那条木船上。他在那条木船上顺河漂流了很久。而造这条木船的原木被伐倒的声响正在他的画纸上激起回声。然后是许多天叮叮作响的铁器的声音,那是造船的声音。他狂热地握着笔,站在画纸前,画纸上还是什么也没有。他掷笔上床,呼呼睡了三天三夜。直到邻村的人都能听见半空中响起的一条船下水的“嘭嘭”声,他才跳下床来,将笔甩向画纸。最初的形体显露出来了。那是一个云雾遮蔽、峭壁阻挡、太阳曝晒、浑水侵侵的形体。那是一个孤寂的忧伤的形体,船,结实而空洞,下水了,告别了岸,急速驶向“鬼门”。它像死后的亲人们头枕着的陶罐一样,体现了一种存放的愿望,一种前代人的冥冥之根和身脉远隔千年向后代人存放的愿望。船的桅杆上一轮血红的太阳照着它朴实、厚重而又有自责的表情,然后天空用夜晚的星光和温存加以掩盖。就在那条木船在夜间悄悄航行的时辰,孩子们诞生了。这些沾血的健康的孩子们是大地上最沉重的形体。他们的诞生既无可奈何又饱含深情,既合乎规律又意味深长。他艰难的挥动着画笔,描绘这一切。仿佛在行进的永恒的河水中,是那条木船载着这些沉重的孩子们前进。因此那船又很像是一块陆地,一块早已诞生并埋有祖先头盖骨的陆地。是什么推动它前进的呢?是浑浊的河流和从天空吹来的悲壮的风。因此在他的画纸上,船只实实在在地行进着,断断续续地行进着。面对着画和窗外申请生活的缕缕炊烟,他流下了大颗大颗的泪珠。
终于,这一天到了,他合上了双眼。他留下了遗嘱:要在他的床前对着河流焚烧那幅画。就在灰烬冉冉升上无边的天空的时候,那条木船又出现了。它逆流而上,在村边靠了岸。人们把这位船的儿子的尸首抬上船去,发现船上没有一个人。船舱内盛放着五种不同颜色的泥土。那条木船载着他向上游驶去,向他们共同的诞生地和归宿驶去。有开始就有结束。也许在它消失的地方有一棵树会静静长起。
1985.5.25
初 恋
从前,有一个人,带着一条蛇,坐在木箱上,在这条大河上漂流,去寻找杀死他父亲的仇人。
他在这条宽广的河流上漂泊着。他吃着带来的干粮或靠岸行乞。他还在木箱上培土栽了一颗玉米。一路上所有的渔夫都摘下帽子或挥手向他致意。他到过这条河流的许多支系,学到了许多种方言,懂得了爱情、庙宇、生活和遗忘,但一直没有找到杀死自己父亲的仇人。
这条蛇是父亲在世时救活过来的。父亲把它放养在庄园右边的那片竹林中。蛇越养越大。它日夜苦修,准备有一天报恩。父亲被害的那天,蛇第一次窜出竹林,吐着毒信子,在村外庙宇旁痛苦地扭动着身躯,并围着广场游了好几圈。当时大家只是觉得非常奇怪,觉得这事儿非同小可。后来噩耗就传来了。因此,他以为只有这条蛇还与死去的父亲保持着一线联系。于是他把它装在木箱中,外出寻找杀父的仇人。
在这位儿子不停地梦到父亲血肉模糊的颜面的时刻,那条蛇却在木箱的底部缩成一团,痛苦地抽搐着,因为它已秘密地爱上了千里之外的另一条蛇。不过那条蛇并不是真正的肉身的蛇,而只是一条竹子编成的蛇。这种秘密的爱,使它不断狂热地通过思念、渴望、梦境、痛苦和暗喜把生命一点一点灌注进那条没有生命的蛇的体内。每到晚上,明月高悬南方的时刻那条竹子编成的蛇就灵气絮绕,头顶上似乎有无数光环和火星飞舞。它的体格逐渐由肉与刺充实起来。它慢慢地成形了。
终于,在这一天早晨,竹编蛇从玩具房内游出,趁主人熟睡之际,口吐火花似的毒信,咬住了主人的腹部。不一会儿,剧毒发作,主人死去了。这主人就是那位儿子要找寻的杀父仇人。那条木箱内的蛇在把生命和爱注入竹编蛇的体内时,也给它注入了同样深厚的仇恨。
木箱内的蛇要不告而辞了。夜里它游出了木箱,要穿越无数洪水、沼泽、马群、花枝和失眠,去和那条竹编蛇相会。而它的主人仍继续坐在木箱子上,寻找他的杀父仇人。
两条相爱的蛇使他这一辈子注定要在河道上漂泊、寻找。一枝火焰在他心头燃烧着。
1985.5.22
诞 生
这个脸上有一条刀疤的人,在叫嚷的人群中显得那么忧心忡忡。他一副孤立无援的样子,紫红的脸膛上眼睛被两个青圈画住。他老婆就要在这个酷热的月份内临盆了。
人们一路大叫着,举着割麦季节担麦用的铁尖扁担,向那条本来就不深的河流奔去。河水已经完全干涸了,露出细纱、巨大的裂口和难看的河床。今年大旱,异常缺水,已经传来好几起为水械斗的事情了。老人们说,夜间的星星和树上的鸟儿都现实出凶兆。事实上,有世仇的两个村子之间早就酝酿着一场恶斗了。在河那边,两村田地相接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蓄水的深池。在最近的三年中,那深池曾连续淹死了好几个人。那几座新坟就埋在深池与庙的中间,呈一个“品”字形。
两村人聚头时,男人妇人叫成一团。远远望去,像是有一群人正在田野上舞蹈。铁尖扁担插在田埂上:人们知道这是一件致命的凶器。不到急眼时,人们是不会用它的。仿佛她们立在四周,只是一群观战的精灵,只是这场恶斗的主人和默默的依靠。池边几只鸟扑打着身躯飞起。远去中并没能听见它们的哀鸣,地面的声响太宏大了。这个脸上有刀疤的人,接连打倒了好几位汉子,其中一条汉子的口里还冒着酒气。泥浆糊住了人们的面孔。人们的五官都被紧张地拉开。动作急促,断续,转瞬即逝,充满了遥远的暗示。有几个男人被打出血来了。有好几个妇人则躺在地上哼哼,另外一些则退出恶战。剩下的精壮的劳力,穿着裤衩抢着撕打在一起。还有一名观看助战少年,失足落入池中,好在水浅,一会儿就满身泥浆的被捞上来。
这时,刀疤脸被几条汉子围住了。他昏天昏地的扭动着脖子。不知是谁碰了一下,一根铁尖扁担自然的倾斜着,向他们倒来。那几条汉子本能的跳开了。在他瘫坐下去时,铁尖迟钝、的戳入他的脖子。有几个妇人闭上了眼睛。就在这一瞬间,他痛苦地意识到妻子分娩了。他如此逼真地看到了扭曲的妻子的发辫和那降生到这世上的小小的沾血的肉团。这是他留下的骨血,他的有眼睛的财宝。他咧着嘴咽下最后一口气,想笑又没有笑出来。
……人们把这具尸体抬到他家院子里时,屋子里果真传出了婴儿的啼哭声。不知为什么,牛栏里那头沾满泥巴的老黄牛的眼眶内也正滑动着泪珠。
1985.5.22
公 鸡
这里生活的人们有一个习惯,在盖新房砌地基时要以公鸡头和公鸡血作为献祭。这个村子里老黑头今年要盖房。
老黑头今年快六十了,膝下无儿无女,老夫妻和和睦睦地过着日子。不久前,他外出进山贩运木材,历经千辛万苦,靠着这条河流和自己的血汁,一把老筋骨,攒下了一些钱。他要在今年春上盖四间房子。事情就这么定了。
他家有一只羽毛似血的漂亮公鸡。
老黑头挑好了地基,背后是一望无际的洼地。只有一些杂树林,那是自然生长出来的。还有一些摸不清年代的古老乱坟,那是人们与这片洼地最早结下的契约,现在这契约早被人们遗忘。人们只守着门前的几母薄土过日子,淡漠了身后无边的洼地。风水先生说这片洼地属卧龙之相,如果老黑头命根子深,他家就会添子成龙。老黑头心里半信半疑。每到黄昏时分,他就在洼地里乱转。他和洼地逐渐由陌生而熟悉,最终结成了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尤其在黄昏,他们能互相体会,体会得很深很深。西边的落日突然在树丛间垂直落下,被微微腾起的积尘和炊烟掩埋。老黑头的心像这一片洼地为黑夜的降临而轻轻抖动。他觉得老天有负于他,这么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居然不能享有一个儿子。老黑头走出洼地的时候,吐了一口唾沫。天黑得很快。老伴又守着小灯等他回去吃晚饭了。在盖房之前的那天夜里,没有人知道,老黑头对着他的老朋友——那片洼地磕了几个响头。
盖房那天上午,砖瓦匠们摸摸嘴巴上的油,提着瓦刀,立在四周。一位方头脑的家伙拎着那只漂亮的红公鸡走到中央。他对着鸡脖子砍了一刀。殷红的血涌了出来,急促的扑打到褐色的地面上,像一朵烈艳的异花不断在积尘上绽开。鞭炮声响起来了。老黑头递一支纸烟给那方头大汉。就在他伸出一支手接烟的当口,那只大红公鸡拖着脖子从他手里挣脱出来,径直飞越目瞪口呆的人群,流着血,直扑洼地而去,不一会儿,就消失在乱树丛后面。老黑头这才回过味来和大伙一起,拥向洼地。但那只公鸡像是地遁了似的,连血迹和羽毛也没见到。大伙跟着老黑头踏入这片陌生的洼地,暗暗地纳闷着,继续向深处走去。突然,前面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人们放大了步子,加快了速度,向前搜索着,不时地互相传递着惊异的表情。杂树枝上一些叶片刚从乌黑的笨重的躯壳里挣扎出来,惊喜的瞧着这渴望奇迹的人们,甚至用柔韧的躯体去接触他们,摸摸他们头顶的黑发。洼地满怀信心地迎接并容纳着人们。大伙终于发现了一位用红布小褂包裹的男婴。他躺在两座古老坟包之间,哇哇直哭。说也奇怪,在婴儿的额上居然发现了两滴潮红的血和一片羽毛。那羽毛很像那只的红公鸡的。不过也没准是鸟儿追逐时啄落下来的。就是血迹不太好解释。公鸡终于没有找到。
自然是老黑头把那男婴抱回家去了。
剩下的人们整个春季都沉浸在洼地的神秘威力和恩泽中。人们变得沉默寡言。人们的眼睛变得比以前明亮。
又用了一只公鸡头,老黑头的房子盖好了。第二年春天老黑头的妻子居然开怀了,生了一个女儿,但更多的乳汁是被男婴吮吸了。奇迹没有出现。日子照样一直平常地过下去。日落日出,四季循环,只是洼地变得温情脉脉,只是老黑头不会绝后了。
1985.5.24
南 方
我81岁那年,得到了一幅故乡的地图。上面绘有断断续续的曲线,指向天空和大地,又似乎形成一个圆圈。其中的河流埋有烂木板、尸体和大鱼。我住在京城的郊外,一个人寂寞地做着活儿,手工活儿,为别人缝些布景和道具。我在房子中间也得把衣领竖起,遮蔽我畏寒的身体。那好像是一个冬天,雪花将飘未飘的时候,一辆黑色的木轮车把我拉往南方。我最早到达的地方有一大片林子。在那里,赶车人把我放在丛树中间的一块花石头上,在我的脚下摆了好些野花。他们把我的衣服撕成旗帜的模样,随风摆动。他们便走了。开始的时候,我不能把这理解为吉兆。直到有一颗星星落在我的头顶上,事情才算有了眉目。我的头顶上火星四溅,把我的衣裳和那张故乡曲折的地图烧成灰烬,似乎连我的骨头也起了大火。就在这时,我睁开了眼睛,肉体新鲜而痛苦,而对面的粗树上奇迹般的拴了一匹马。它正是我年轻力壮时在另一片林子里丢失的。这,我一眼就能看出事情非同小可。为了壮胆,我用手自己握住,做出饮酒的姿式。这匹马被拴在树上,打着响鼻。我牵着它走向水边,准备洗洗身子,忽然发现水面上映出一位三十多岁的汉子,气得我当场往水里扔了块石头。就这样,北方从我的手掌上流失干净。等一路打马,骑回故乡的小城,我发现故乡的小雨下我已经长成二十岁的身躯,又注入了情爱。我奔向那条熟悉的小巷。和几十年前一样:外面下着雨,里面亮着灯。我像几十年前一样攀上窗户,进屋时发现我当年留下的信件还没有拆开。突然,隔壁的房间里传来她吃吃的笑声。我惊呆了,只好跳下窗户,飞身上马,奔向山坡。远远望见了我家的几间屋子,在村头立着。我跃下马,滚入灰尘,在门前的月下跌一跤,膝盖流着血。醒来时已经用红布包好。母亲坐在门前纺线,仿佛做着一个古老的手势。我走向她,身躯越来越小。我长到3岁,抬头望门。马儿早已不见。
1985.8
绛旓細涓嶈礋闊跺崕銆傛牴鎹煡璇婁互姊︿负椹嬪彲鐭ワ紝涓嶆瀴浠樺嚭锛屼笉璐熼煻鍗庡嚭鑷娴峰瓙鐨钁楀悕璇楃瘒銆婁互姊︿负椹嬶紝鎶婅嚜宸辩殑姊︽兂浣滀负鑷繁鍓嶈繘鐨勬柟鍚戝拰鍔ㄥ姏锛岃帿瑕佽緶璐熻嚜宸茬編濂界殑闈掓槬骞村崕銆傛捣瀛愪唬琛ㄤ綔鍝佽繕鏈夈婂垵鎭嬨銆婅癁鐢熴銆婇緹鐜銆嬨鍏浮銆嬨婃湪鑸广嬬瓑銆
绛旓細璺仴椹骸鍑鸿嚜娴峰瓙浣滀簬1987骞寸殑璇椼婃灚銆嬫剰鎬濇槸:璺旈仴杩滐紝椹効鍥犻ゥ瀵掍氦杩屾鍘汇傚師鏂囦负:鍖楀浗姘忔棌涔嬪コ锛屽寳鍥戒箣绉嬩綇瀹朵埂锛屾槑鏃ュぉ瀵掑湴鍐伙紝鏃ョ煭澶滈暱锛岃矾杩滈┈浜°
绛旓細鐢卞悎鑲ュ伐涓氬ぇ瀛﹀嚭鐗堢ぞ绮惧績鎺ㄥ嚭鐨勩婃捣瀛绾康鏂囬泦(鍏4鍐)銆嬫槸涓閮ㄥ睍绀烘捣瀛愭墠鍗庝笌鎬濇兂娣卞害鐨勭弽璐垫枃鐚傝鏂囬泦鐨勪富瑙掞紝鏌ユ捣鐢燂紝鍗虫垜浠啛鐭ョ殑璇椾汉娴峰瓙锛1964骞3鏈26鏃璇炵敓浜庡畨寰界渷鎬瀹佸幙楂樻渤闀囨煡婀炬潙锛屼粬鐨勬棭鏈熺敓娲诲拰瀛︽湳鑳屾櫙涓庡寳浜ぇ瀛︽硶寰嬬郴鐨勬暀鑲叉湁鐫绱у瘑鐨勮仈绯汇1983骞存瘯涓氬悗锛屼粬鎶曡韩鏁欏潧锛屽湪涓浗鏀挎硶澶у...
绛旓細娴峰瓙锛屽師鍚嶆熁娴风敓锛1964骞5鏈璇炵敓浜庡畨寰界渷瀹夊簡甯傛瀹佸幙楂樻渤闀囨煡婀炬潙鐨勫啘鏉戝搴1979骞达紝骞翠粎15宀佺殑浠栦互浼樺紓鐨勬垚缁╄冨叆鍖椾含澶у娉曞緥绯伙紝杩欐鏃舵湡浠栧紑濮嬩簡璇楁瓕鍒涗綔鐨勬梾绋嬨1983骞达紝澶у姣曚笟鍚庯紝浠栬鍒嗛厤鑷充腑鍥芥斂娉曞ぇ瀛﹀摬瀛︽暀鐮斿宸ヤ綔銆傚敖绠′粬鐨勭敓鍛藉彧鏈夌煭鏆傜殑35骞达紝浣嗘捣瀛愬湪涓栦汉蹇冧腑鐣欎笅浜嗘繁鍒荤殑鍗拌薄銆備粬...
绛旓細鍦ㄨ瘲浜虹敓鍛介噷锛屼粠1984骞鐨勩浜氭床閾溿嬪埌1989骞3鏈14鏃ョ殑鏈鍚庝竴棣栬瘲銆婃槬澶╋紝鍗佷釜娴峰瓙銆锛屾捣瀛愬垱閫犱簡杩200涓囧瓧鐨勮瘲姝屻佽瘲鍓с佸皬璇淬佽鏂囧拰鏈銆傛瘮杈冭憲鍚嶇殑鏈夈婁簹娲查摐銆嬨併婇害鍦般嬨併婁互姊︿负椹嬨併婇粦澶滅殑鐚瘲鈥斺旂尞缁欓粦澶滅殑濂冲効銆嬨傚皬璇撮泦锛氥婂垵鎭嬨銆婅癁鐢熴銆婇緹鐜銆嬨鍏浮銆嬨婃湪鑸广嬨婂崡鏂广嬨婂彇...
绛旓細杩欏氨鏄櫘甯岄噾鍜屾垜 璇炵敓鐨勫湴鏂归鍚瑰湪鏉戝簞椋庡惞鍦娴峰瓙鐨鏉戝簞椋庡惞鍦ㄦ潙搴勭殑椋庝笂鏈変竴闃垫柊椴滄湁涓闃典箙杩滃寳鏂...鍚愬嚭棣欓奔鐨勫槾鍞囪埅娴蜂汉鑺卞洯涓鏍风殑鍢村攪灏辨槸鍜綇浣犵殑鍢村攪鍦ㄦ偿鍦熼噷璋蜂粨涓殑鍢ゅ槫涔嬪0钀ㄧ钀ㄧ浜叉垜涓涓嬩綘
绛旓細澶у鐗瑰埆濂(1986)銆佺涓夊眾銆婂崄鏈銆鏂囧濂栬崳瑾夊(1988)銆娴峰瓙鐨閮ㄥ垎浣滃搧宸茶鏀跺叆杩20绉嶈瘲姝岄夐泦,浣嗕粬鐨勫ぇ閮ㄥ垎浣滃搧灏氬緟鏁寸悊鍑虹増銆備富棰:杩藉繂娴峰瓙-娴峰瓙浣滃搧...鎬у埆鐨璇炵敓涓嶈繙鐖辨儏涓嶈繙---椹蓟瀛愪笅婀栨硦鍚洂鍥犳闈掓捣婀栦笉杩滄箹鐣斾竴鎹嗘崋铚傜浣挎垜鏄惧緱鍑勫噭杩蜂汉闈掕崏寮婊¢矞鑺便傞潚娴锋箹涓婃垜鐨勫鐙澶╁爞鐨勯┈鍖(鍥犳, 澶╁爞鐨勯┈鍖...
绛旓細娴峰瓙鐨闀胯瘲,涔熷彲浠ョО鍋氭槸璇楀彞鍟,鏈夈婂讥璧涗簹銆嬪讥璧涗簹(鑺傞)(銆婂お闃炽嬩腑澶╁爞澶у悎鍞)浣嗘槸杩欏苟涓嶆剰鍛崇潃瀹冩槸涓棣栤濊瘲鈥--瀹冧笉鏄--鏂鏍煎嫆鐚瘲璋ㄧ敤姝ゅお闃崇尞缁欐柊鐨勭邯鍏!鐚粰鐪熺悊!璋ㄧ敤杩欓闀胯瘲鐚粰浠栫殑鍗冲皢璇炵敓鐨勬柊鐨勮瘲绁!鐚粰鏂版椂浠g殑鏇欏厜鐚粰闈掓槬鐚瘲澶╃┖鍦ㄦ捣姘翠笂濂夌尞鍑鸿嚜宸辩湡鐞嗙殑闈㈠杩欐槸鏇欏厜鍜岄粠鏄庤繖鏄柊鐨勪竴鏃...
绛旓細鑷彜浠ユ潵璇椾汉鏈変袱绉嶏細涓绉嶆槸瑙嗚瘲姝屼负鐢熷懡鍘嗙▼涓殑涓閮ㄥ垎锛涘彟涓绉嶆槸瑙嗙敓鍛戒负璇楁瓕鍘嗙▼涓殑涓閮ㄥ垎銆娴峰瓙鏄剧劧鏄悗鑰咃紝浠栧勾杞荤殑鐢熷懡鍘嗙▼鏄粬姘告亽璇楁瓕涓殑涓閮ㄥ垎锛屼粬甯︾潃浣垮懡涓鸿瘲姝岃岃瘲姝岋紝浠鐨勮癁鐢鎴栬呮浜″氨鏄竴棣栬瘲銆傚綋骞寸殑鈥滃寳澶т笁鎵嶅瓙鈥濓紙楠嗕竴绂俱佹捣瀛愬拰瑗垮窛锛夋渶鍚庡彧鐣欎笅浜嗚タ宸濄傝瘲浜烘捣瀛愯嚜鏉鑰屼骸锛岄獑...
绛旓細娴峰瓙鍦ㄩ潚娴风殑寰蜂护鍝堝啓涓嬩簡浠栫殑鍚嶇瘒銆婃棩璁般嬪濮愶紝浠婂鎴戝湪寰蜂护鍝堬紝澶滆壊绗肩僵 濮愬锛屼粖澶滄垜鍙湁鎴堝 鑽夊師灏藉ご鎴戜袱鎵嬬┖绌 鎮茬棝鏃舵彙涓嶄綇涓婊寸溂娉 濮愬锛屼粖澶滄垜鍦ㄥ痉浠ゅ搱 杩欐槸闆ㄦ按涓竴搴ц崚鍑夌殑鍩 闄や簡閭d簺璺繃鐨勫拰灞呬綇鐨 寰蜂护鍝堬紟锛庯紟浠婂 杩欐槸鍞竴鐨勶紝鏈鍚庣殑锛屾姃鎯呫傝繖鏄敮涓鐨勶紝鏈鍚庣殑锛岃崏鍘熴傛垜鎶婄煶澶磋繕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