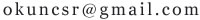《流浪儿》 | 上
我总在流浪,看遍山川大河,历尽人间孤苦,也看过人性至暗。我不信命,却被这所谓使命、职责玩弄于股掌之中。总听人言,人间走一遭,总该背负什么。
或许是吧,世间规则我从未搞懂。
夜风微凉,我宿在山头破败山寺。这地方看着楼宇林立,却早没了香火。只留一老翁,佝偻着身子苦苦守着那份安宁。
“阿弥陀佛,施主一身风霜,不若稍作休整。”他虽是俗家弟子,却也对我双手合十,慈悲若佛。
我一身破烂衣衫,斗笠虚掩着灰败面容,怀中抱一浆洗发白粗布包裹。颇有些狼狈,的确不似寻常江湖游子。
见他拿着扫帚,眼含善意。我也学他模样,恭敬回礼。
“小可叨扰,万不敢搅了佛门清净。”将腰间酒壶亮出,对他摇晃两下示意。正午时分阳光毒辣,他隐于屋檐之下一身清爽,而我被这刺目艳阳晃了眼,无意识舔着干涸开裂的唇角。
再做一揖,“污浊不堪,酒肉穿肠一俗烂人,某惶恐。”抬脚便走,不愿多留。
身后声响渐近,还是那双慈悲目。烈日当头,却不急不缓。依旧低眉敛目,语带担忧:“山野之地,无繁冗戒律清规。若再往山间行,恐施主今夜需栖于深山,此处猛兽出没并不安宁。”
是挽留之意,佛家子弟一贯好心肠,此下不好拒绝。只好再次回礼,稍退几步拍落些许尘土,才敢跟进寺中。
**
酒壶别在腰间,我将胡乱盖在眼前的斗笠拿下,攥在手心。对着前头隐有蹒跚之态的师父恭敬道:“多谢收留,若师父不嫌可唤某小字,清源。”
他转身对我报以一笑,先行几步,将扫具置于一旁。复取一瓢井水朝我走来,让我喝下。又引我入禅房,此处傍篱临水颇有雅趣。
“某粗鄙之身,便仗着年岁托大,唤某福伯即可。”福伯见我满脸倦怠,便让我坐于蒲团之上休息。
一身狼藉怎敢踏入坐禅参悟之地?我只站在门边摆手:“福伯莫要这般客气,清修之地清源不敢贸然打扰,廊下小坐片刻便是。”
福伯见我推脱,颇为焦灼再次开口:“公子可有难言之隐,才这般妄自菲薄?某虽老眼昏花,却未曾忘了恩人模样。那年公子奋力保下天王殿金身,守一方百姓于此。老朽才在洪灾中捡回一命,以图来日报答。不料此去经年,重逢恩公却...相去甚远。”口吻流露伤感。
听此言到勾起些往日碎片,随意漂泊多年,有些事早已抛诸脑后。未曾想这兰芝入室之地,却是旧日之景。
将杂物置于脚下,顾不上其他忙将弯腰欲拜之人扶起。“福伯莫拜,不过往日小事。折煞我也,我进便是。”我除去外袍放在廊边,再脱下鞋袜方才踏入室内。
一路走来未见旁人,也大致明了此处破败,早没了香火。可入室未见一丝凌乱,窗明几净。三两蒲团整齐摆放,小桌放着几块粗陶小碗,旁又置着茶炉内里是新添置不久的普通木炭。
规整,也处处透着寒酸,我不免心下触动。
当年,若是当年愿继续为世道奔走,为百姓谋福祉,不心灰意冷遁走江湖,一门心思为民生专研。这沿路哀鸿遍野,插萸卖亲等事,可能避免?
可我已疲倦,世道如何,实不该是我一流浪儿背负使命。此番不过想找一埋骨地,了结一生罢了。
**
我跪坐蒲团上,才叫人看清面容。眼下乌青,面色在日头下呆得太久泛不正常的惨白,脸颊瘦削,隐隐开裂。一双桃花眸料想也曾明亮如斯,却从左眼旁疤痕丛生,如枯朽树根上干脆杂乱的树皮,映衬得整张脸泛着狰狞死气。
福伯见我模样也面露惊色,只一眼便敛下情绪用粗陶小碗再为我斟杯:“乡野粗茶,是午间沏下,公子您请。”
也难为老人家,见我着般面容。我双手接茶,面露苦色:“未曾想您竟认得在下...还是莫唤公子,残破身躯经不起这体面词,一声清源便是。”见福伯愁容满面,又欲起身叩拜。忙抬手拦住,继而说道:
“当年事不过职责所在,您无需挂念多年。公子清早已不复存在,某不过一流浪儿。浮游飘零,讨口生活罢了,清源担不起您老的感激。”我将他扶回原位便将头低下。
福伯心间暗叹,那时他是何等意气风发?当年洪灾来得突然,一众老弱妇孺逃难至此。此人一身青衫,开私库接济山民。又在夜遇山匪时,手提长剑沉着制敌,夺回金身。
抱着啼哭小儿细心安慰,掏出怀中糖饼掰成小碎,用手指点着逗趣,取帕一点点为他拭泪。眉目皆是平和,谈吐有度,翩翩若仙。
可眼前人双眉紧蹙、满眼沧桑一点不见当年模样。虽风华不在,那满身气度、周全礼节却叫他一眼认出。
转念细思:他既流浪,不若将他留下,也好叫他有个落脚处。
“清...清源施主,眼下寮房尚有空缺。老朽为您收拾一间出来,尚有一事相求,不知当不当讲得?”福伯寻得理由,抬眼望着我。
我也尽量柔和眉目,轻拢中衣对他点头:“您说。”
听福伯说出山寺破败,他年事已高想找个帮手修缮时。我便猜到其中缘由,但未戳破。左右不过漂泊,在哪停留一段与我而言没有差别。况且,老人一口一个恩公...便当是做件好事。
**
山泉清冽,我倚靠于水中水块边清洗身子。斗笠包裹一并放于房中,寺中自然无其他衣裳。福伯不知从哪拿了件僧服嘱咐我换上,又拿几贯盘缠让我寻个好天去赶赶集,购置行头。我领了衣裳却推诿着不接银钱,又将钱袋推至他怀中便按照指引将自己收拾体面些。
原先自在惯了,也无所谓周遭目光。索性蓬头垢面过着,但有老人在自然不行,平白惹人伤心。
休整一夜,便起了大早在山寺转悠。将需修缮之处一一记下,才去寻福伯定了要紧处。其实败落多年,真要整改起来是项大工程。左右就我与福伯二人,许多地方没必要。
虽是借口,却也是件要紧事。屋舍年久失修,总有些隐患,怕他伤着。我走后也无人照应,便是顶顶困难。
这日简单修缮几处却被瓢泼大雨喊停,只得歇下手中活回屋等待。
福伯虽是俗家弟子却也讲究斋戒,是以这段时日我也随其身后一同用膳。许是几日相处,二人熟稔不少。他也不再拘谨,试着与我话家常:“清源施主,您...可曾想过再此长留?”他说完便觉得不妥,不经意用手挠了耳后,补充道:“怪老朽多事,想多嘴一句。”
我本无家可归,天地之大也无我容身之处。此处安生,却不是我的归来处。
每每闭眼是金乌大狱、是房梁悬尸、是含恨而终。心中隐有不甘,也有愤恨,恨人生毫无意趣却总觉有要事未做。
思来想去,所为何事?世人皆弃我而去,我又有何事须做?我未曾想通,为这一点挂念四处流浪,却也累了。
...
不知作何回答,只接过汤碗再为他盛一菜汤:“您多吃点。”岔开话头,他也讷讷点头,未再提此事。
**
未曾想,确是离开不得。夜半偏殿漏雨,福伯独自挑灯前去却踩空滑倒。听声响我才知出了事,顾不得其他径直冲进雨中。
雨点汇集连绵,织成一张滂沱大网。冲刷着青石板,一下一下砸在他的身上、头上。福伯披着蓑衣仰面倒地,已有混沌之态。嘴里呜呜咽咽含着疼,我走近后却不敢立刻碰他。
顾不上遮雨,忙上前检查。有斗笠护着,未摔到头已是万幸。却不慎断了腿,我只得寻了木板,将衣摆边沿撕下。为他做个初步固定,才将他抱回里屋。
梳洗一番后,又取了生姜红糖就着炉子煮了些驱寒茶,一点点喂他喝下。夜半时分山间偏僻,寻个大夫亦是难事,何况福伯此刻身边离不了人。
我走回屋中换了身利索衣裳,便守在床前。
一夜凶险,却也安然度过。可这腿伤拖不得,按脚程算去请大夫来回便是大半天,拖得太久。
思来想去,先熬了白粥连碗一块端入热水盆中扣着,放于床头。又给福伯留了字条,在天光泛白便入了山林。
归来时人将将醒来,费力撑起身子偏头咳着。
“本想让施主有处安宁,不料成了拖累。实在对不住您,又救了老朽一命。”到底上了年纪,此番说完又费力咳嗽,手也无力垂在身侧。我拿着碾碎的药草坐在床边,对上他泛着灰败的眼,一边为伤处敷药一边宽慰道:“哪的话儿,不论是谁都该救的,此为人之根本,无需多谢。”
此次入山着急,顾不上太多。山林不比寻常小道,总有些荆棘野蛮生长。脸上泛着绵密痛感,上手摸了把不出意外的见了血。
本就面目狰狞,这副尊容未免有些冲击,但药未上完也无法作那劳什子的清理。只能尽量侧开脸,低头说话。
福伯早便见到,却被咳嗽堵了话头。见我眼中闪躲,不知怎的竟哭了。他哽咽着用手背抹泪,“恩公是个顶个的好人,怎总受他娘的狗屁世道磋磨?那日见您,老朽心中便酸涩的厉害。您在老朽这是个神仙模样,可不因这皮囊受损便丢了仙气。”
我听这话有些乐了,哭笑不得地回应:“您这话说的,可别再哭了。”说完微微举起双手,“两只手都忙着呢,没法儿给您擦擦。”
老人依旧将哭未哭的模样,我心里久违的破了口。手下动作不停,嘴里也麻溜解释着:“这疤...不是遭了冤家,是自个儿划的。”
我将左脸侧向床边,做了舒展模样,将那伤疤完整暴露在他面前:“您看,这边上还泛着青呢。早年入了狱,免不了一顿磋磨,被刺了字。后也算熬到头了,也没再做官。可每每见这辱人的腌臜东西,总会想起些不好的事儿,索性拿刀划了。”谁不在乎皮相?但比起那耻辱印记,他宁愿生生划开,将陈年往事中那些个辱人场面从脑海里消磨。
当时情况会比所说更屈辱些,吃人的世道,为民生是错,冠以清廉二字便是错上加错,自然成了旁人眼中钉。
定罪之物不过是轻飘飘几页诗集,再加上恶意煽动几句捕风捉影之词,被御史台搬出大做文章。"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察事,或能牧小民[1]"便是狂妄自大,不尊朝廷。更有荒谬言论指我不尊同窗,蔑视王法,有辱圣贤。
再加上胡乱扣上几句罪名,数罪并罚便让我不得超生。年轻之时,到底天真了些。不断上诉,盼人主持公道。
我到底不孝,全了自己那所谓道义。母亲劳郁成疾病死家中,父亲为我四处奔走,散尽家财,最终不堪背负恶名吊死于房梁之上。
可笑我为人二十余载,为官三载。为国之兴盛而寒窗苦读,为民谋福祉,做尽好事却连拾骸骨都做不到,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
我曾出轻狂言命数不由天定,职责使命所在便让我一往无前。可我输了,输得一败涂地。
...
从过往樊笼中抽离出,我继而笑着说道:“这疤是骇人了些,但小可心中痛快。您不必过分忧心,男儿不在乎这点身外物。”
福伯不知何时忍着痛,撑着身子将自己坐得板正。对我双手合十,行了一礼:“旁人不知,可如某这般受您庇佑之人心中门清:您有大义。”
“哈哈哈哈...”听了这话却笑得开怀,眼中带着癫狂。
“一人之力不过螳臂当车,现下正乱着,那些个仁心侠义,到底与我无关。”已经包扎完毕,我两手一摊,卷起的衣袖自然垂下。
我自顾自笑着,可福伯却不忍心撇过头去。深吸口气,似在回应着我:“虽然您只字未提,老朽却已明了您的苦楚,您所做之事并非毫无意义。譬如当下,您只身入险山为老朽这条贱命奔走。譬如当年,您以一当十夺金身,救人质。同寺中僧人安置老弱妇孺,让可怜人有了容身之处。这一桩一桩皆是善缘,那些人想必都同吾这般寄挂着您...”
“佛曰不可说,万事皆有因果。错在世道,您何错之有?”
我听完此话,久久未言。只拿起盆中白粥,一口一口送入福伯口中。
**
福伯腿伤一时半会未能痊愈,我便看顾着。伤草已然见底,我带上背篓再入山林,顺道带些寻常草药回来,防着再出岔子。
归来时却带回一昏迷男子,已陷昏迷口中却不知呢喃什么,隐约听似快逃...
遇上这事本不欲救,更何况路过时,我观那蒙面众人围攻架势和那男子视死如归神色,料想是做好见阎王的打算了。我非善类,又何苦凑上前做那无私菩萨。
但数十步后,还是暗叹自己多管闲事。卸下负担,抽出腰间软剑疾跑上前。那人本是强弩之弓,打斗之时隐有颓势。步法虚空,肩颈、手臂泛着红,顺着指尖滴落在地。见我上前,先做防守姿态,却失了气力直直跪下以剑撑地。
其余几人见此态势,正喝一声欲取他性命。我顾不上其他,纵身一跃发起攻势,剑身甩动如钩逼向黑衣刺客,堪堪切过咽喉。
“酒肉和尚莫沾江湖事,速速退去!”似是众人头领,冲我喊话。
我不欲伤人,只向后仰头脚尖倒挂踢向几人,又集中臂力甩向侧方一人,划过下腹。虚晃几招,将那男子护在其中。
“哪来和尚?你爷爷头顶长毛莫是认不清?给小爷滚。”我散开衣袖,除去外袍丢于一旁,从怀中掏出白色粉末洒向众人,引得几人速速后撤。将那男子虚扶着向隐蔽处藏。朝南北两角各掷一石块,作声东击西之势。
喘息片刻,便手抚他脖颈,探其鼻息。鼻息尚存,颈上动脉跳动如斯。这才松一口气粗略止血后将人背起,寻回草药往山下行。
踏过山门疾驰向里,到殿前才缓下步伐。绕过钟楼,直奔寮房。但脚步再轻,依旧扰了福伯清净,如今他腿脚不便大多在卧房歇息。
听他换我,恐其不便赶不得褪去血衣就抬腿迈向房门,行至其间才醒得一身血腥就顿住脚步立于门侧。
“施主可是受了伤?”福伯语气焦急,听到几声动静我恐他摔倒,才叹了声走进屋中。
“福伯,小可未曾受伤。只是采药路上救了一人,私自做主带回寺中安置了,找您请罪来了。”
他坐于床前,将我上下打量数下才放心微微塌下脊背,倏地抬头:“这是哪里的话,带回之人可好?是受了什么伤?”
他指向床侧柜子,“二层抽屉放有些金疮药,连着底下药箱一并拿去为其疗伤吧,若有需要的再来找我。”
我来不及开口,就被福伯丢下一句切莫管他救人要紧,催着快去看看那人。这老人家,几日前还一口一句恩公,慌诚惶恐,如今到是有了长辈模样,舒适不少。
**
那人面色发白没了意识,只能听到微弱喘息。我恐不妙,速褪去衣衫查看伤势,心口腹部无致命伤,只是流血过多。见其颧骨凸起,眼窝隐有凹陷也料想是逃难多日。我观其剑势如虹,应是个中好手也不知惹了哪股势力。
“真是好运,凑巧遇上我。”
药粉中掺了软筋散,林家以医药圣手之名扬天下。若不是我舍不下恻隐之心,想来也...我有些恍神,药粉洒偏了许多。听到那人闷哼一声,却也没有醒来。
为他擦了身子,又换了一身利索衣裳,我才往山泉边行。不料归来时那人已醒,欲挣扎起身。
“若想牵连我再为你包扎一回,你便尽管乱动。”我将脏衣扔在一边,跪坐蒲团边睨着他。
那人果然止了动作,又睁眼打量四周。见我不理睬他,自顾自端着粗陶碗提壶倒水时,踌躇片刻才开口:“...师父?可否给口水喝?”我半挑眉梢,换了个小口陶杯调成温水才递给他。见他双臂包扎,也就坐下将人托起一些喂了水。
不知是我这般面容吓坏了他,还是如何。他瞪大眸子直勾勾盯着我,咽了几口唾沫又说不出什么。我不喜他人这般直白目光,哼的一声收了手起身坐回原位。
开口讥讽:“怎的,有话便说?”又转头补充一句,“我非僧人,不必唤我师父。”
他双眉紧蹙,似陷入回忆。未过几时,才回过神来,不确定开口:“侠士有些面熟...可否冒昧问声名讳?”他侧头看我,眼中隐有激动。
瞧他这副神色,我也回首细细打量此人确信并未见过,这才开口:“甚是有趣,问我名讳却藏首畏尾不自报家门吗?”
他犹豫片刻,对我行江湖抱拳礼:“在下张启,见侠士风骨肖似故人,方才唐突。”说完,眼神却丝毫未从我身上移开,与我对视着:“您可是苏北林氏...那位?”他说的隐晦,当年那事一出便沦为笑谈,哪有人记得苏北林氏妙手回春救了多少人。
我把玩衣摆,避开目光随意问道:“苏北林氏...何来此家?我无名无姓,流浪儿罢了。”脑海中再次闪过过往片段,确信未见此人不欲多谈往事。
“我曾与您有过一面之缘,有幸拜读过您的《晁错论》,那句‘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於不可救’至今不敢忘。”那人言语谦卑,语气笃定[2]。
“治世之道与我无关,我无心寄挂。公子清也好,苏北林氏也罢早已不复存在。”我下意识甩开衣袖,却忘了沐浴归来未着外衫,有些许滑稽。
见我不欲多言,张启自行止了话头。一室寂静,我虽欲离开也得顾及伤员。
“此为隐山寺,寺中仅有你我与一位俗家僧人。亏你命大,我为他采药才将你捡回来。你可在此养伤,但伤好便走。山中人不问世事,莫搅了这份安宁。”
其实我知,恐是再无安宁。说完才对他点头示意,在房中翻找来时旧衫披着便去了福伯那里。
**
福伯如今腿脚渐好,但尚未拆板到底行动不便。我去时他正前倾身子够着床沿边,不知做些什么。我快步走至他身边,虚扶一把问道:“您悠着点儿,需要拿些什么与我说便是。”
他对我摆手,又坐回床中:“怕您一人没法应付,正想拿拐出屋看看。”他引我坐下,又仔细问起那人情况。
“已无大碍,但需将养几日。”我一一回答完才为他掖好被子,复又说着:“您无需过分牵挂,我守着您。”福伯听此话稍顿,随后面带喜色却未多言。只拉过我的手,笑了满怀嘴里念叨几句琐碎。
屋舍藏于树荫之下,鸟雀虫鸣之声未绝,却掀不起一丝烦躁之意。偶尔有风吹过,树影婆娑,卷过池边水汽衬得此景惬意非常。
正与老人话家常,却见门外传来细微声响。我止住话头,敛起眉目侧耳细听,几息后才递给福伯一安抚眼神,抽出腰间软剑夺门而出。
不料庭中有一身量矮小男子徘徊,披一身短褐,颧骨突出唇色发白,脸颊脖颈处黑灰一片。见我持剑立于廊下,眸子微闪却沉下脚步朝此处做揖,“误入山林,冒昧进此间,实在抱歉。”
此人言辞诚恳,神色谦恭。尚未开口,屋内有声传出:“施主若不着急,可在小寺休整一夜。”
他瞧我一眼,右手抱拳内,屈臂成圆于胸前行一江湖礼,未见俱意:“实在叨扰!”既福伯说留,我不好开口,收拢剑锋回以右礼。
“汝稍等片刻。”说完才回房内,福伯支着大半身子费力撑起拐杖,见我愁眉未展,尽力蹬直右腿朝我招手:“既是迷途人,误入佛门合该照应。”
我忙起身将他扶回床沿;“您且顾好自己,其余交由我来便是。”寺庙修缮,没有太多空余房间,何况刚救回个拖油瓶。
思索片刻,将人带至禅房。又在福伯指引下找了被褥,放在一旁。那男子施一感激笑容,行至门边左右摩挲手掌沿着袖筒边沿掸灰,棕黄色下裤上绑带缠绕,崭新如斯。
“寺庙清修,只供朝、哺二食,我于申时送于此间。”说罢欲转身沿石板路离开,远处墙皮脱落,角落青苔沿墙缝而生,周围一片黏腻湿滑。我回头补充:“山寺年久失修恐有危险,若无事切莫走动。”
却无意瞥见门外一双黑色云靴,尖头厚底无一丝泥泞。
今夜月沉,只余浮光霭霭。我屈身倚于福伯廊下柱旁,环抱酒壶百无聊赖地盯着大麻烦所在屋舍。果然,子时未过便见人影晃动。
那瘦小男子未燃火折,在窗边摸索几下探入一孔,吹进迷香。掏出黑巾掩面,正待时机。耳边破空划过异响,连连后退几步掏出怀中匕首,警惕非常。不料空中一人洒下白粉,又被那人近身扯开面巾。待回神时,已有利刃架于其上,却失了浑身力气反抗不得。
我啧啧三声,原以为此人有两把刷子不料三两下就被药倒,像个软脚虾般被我收了凶器掂在手中。“本不欲多生事端,已出言警告。此为佛家之地,莫将劳什子腌臜事都参合进来。”
不料得意过早,此人出手直击下盘,复又补上一脚,惹我痛呼一声将其掷于一旁。趁此期间,欲遁墙而走。
我强忍痛意,紧跟其上。跳墙而下,往林间行。眼见身影消失,用了几分力道甩出匕首。只听一声闷响,却在树影庇护在暗夜掩护下如鬼魅潜隐。
我提剑前去,那人还是慢了一步。又落入我手,“若我想取你性命,不必费口舌与你周旋。”
那人眼见无路可走,啐我一口。哼笑说道:“要杀要剐自便,我无话可说。”
我谨慎许多,抽出腰带将其牢牢缚住。“我无意杀你,说完便放你走。”
“那人在寺外若要打杀只凭你们本事,但在佛门之地若造杀孽,别怪我不留情面。”说完,将利刃靠近喉间一寸,又靠近些许:“你可否明白?”
心里却知,躲不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