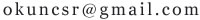红豆生南国
也许是缘于入春,杭州这几日不停地下雨,让人没个安歇。雨珠不住轻落,行人经过,断了线的珠子便刚好从一簇红豆跳到一人的伞面边缘。
不同于京城的拘谨,更不像边疆人的粗俗,江南属于一隅净土。伞上虽落了雨,衣上虽沾了清,那人却不恼,只是缓缓抚走了肩上的水珠,继续走自己的路去了。
却不像夏梅那样,一下能浇个透彻,贺朝没多喜欢春季的雨,缘由也简单,过了惊蛰后,人间本该回暖,却因一阵风雨来,又冷下去。
就像现在他的处境,本来应该随便找个地方混吃等死,结果被教书先生鄙视了个完全,见他吊儿郎当的样儿,说:“你这种人,还有什么用?”
他把老师打了。
然后不知怎的,又得转所学校上课,真是气人,他心里闷闷地想,倒离书院是不远了,估摸着只差几步……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贺朝一愣。
空谷幽兰、昆山碎玉、长白池泉,单独吟诗的字句清晰,不染不妖,雅致、有力、绵延、清澈。
没有词可以形容完的声音,就这样实实地撞到了他。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随着那句清脆的音落下,一群稚嫩的童声齐齐诵道。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透过淡色的绵雨,透过扑簌的枝条,透过春季独有的淡致的空气。
学馆的先生看着年轻,估计与他是差不多的。皮肤很白,嘴唇随着一字一句微动微阖。手腕、手心、指尖,指甲修长却无女感,将整个人衬得冷冽又分明了许多。
一纸冥烟雨,悠然入我心。
谢俞正上着国文课,隐约听见学馆外的“簌簌”声响,下意识地朝动静传来的方向一偏头。
四目相对。
贺朝怔神,片刻后才用懦懦的语气开口:“李商隐的《红豆》?”
“王维,《相思》,”谢俞心道这人看着快二十岁了,脑子却不太灵光,自己凑了个诗名不说,还能将王维和李商隐搞混。想来应该是前些天被另一所学校开了的贺大少,于是谢俞正了色,只问了句,“今天要来的,贺朝?”
温润的嗓音,冰冷的语气,放在他身上却没有多违和,反而更显风雅,贺朝这样想着,嘴上不知廉耻地说道:“没想到先生知道我,贺某三生有幸啊。”
一个月前伸手可以打教书先生,半年前一句话就包了西湖游船,两年前又疯疯癫癫地在雨雪深冬去跳没结厚冰的湖。
无人不知贺大少。
“嗯,你坐在后面那个位子上。”他抬手指了指最后端的桌子,淡淡地道,好似眼前的人是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学生。
在谢俞刚要回身时,贺朝直接上手拉住他的衣角,还小声问:“我眼睛不太好,能不能坐前面些?”
谢俞只应了声“嗯”,又指向第二行最旁角的位子。
贺大少是坐不住安不下的,刚坐到自己的位上,又戏谑道:“先生就不怕我一拳头上来?”
“不怕,”他轻拂了下自己的袖子,“你打不过我,所以劝你珍惜生命。”
这会儿,谢俞看了他一眼。
稍纵即逝,便转身授课去了。
时近春分,天近暖,这几日阳光灿烂得很。
正好放假,贺朝在谢俞的书房里坐着,几日下来,他倒是发现这个教书先生刀子嘴豆腐心,混熟了之后一点都不用怕,这时正恳求地道:“先生,能否出去放风筝啊?”
“你去吧,我也没拦你。”谢俞答完,又提笔写字去了。
桌上宣纸平摊,砚台方然,笔在砚上刮了几口,又轻慢地落下,一直到了纸上。
窗棂映进来几缕阳光,和纱窗的影交织混杂在一起。
“先生,谢先生,”贺大少就蜷成一团,上半身趴在案上,“谢俞,我们一起出去吧,外面朝光正好,适合放风筝的。”
谢俞刚写完一个字,停下笔,想着这词是写不好了,说:“不许直呼师长的名讳。”
“你比我还小一岁……”
“走吧。”
“干嘛?”
谢俞没答,外头的阳曦确实艳极,春季的东风彻底消了冷意,只剩一阵阵的昕暖。书院前栽了一树红豆,此时随着暖风扑簌着一隅的叶子,声响纷纷。红豆下一方石桌,杯盏俨然,估计是谢俞小憩时放的。
贺朝揣着纸鸢,一撒一拉一放,那风筝便飘扬在空中了。这会儿看去,活像一只飞燕在低空中盘旋。
谢俞站在一旁,双手抱臂,视端容寂。
“谢先生,你看我放风筝帅不帅?”
谢俞随手拿石桌上的瓷盏,抿了口发凉的茶水,边敷衍地向耍帅的贺大少作答:“好看。”
“有多好看?”
“让我觉得,你这样的性子,实在可惜了你这张脸。”
口齿伶俐,贺朝心道,嘴上却没说什么,只是一步步迈向先生,一把将他拉起。
“谢先生,别坐着啊,起来晒晒太阳。”他拿手攥着谢俞的手心,直把人往外带。
不巧,顾这忘那,一阵说不上大的风吹过,却直接偷——不对,是掠走了这只纸鸢,贺朝还想去抓,结果这风忽大忽小,最后成功掠夺,走了。
只留下贺大少风中凌乱。
噗。
“谢先生,你笑了。”
“没有。”
“明明就有,谢俞你别蒙我哈。”
“没有。”谢俞神色依旧如常,心底也早就平静下来,作势要回身,结果被贺朝拦住了脚步。
他拿自己的手紧攥着谢俞的,随后变成一只手钳制两只的情形,贺朝又抓着他的手往里拽,一把把人推到院里墙上。
“谢先生,”他故意往先生耳朵旁哈气,等人耳根泛起一层粉红——朱红加上皮肤白的颜色的时候,才说出下一句话,“帮我写个字儿呗。”
没想到,平时文静儒雅——是冷到极致的谢先生直接挥拳招呼他。
“诶,谢先生!谢俞!老谢!”
贺朝没还手。
好了,莫约一刻钟后,书房里坐下来两个人,一个伤痕累累,一个清闲如斯。
“你要写上什么字?”谢俞还是一脸平静,好似刚才打他的不是自己似的。
“帮我写首词。”
“你说来。”
贺朝靠到案前他肩旁,一个字一个字地说,谢俞便一个字一个字地写。
“晓看红枝沾袖枝。怎知俞叶寄青丝。朝光正好,汴水信笺迟。
红豆引君无断绝,一蓑烟雨浸江莳。君何知也?”
是首《相思引》,谢俞把他说的字一一写下,罢了,只是直勾勾看着他,仿佛在问“最后一句呢”的神色。
“嘶——嘴皮真痛,老谢你下手轻一点啊。”贺朝故意吸了一口凉气,好似——不必好似了,就是想让谢俞看看自己伤得多重,也没有真想到什么词句。
谢俞又冷眼瞪他:“谁教你你能这样不尊敬师长的?”
“我、错、了。”
“我自己写了。”谢俞说完就往宣纸上落笔,终于是完成了。
“此物最相思……谢先生引用得好啊,怪不得那么受,各位学生的喜欢。”
谢俞的嘴角抽搐了下。
然后,那张字被裱在了学院的墙壁上。
孟夏正是草木盛长的时节,蝉鸣蛞噪,鸟啼千转,好似在闹中取不得一点儿静意。
可是对于贺朝,窗外喧嚣似乎并不起甚作用,近来几日都是困极,像没睡觉的样子。
例如今天。
谢俞背身吟了一段岳帅的《满江红》,音色没被夏季的暖阳感染多少,只是寒气中还透着十足的中气,却是一种独特的悲壮。他转回身时倒是关心起贺朝来——这学生习写算术皆不在话下,又识诗词绘画,也不知是谁传说“贺大少青年时不习不学、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
结果是,他瞥眼,发现贺朝第一次在自己的课上睡着了。
少年这会儿正趴在桌子上,同桌见谢先生看过来,欲要拍醒他,却被谢俞一个“嘘”的手势止住了。
谢俞嘴上继续讲课,抬脚却是踱步走向贺同学的位子,只一倾,拍了拍他的身子,口里也不讲课了,而是低声说着什么。
贺朝在这个觉里做梦了。
他梦到自己被骂,上个学院的先生姓徐,女的,生得不叫亭亭玉立,说得不能出口成章。
还有什么来着?
嗯,应该跟她解释,自己是为什么在课上睡着了的。
“你这种人,能有什么理由?”
“不是的,我是因为……”
“快点回去,我担不起你这种学生。”
什么叫“你这种人”?
斯时,谢俞不语,到了下课便让学生们嬉戏去了,他见贺朝紧蹙着眉头,喘息声重得吓人,想叫醒他。
“贺朝,你先醒醒。”
贺朝却还在半梦半醒之间,这睡得确实熟,谢俞都要怀疑自己的威严了。只听见贺朝道:“啊?先生,不好意思,我……您别让我退学就行。”
“你理应有很多学校供选择的,先把原因说了吧,要么你再休息会儿,下节课不重要,你会了的。”谢俞神色还是平静,却在语气上明显暴露了一丝关心来。
贺朝一怔,随即醒了神,没什么解释,只道:“没什么原因,谢先生,我就是有点累,夜里睡得晚了。”
“近来有心事?”
“谢先生,你把手伸过来,闭眼。”贺朝没解释,只是轻声唤他。
他照做。
手腕上轻落下一串东西,因视觉无用,其他感官变得异常敏感,故而有点痒,他也没计较去了。
圈住手腕,又是轻系起来。
“好了,可以睁眼了。”
是一串手链,斯时正系在自己的手腕上,绑的时候留缺,并没有勒痛感,配上绳串的深红,衬得手腕更白皙了些。最漂亮的点,在手链上吊着红豆,为两颗。
这时,是民国二年五月十一。
“就为了这个?”
“嘿嘿,先生,我串了好久,你就不能说句谢谢吗?”
“如果再拿休息时间弄这个,你等着被退学吧,”谢俞还是一脸的冰冷,贺朝却是听出了关心,然,谢俞又补了句,“以后不必给我送礼,身子总比交往重要。”
再后来,学子们都有一个挺好奇的问题。
谢先生怎么一直戴着这串手链,从未换过呢?
民国三年十月廿九,小雪。
尚且天冷,江南虽不下雪,可现在天晚,加上一场纷飞零落的雨,还是让谢俞不由得打了个喷嚏。
按照学习情况来看,贺朝到大雪时就可以升至北京大学了。
他放下茶盏,没说话。
屋里没点灯,窗外雨潺潺,黑云翻墨,乌压压的一片,无甚光亮。
谢俞起身,努力让自己不去想他,心底里却像缺了一块,冬风过隙,让人忍不住一哆嗦。
盯着窗棂的旧木看了会儿,正抬眼时,窗外却飘摇过一星点的火光,他捻了下木围,看见那人是脚步踉跄的贺朝,才撑上油纸伞,跑过去。
这人一身酒气。
“贺朝……你喝酒了?”
“没,谢、先生,我好、想你,”贺朝嘴上越发不利索,语句结巴,声音也轻,混在细细密密的雨声里,听不大清,谢俞把身子靠得更近才闻见,“我不想、离开先生……”
哭了。
他持着略显沙哑的嗓音轻声道:“你还是,快些走吧。”
贺朝只是倾听到他的犹豫,倾了身子,拂了衣尘。
又是一年春好处,今年春意虽减——自然是因为军阀间战乱而致的,不过身处临安,是没太多顾虑。
谢俞持笔落墨,只是挥毫,不兴时,纸上便现出一首诗。
雨坠在枝头
褐色的盘虬挂满了银绸
我望向一树的梨花
它们洒来一片的清香
不消时
铺了满地的涟白
雾蒙蒙
雨濛濛
春弃寒来暖蓬篷
不计春来暖未还
心中自有春欣然
民国五年四月二日,
谢俞于院中作。
一树梨花落了雨珠,显得柔和青翠了些,又有欲坠之意,几番拍打,竟是真的打下几只清香。
谢俞无心作什么葬花的矫情事,只是触景生情,绕回刚才想到的战乱,又想起贺朝来。
贺朝自然不会做什么卖国求荣的肮脏事,却是怕有小人用计,他又这般冒事,令人不能不担心。
再抚上那串手绳上的红豆,却是缄默无言了。
他坐在石桌旁,本想细抿一口茶盏里的龙井,不曾想刚赏花作诗的时间太长——若是正常人喝茶,杯底都不知亮了几次,他这一口,又被冷了个哆嗦。
“凉了就再泡杯来,我带了些茶叶。”
谢俞闻声一惊,刚要转身,却落入一个怀抱,贺朝将头靠在他的肩头,拿未锢着手套的右手抓着谢俞的手腕,食指正好碰到那链手绳上的红豆,喜色依旧。
“谢先生,我回来了。”
“贺朝,进门烧些茶去。”谢俞倾身,示意他跟着自己进去。
几年不见,学堂——然,一年前就不办学堂了,现在是谢俞的草堂,不过没太大变化,只是自闲下来后,谢俞变得更爱养些植株,院外种的红豆新生,迎春盛放,桃花含苞,海棠抽芽。
贺朝踏过门槛,嘴边道:“小园春色染春光,四季芬然诗满章。”
“这时候怎么回来了?”谢俞静静听他感慨完两句,问道。
“战乱纷繁,怕殃及江南,临安这带就由我领下了,”他清了下嗓子,极郑重地说,“谢俞,你可以叫我——贺帅。”
“哦。”谢俞听完敷衍应下,还不轻不重地掐了下贺朝不知不觉就攀上自己手心的手掌。
“目前来看,还可以安生一段日子,你最近要是遇上了不顺的事不顺的人,就像那些叛国贼一样的人,我帮你教训他……”
“滥用职权,”谢俞面上依旧没什么表情,只是眼底里漏出了些笑意,而嘴上直接打断了他,“我没有什么仇人,你若要打仗,可别殃及百姓,还有,需得为他们多做事……”
贺朝一一应下。
“最后,惟愿你平安顺遂。”他解下自己手腕上的红豆手绳,将贺朝的袖子往上艰难地提了提,将那串明红色轻系在他手腕上,“是我新做的,送你了。”
不错,红豆是新生的,穿绳倒是没变,依旧衬着红豆,一阵静好。
“那你呢?”
“这不是你负责的吗?”
贺朝故作讶然,随即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个木匣子,还带着一丝丝的松香味。谢俞打开,果不其然,是一串崭新的手绳。
“那我明日辰时再来找你,谢先生记得给我留早饭啊。”
“嗯,桂花糕。”
第二日,他果不其然就见到了桂花糕。
棉白色的糕身,洒了糖浆的鼓包,撒上黄桂花和黑芝麻,精致得很。
“我自己做的,你且吃着,不好吃的话……”
哪知贺朝睁亮了眼睛,夸赞道:“好吃!已经有两年多没吃过这儿的点心了,先生你做的太好吃了!”
“你喜欢就好。”
“先生,以后可不可以去我营里送些吃的,万一忙得脱不开身,也有东西解馋。”
谢俞应下。
“每日辰时去送。”
谢俞穿了件白底青纹褂,拿着几层盒绿豆糕,这会儿徐徐走来,像是带了一场细密的春雨。
“您好,我是谢俞。”
“谢先生啊,您请您请,将军在里面等您好久了。”战士将他恭迎进屋里。
贺朝穿着一件军衣,此时像是无心脱下外套,手上抓着钢笔,微蹙着眉,眼前摆着几张报纸,看见什么便起笔划线旁批,好似没察觉他的到来。
谢俞故意踏了几步。
“茶水放桌上就行。”
谢俞无言,只是轻步着到他的桌旁,指着报上一处注记道:“这处的字还是差了,还不算深思熟虑。”
贺朝见一只白皙手掌顶在报纸的那处批注上,一瞬的愕然,一瞬后却作虔诚状,洗耳恭听了。
“先生怎么想?”
“你看,此军若是从湖州攻过来,比起在塘栖作战,我们在半山,也就是皋亭山开战是损伤最低的,然,无论从人命还是文化上。”
“可,我们的军队不适于在山林间穿梭……他们又是亲日派的军阀,怕是有什么枪炮等的重火器。”
“自然不是要这样做,我们只是将敌人从半山引进,若能引到塘栖附近,便看他们有没有那个胆子了。至于枪炮,山谷中不能发射炮弹,也不宜用什么重武器,如若他们还是炎黄子孙,就不会在城镇放炮。”谢俞倾身,示意他给自己拿块绿豆糕。
“从引诱到包围,谢先生,你懂得好多——”
谢俞只咬了几小口,慢慢咽下去后才说道:“切记,百姓人家绝对不能受伤。你一定要平安,岁岁平安。”
贺朝同他交换了眼神。
很深的一个眼神。
谢俞到底是位教书先生,到了谷雨时节,有学生邀他吃顿饭,就在草堂附近。
贺朝这几日已经启征,他无聊得很,顺便念在情分,谢俞总归是去了。
“所以,你花那么大的排面把我请来,是要做什么呢?”谢俞望着一桌子的菜肴,没有动筷。
跪倒在地上的学生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始哭喊:“谢先生,对不起,我是真的没办法啊。如果我不答应,他们就会杀了我爸妈的!”
谢俞还是穿着纯白配水绿色的马褂,脸上不曾流露一丝神情,只是沉声讲道:“我怎么不记得自己教出过这样的学生?我不怪你不会审时度势,但你如此离经叛道,与外国人勾搭在一起很光鲜亮丽吗?你不应该向我道歉,你应该向你身上流淌着的血液说对不起。”
谢俞这才注意到一旁还坐了个日本军官。
“还跟他废话什么?直接送到那姓贺的领帅那去,给他看看我帝国的计谋。”
谢俞没法听出来多少,见他如此,开口说道:“如此无礼,就是你们一个疆域辽阔的‘帝国’做得出来的行为吗?”
那学生哪看过他先生真的愤怒,被吓得腿软,差点就不敢跟那军官翻译了。
“到了哪里我就是哪里的规矩,把他抓起来。”
谢俞被几个人共同钳制住,欲要挣扎也没气力,结果一人直接抓了个针管打到他的大臂上。一会儿便不省人事。
“还是麻醉方便……”
再醒来时,眼前却是同样的中国人的脸。
“说,那姓贺的到底要用什么手段?”
“不知道。”
那人折了下鞭子,一下,凌空的风啸声,结结实实地打到谢俞的肩上。
是贺朝最喜欢靠的左肩上。
“你说不说?那厮到底要用什么计?”
“我岂能告诉叛国贼?”
“啪。”
又是一下。
又是一下……
直到谢俞的血液已然布满全身,身上骇然的伤口共十四道时,狱卒——倒不如说是刽子手,又问了一遍。
“你到底,说不说!”
“你靠过来些。”
那人真就靠了过去,谢俞倾了身子,突然就抬起没受缚的右脚,实实踢在胸口,没留一点余力。
“呵,我告诉你,你从我这里套不出任何情报,痴心妄想还是留到来世再做吧。”谢俞轻蔑一笑,在笑这种狺狺狂吠却要为自己狡辩的垃圾。
狱卒终于忍不住,直接放下鞭子,朝血肉混凝在一起了的谢俞走过去。
手指尖传来的刺痛连通心脏,像是绞死自己的那种痛苦——那人要把指甲和手指分开。
“咔——”
“啊——”谢俞叫得撕心裂肺。
“咔,咔,咔,咔。”
在黑暗中,谢俞手腕上明红色的手绳显得极为夺目,狱卒像是欣赏艺术品般满意地望着自己拔掉了指甲的那只手。
谢俞身上血肉模糊,指甲已有一半被卸了,血水汩汩簌簌地往下流,还未落下,就在他身上停滞了。
“我生是中国人
生长在中国的疆域
死后将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
我是中国人
我不会做出叛国的苟且事
我不会被利欲熏心
我不会被威逼而屈
我告诉你
你在一个中国人口中
就理应套不出任何信息
母亲啊,您的儿子
唯愿华夏永在
不可分割,不可分裂
屹立于世界东方!”
谢俞眼尖,早看出狱卒带了刀,一把便抢过,往自己脖子上一架。
民国五年,四月二十日。
谢俞自杀,卒。
贺朝按谢俞的兵计对抗,竟出奇顺利,眼下敌人全军覆灭,已然胜利。
“剩下的士兵,一个不留。”贺朝下令,又陷进无边的沉思中。
“谢俞……”
眼前局势开朗,他却高兴不起来。
如果没有这些罪人,谢俞还会在这种垃圾里死吗?
他命人查探过,牢房也被搜了出来,不过除了血污和浓重的血腥味之外,墙上还有一道刚正的字迹,仅四个字。
平安顺遂。
“谢某无远志,唯愿祖国平安顺遂,不受国内之动荡,不受国外之贬低,华夏永在,不可分割,不可分裂,屹立于世界东方。”
“再,愿贺朝能平安顺遂,永远永远。”
贺朝再也是没撑住,无声地哽咽起来,心底里像堆了一团乱麻,想找人倾诉,却不见故人,饶是更委屈了。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院前红豆随着春雨轻曳,白雨又落到石桌上的茶盏里,不期然,把茶水浸染上了几点凉意。
倒也符合孟春时节的意思。
——全文完——
绛旓細銆婄浉鎬濄嬨傘愪綔鑰呫戠帇缁 銆愭湞浠c戝攼 绾㈣眴鐢熷崡鍥锛屾槬鏉ュ彂鍑犳灊銆傛効鍚涘閲囨挿锛屾鐗╂渶鐩告濄傝瘧鏂囷細椴滅孩娴戝渾鐨勭孩璞嗭紝鐢熼暱鍦ㄩ槼鍏夋槑濯氱殑鍗楁柟锛屾槬鏆栬姳寮鐨勫鑺傦紝涓嶇煡鍙堢敓鍑哄灏戯紵甯屾湜鎬濆康鐨勪汉鍎垮澶氶噰闆嗭紝灏忓皬绾㈣眴寮曚汉鐩告濄傚垱浣滆儗鏅細銆婄浉鎬濄嬫槸鍞愪唬璇椾汉鐜嬬淮鐨勫垱浣滅殑涓棣栧熷拸鐗╄屽瘎鐩告濈殑浜旂粷銆傛璇楀啓鐩告...
绛旓細绾㈣眴鐢熷崡鍥锛屾槬鏉ュ彂鍑犳灊銆傛効鍚涘閲囨挿锛屾鐗╂渶鐩告濄傝瘧鏂囷細椴滅孩娴戝渾鐨勭孩璞嗭紝鐢熼暱鍦ㄩ槼鍏夋槑濯氱殑鍗楁柟锛屾槬鏆栬姳寮鐨勫鑺傦紝涓嶇煡鍙堢敓鍑哄灏戯紵甯屾湜鎬濆康鐨勪汉鍎垮澶氶噰闆嗭紝灏忓皬绾㈣眴寮曚汉鐩告濄
绛旓細鈥滃崡鍥解濓紙鍗楁柟锛夊嵆鏄孩璞嗕骇鍦帮紝鍙堟槸鏈嬪弸鎵鍦ㄤ箣鍦般傞鍙ヤ互鈥绾㈣眴鐢熷崡鍥鈥濊捣鍏达紝鏆楅楀悗鏂囩殑鐩告濅箣鎯呫傝鏋佸崟绾紝鑰屽張瀵屼簬褰㈣薄銆傛鍙モ滄槬鏉ュ彂鍑犳灊鈥濊交澹颁竴闂紝鎵垮緱鑷劧锛屽瘎璇闂殑鍙e惢鏄惧緱鍒嗗浜插垏銆傜劧鑰屽崟闂孩璞嗘槬鏉ュ彂鍑犳灊锛屾槸鎰忓懗娣遍暱鐨勶紝杩欐槸閫夋嫨瀵屼簬鎯呭懗鐨勪簨鐗╂潵瀵勬墭鎯呮濄傗滄潵鏃ョ划绐楀墠锛屽瘨姊呰憲...
绛旓細绾㈣眴鐢熷崡鍥锛屾剰鎬濆氨鏄孩璞嗙敓闀垮湪鍗楁柟杩欏彞璇濆嚭鑷攼璇楃浉鎬濅竴璇楃孩璞嗙敓鍗楀浗锛屾槬鏉ュ彂鍑犳灊鍔濆悰澶氶噰鎾凤紝姝ょ墿鏈鐩告濊繖鏄竴棣栬剭鐐欎汉鍙g殑璇楄瘝锛岀煭鐭簩鍗佷釜瀛楋紝灏辨妸绾㈣眴鐨勶紝绾㈣眴鐨勭敓闀垮湴锛岀敓闀挎儏鍐碉紝鍜屼綔鐢ㄤ互鍙婁綔鑰呯殑銆傗滅孩璞嗙敓鍗楀浗鈥濆嚭鑷帇缁存睙涓婅禒鏉庨緹骞寸孩璞嗕骇浜庡崡鏂癸紝缁撳疄椴滅孩娴戝渾锛屾櫠鑾瑰鐝婄憵锛屽崡鏂逛汉甯哥敤浠ラ暥...
绛旓細绾㈣眴鐢熷崡鍥鍑鸿嚜鍞惵风帇缁寸殑銆婄浉鎬濄嬨傚叏璇椾负锛氱孩璞嗙敓鍗楀浗锛屾槬鏉ュ彂鍑犳灊銆傛効鍚涘閲囨挿锛屾鐗╂渶鐩告濄傘婄浉鎬濄嬫槸鐜嬬淮鍒涗綔鐨勪竴棣栧熷拸鐗╁瘎鐩告濈殑浜旂粷锛岀敤绾㈣眴琛ㄨ揪瀵瑰弸浜虹殑鐩告濅箣鎯呫傚叏璇楃炕璇戜负锛氱孩璞嗙敓闀垮湪鍗楀浗鐨勫湡鍦颁笂锛屾瘡閫㈡槬澶╀笉鐭ラ亾闀垮灏戞柊鏋濄傚笇鏈涗綘鑳藉敖鎯呭湴閲囬泦瀹冧滑锛屽洜涓哄畠浠渶鑳藉瘎鎵樼浉鎬濅箣鎯呫傜孩璞...
绛旓細鈥绾㈣眴鐢熷崡鍥锛屾槬鏉ュ彂鍑犳灊锛屾効鍚涘閲囨挿锛屾鐗╂渶鐩告濃濈殑鎰忔濇槸锛氶矞绾㈡祽鍦嗙殑绾㈣眴锛岀敓闀垮湪闃冲厜鏄庡獨鐨勫崡鏂癸紝鏄ユ殩鑺卞紑鐨勫鑺傦紝涓嶇煡鍙堢敓鍑哄灏戯紵甯屾湜鎬濆康鐨勪汉鍎垮澶氶噰闆嗭紝灏忓皬绾㈣眴寮曚汉鐩告濄傛嫇灞曠煡璇1銆佽瘲鍙ュ師鏂 銆婄浉鎬濄嬪攼路鐜嬬淮 绾㈣眴鐢熷崡鍥斤紝鏄ユ潵鍙戝嚑鏋濄傛効鍚涘閲囨挿锛屾鐗╂渶鐩告濄2銆佹敞閲婄浉鎬濓細棰樹竴...
绛旓細鈥绾㈣眴鐢熷崡鍥锛屾槬鏉ュ彂鍑犳灊锛屾効鍚涘閲囨挿锛屾鐗╂渶鐩告濃濈殑鎰忔濇槸锛氶矞绾㈡祽鍦嗙殑绾㈣眴锛岀敓闀垮湪闃冲厜鏄庡獨鐨勫崡鏂癸紝鏄ユ殩鑺卞紑鐨勫鑺傦紝涓嶇煡鍙堢敓鍑哄灏戯紵甯屾湜鎬濆康鐨勪汉鍎垮澶氶噰闆嗭紝灏忓皬绾㈣眴寮曚汉鐩告濄傛嫇灞曠煡璇1銆佽瘲鍙ュ師鏂 銆婄浉鎬濄嬪攼路鐜嬬淮 绾㈣眴鐢熷崡鍥斤紝鏄ユ潵鍙戝嚑鏋濄傛効鍚涘閲囨挿锛屾鐗╂渶鐩告濄2銆佹敞閲婄浉鎬濓細棰樹竴...
绛旓細銆婄浉鎬濄嬨愪綔鑰呫戠帇缁 銆愭湞浠c戝攼 绾㈣眴鐢熷崡鍥锛屾槬鏉ュ彂鍑犳灊銆傛効鍚涘閲囨挿锛屾鐗╂渶鐩告濄傝瘧鏂囷細椴滅孩娴戝渾鐨勭孩璞嗭紝鐢熼暱鍦ㄩ槼鍏夋槑濯氱殑鍗楁柟锛屾槬鏆栬姳寮鐨勫鑺傦紝涓嶇煡鍙堢敓鍑哄灏戯紵甯屾湜鎬濆康鐨勪汉鍎垮澶氶噰闆嗭紝灏忓皬绾㈣眴寮曚汉鐩告濄傚唴瀹瑰搧璇伙細杩欐槸鍊熷拸鐗╄屽瘎鐩告濈殑璇椼備竴棰樹负銆婃睙涓婅禒鏉庨緹骞淬嬶紝鍙鏄湻鎬鍙嬩汉鏃犵枒...
绛旓細鐩告 浣滆咃細鐜嬬淮 鏈濅唬锛氬攼鏈绾㈣眴鐢熷崡鍥锛屾槬鏉ュ彂鍑犳灊锛熸効鍚涘閲囨挿锛屾鐗╂渶鐩告濄傘愯瘧鏂囥戠孩璞嗘爲鐢熼暱鍦ㄥ崡鏂癸紝鏄ュぉ鍒颁簡瀹冨皢鐢熷嚭澶氬皯鏂版灊鍛紵甯屾湜浣犲閲囨憳涓浜涚孩璞嗭紝瀹冩渶鑳藉寮曡捣浜轰滑鐨勬濆康涔嬫儏銆
绛旓細姝よ瘲鍑鸿嚜鍞愪唬澶ц瘲浜虹帇缁淬婄浉鎬濄嬩竴璇椼傚叏璇楀涓:绾㈣眴鐢熷崡鍥锛屾槬鏉ュ彂鍑犳灊銆傛効鍚涘閲囨挿锛屾鐗╂渶鐩告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