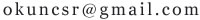散文|水的记忆
01/…我出生在豫南南部的一个古朴的小县城,我记事时古城墙的遗址尚存,城中东西南北笔直交叉的十字大街连接着各条小巷和人家。我家就在县城北大街城乡结合部的一个小巷里。
那是一个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不算丰富的年代,城里没有楼房,目之所及,全都是“人”字型结构的平房。平房又有青砖黛瓦和土坯草房之分。少部分富裕人家住的是瓦房。住草房子的,绝大部份是农村人家,也有个别城镇户口的,我家就属于后者。草房子与现今旅游时看到的杜甫草堂那样的茅草房不同,一是它的房顶上铺的不是茅草,而是当地野生的一种经久耐用的淮草。二是草房子房顶下方边缘处都有一排突出到墙体之外的瓦檐,俗称滴水檐,用来预防雨水滴沥到墙面上。
那时候既没有觉得深宅大院的楼瓦房有什么好,也丝毫没觉得自己的草房子有什么不好。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下雨天里,左邻右舍都是封闭门户,生怕雨水挤进屋里,而我家却房门大开着,因为要接雨水。
每每看着天要下雨,我们姊妹几个就习惯性地把屋里的盆盆罐罐都找出来,挨个摆在门口的瓦檐下。即便是半夜里下起雨来,要么按奶奶的吩咐,白天早已提前摆好,要么是奶奶临时起来,独自一个个摆上。
那时候下雨似乎比现在多。雨刚下起来的时后,我们像叽叽喳喳的小鸟一样,在门口挤作一团,争相观望着,议论着。尽管盆盆罐罐大小不一,高低不齐,但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圆的。哥哥说它看上去像一串糖葫芦,说滴水的声音像开音乐会。奶奶站在我们身后不说话。我们的心随着盆盆罐罐里的水位升高而欣喜,或者,因为雷声大雨点小接不到水而焦急。
起初,爸爸妈妈都在县城里的小学教书,后来,爸爸响应去偏远乡村支教的号召,去了离县城30多里远的一所乡村小学。再后来,弟弟出生不久,似乎没有征兆地,妈妈突然就患上了急症,得病不到一个星期就去世了。
妈妈去世那一年我7岁,哥哥9岁,比我小的还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妈妈走了,家里大人就剩爸爸和奶奶。那天出殡回来已是午后,虽然院子还是那个院子,家还是那个家,可是感觉上,就像刚刚被盗过一样,院子里树上的树叶稀稀拉拉的,屋里凌乱不堪。傍晚的时候,爸爸的一个好友,也是街坊,领来一个拉车的,车上载着一口倒圆台形状的陶瓷水缸。水缸很大,我和哥哥刚刚合抱得住,高度和5岁的妹妹一般高。几个人把水缸从车上卸下来,携手抬到灶屋里,放在了门后的墙角处。
那时侯还没听说过“自来水”这个词。生活用水只有两个途径,洗洗刷刷的可以去水塘,但饮用水就必须去就近的担水井。因为地质原因,县城里的水井寥寥可数,而且水井还特别深。小城的家家户户都有一条扁担两只水桶,还有像盘着的长蛇一样的一捆子井绳。我家东边300米远的那口水井,算是距家最近的了。曾经有一年大旱,那口水井临时枯竭,爸爸不得不到北关外去挑水,北关外那口井离家一里多远,爸爸挑满一缸水要六个来回。
挑水是个力气活儿,把水从井里提出来更是技术和风险并存。这在别的家庭并不算什么,但在我家,却是一个大问题——奶奶年过花甲,而哥哥才九岁,老的老小的小,我们都不能挑水,所以,挑水的重担自然就落在了爸爸一个人身上。县城到爸爸教书的地方不通公共汽车,爸爸骑自行车上班,每星期回家一次,所以,每周末临走前,爸爸必定要挑满一缸水。
平时奶奶尽量俭省着用水,能去水塘里洗的尽量去水塘,洗菜的水澄清了重复着用,这样紧紧巴巴地一缸水够吃一星期。偶尔不够吃,或者夏天天热,不到七天头上水就变质了,奶奶只好想别的办法。遇到舅舅或老表等亲戚上门,不用说都主动给水缸蓄蓄水,而有时候就得求邻居帮忙。
奶奶不喜欢总是劳烦邻居,所以,那个时候另一个办法就是接雨水。我和哥哥把房檐下接满了水的盆盆罐罐或端或提,小心翼翼地移进屋里,放上半天或一夜,水澄清了,就可以用来刷牙洗脸、洗碗刷锅了。奶奶说,雨水不能喝,喝到肚子里会长石头,所以我们从来没喝过,奶奶当然也不会用雨水做饭。
长大后才明白,喝了雨水也不会让肚子里长石头,奶奶是骗我们。
02/…
那时候,姊妹五个当中,我是最调皮的一个。
下雪天里,草房子的房顶上积雪融化后的雪水从淮草里渗下来,随着夜里温度的降低结成冰,到了早上,一米多长、棒槌一样粗的冰溜子挂在瓦檐下面,在雪过天晴的日光下熠熠生辉。每每这个时候,我就会拿棍子把冰溜子敲下来,或当免费的冰棍含在口里,或是当作宝剑对着弟弟妹妹挥舞,甚至趁他们不备,塞进他们的脖颈里。那一弯一弯的交互相扣的漂亮瓦檐,竟因为我屡次三番的敲冰溜子,变得像我们该换的牙齿一样参差不齐。当然,我也少不了被爸爸和奶奶训斥。
草房子住久了,房顶上会生出大小不一的像多肉一样的植物,有的翠绿,有的墨绿,有的血红,有的酱紫,底衬着淮草清浅的黛色,看上去像极了美术课本上的油画。奶奶说那叫太岁草,不能拔下来。可我偏偏不听,常常趁奶奶不注意,拿竹竿捣几棵下来。直到长大后才知道,那太岁草代表福气,包含着奶奶对这个家、对我们姊妹几个的殷切期望。
那时哥哥比我文静,比我懂事得多。妈妈去世后的第二年,哥哥一度对担水发生了兴趣。几次看见,爸爸担完最后一担水,哥哥跟在后面拿井绳的时候,趁爸爸不注意,偷偷地往井里看。受哥哥的影响,更是被强烈的好奇心驱使,那天让我拿井绳,我也往那个奇妙的井下世界望了一眼——我小心翼翼地接近井口,弓着腰往前探出半个脑袋,当目光穿过空洞的昏暗,掉落在只有奶奶照脸的镜子一般大小的水面时,我不由得心理突突直跳,瞬间把半个脑袋缩了回来。
此后便有了我与哥哥第一次担水的经历。
记得那是夏日一个被蝉鸣填满的中午,奶奶手里握着芭蕉扇靠在躺椅上睡着了。哥哥拉着我的手到灶房水缸前,舀起一瓢水端到我面前,跟我说:“你闻闻,这水都臭了。”
我凑近水瓢吸吸鼻子,果然嗅到一股腥臭味。我点点头。哥哥说:“我们去担水!”
我不由得想起那次往井下望的情景,心里又是打鼓一样突突直跳。
悄悄地走到房檐下,哥哥学着爸爸的样子,拿起扁担放到肩上,笨拙地勾起两只水桶,我抱起一捆子井绳,蹑手蹑脚地往门外走,出了大门我不由得回望了一眼,奶奶依然在睡梦中。
本来井沿附近柳树下经常有人乘凉聊天的,但可能是那天天太热的缘故,除了树上知了的聒噪,树底下一个人也没有。是世界太空旷,还是我太胆小,像脚底踩在棉花上一样,我颤颤兢兢地在离井口两米远的地方站住。
哥哥接过我递给他的井绳放在井沿上,用一端的环形铁钩子钩住桶襻儿,捋着井绳,一把一地顺进井里。感觉到桶接触了水面,开始左右摆动井绳,接着,一把一把地往上拔,每次打上来的水都是小半桶。如此反复四次,最后匀成两个大半桶……自始至终,我都是一个胆小的旁观者,至今我还能感觉出来,后来我把井绳紧紧地抱在怀里,我从来都没有抱那么紧过,就仿佛井绳的另一头系着哥哥的命运一般。
一路上歇了两次,终于把水担到了家。可是,毕竟是第一次,又那么远的距离,放下水桶时“哐当”一声——奶奶醒了。待看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时,奶奶忽地一下站起身,迈着伶仃的小脚冲过来,把手里的芭蕉扇颠倒了个头,抓着芭蕉扇叶子的一端,扇柄像雨点一样噼里啪啦地落在哥哥的头上。
那个时候头脑简单,只觉得哥哥做了好事,还挨了一顿打,却体会不到自己的“好心”给长辈带来的巨大的心理负担。
那个星期六晚上,哥哥怯生生地躲在里屋昏暗的煤油灯下写字,怕爸爸回来知道后再挨打。
周末的夜黑而漫长,直到蝈蝈的催眠声把我送入梦乡,爸爸都没回来,爸爸总是那么忙。第二天爸爸虽然只是训斥了哥哥几句,可这事儿却没有完——
周末爸爸照例担满一缸水走了之后,第二天一大早突然又回来了。望着爸爸满脸的憔悴和疲惫,我和哥哥,当然奶奶也是,我们都感到诧异——虽然是暑假,但爸爸管着学校后勤,负责着学校的房屋、桌椅修缮,从来没有在家多呆一天过——为什么昨晚刚走,这一大早又回来了呢?
爸爸和奶奶在里屋里说了几句话,出来摸了摸哥哥的头,抱了抱弟弟妹妹,一口气喝完奶奶递给他的半碗面汤,推起自行车就又走了。
爸爸走后,我们姊妹几个围着奶奶,问爸爸回来干啥。奶奶禁不住再三盘问,叹口气道:“你爸昨天夜里做了个梦,梦见哥哥掉井里了,梦醒了再也睡不着了,早上天不亮就骑车赶回来了。”
奶奶的眼眶湿润了,哥哥哭了。
我没哭,但似乎是从那以后,我不那么调皮了。
03/…
哥哥向爸爸保证以后再不担水,他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攒钱买水。听他说“买水”,我瞬间便想起了那个卖水老人和他的摇铃声。
家大门口到街口约百米远。那时候大街上,没有汽车轰鸣,没有音响播放,甚至都没有叫卖声。相对比较安静的环境里,有三种声音在我的记忆里印象深刻:一种是卖货郎的拨浪鼓“波啷啷”的脆响;一种是卖油郎手里的铁片“叮叮叮”的敲击声,悠远而绵长;还有一种就是卖水人“嘀铃铃”的摇铃声,比前两种声音要响亮得多。
三种不同的声响中,我们自然最喜欢拨浪鼓的声音。一旦拨浪鼓的声音响起,我们就会立刻停下所有的游戏,雨后春笋般地从四面八方冒出来,一窝蜂地拥上去,围着货郎担,翻出衣兜缝里藏匿已久的一分二分的硬币,换来或糖豆或其它什么。奶奶最惦记卖油郎,等卖货郎挑着担子走远了,我们回到院子里,奶奶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我们听:“卖油的有几天没来了。”言语里充满了期盼。这个时候,我就知道,厨房里的香油瓶子快见底了。
童年对一切甜的东西的敏感,让我对西关外那口“甜水井”充满了无限遐想,后来从大人的眼神里渐渐明白,认为那井水像糖豆一样甜简直就是个笑话。所谓的甜,就是不咸不涩罢了。上学以后,路上遇见那个卖水的,不免会站在旁边观看:胶轮的人力车上,横卧着一个用铁皮制造的汽油桶改造的大水桶,桶的上部开一书本大小的方孔,焊接上一个四方形的漏斗,作注水用。桶的底部焊上一段直径3-4厘米的圆管,圆管上再套上一段自行车的内胎,作放水用。
水按桶出售,一桶水5分钱。
一年四季,无论刮风下雨,天热天冷,卖水人的摇铃声都会每天早一次、晚一次地照常响起。但爸爸和左邻右舍决然是不会去买水的。而且,偶尔遇见有人买水,还常常显露出鄙夷的神色——在那个生活窘迫的年代,有免费的水吃,怎么能把钱扔在买水上呢?爸爸一个月36元的工资,要养活一家七口人,每月除了煤米油盐,再扯几尺给我们做衣服的粗布就没了。现在想来,那时爸爸才是名副其实的“月光族”,不仅月月光,常常还要预支、借债。
童年小县城的四条街,东大街有电影院,有开万人大会宣判犯死刑犯的大广场;西大街有戏院,有县政府大院;南大街有新华书店,再往南还有古城墙遗址和吊脚楼。唯独北大街显得冷清,只有一个废品收购站。然而,冥冥之中就仿佛上帝故意的安排一样,让人没想到的是,后来那里竟成了我和哥哥取钱的“银行”,买水的钱全都是在那里卖废品赚来的。
第一次收集废品特别不容易,之前因为卖货郎的诱惑,眼皮子底下能卖的,废铁废铜废书本报纸等,早都卖净了。所以,那一次选择了卖碎玻璃,一放学就出门捡,连续捡了几天。为了把地上的玻璃抠出来,手都割破了。
那天放学回来,我和哥哥慌慌张张地把一篮子碎玻璃抬到收购站,再揣着兑换来的一角三分钱兴冲冲地返回家候着。当听到卖水人嘀铃铃的摇铃声在巷口响起,第一次发现,那声音竟也那么好听。
哥哥提上两个桶前面走,我拿一根木棍后面跟,小脚伶仃的奶奶追到大门外,我回头自豪地扬扬手,我说:“去买水!”
我们把一角钱交给卖水老汉,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他往桶里放水,看到没把水放到与桶口平齐,那一刻我心里好失望。结果,把木棍穿在桶襻儿上,抬着才走了几步,水就往外溅。哥哥怪我“路都不会走”,说着连忙把桶放到地上。再一次抬起来走水还是往外溅,于是再放下……哥哥让我把木棍抽掉,独自用手掂起水桶,走六七步放下歇一口气,再走六七步再放下歇一口气……我跟在后面,无助,委屈,又是心疼,眼泪差一点溅出来。
好心的邻居看见了,上前帮忙把水提回了家,还向奶奶夸奖我们长大了。奶奶把邻居送出大门,回身去鸡窝里摸了两个鸡蛋,用我们买的甜水,破例做了一锅鸡蛋面片——记忆里那是我童年最好吃的面片,吃得我直打饱嗝还想吃。
那之后挖空心思收集可卖的东西,卖过桃仁、杏仁、橘子皮,卖过槐米、楝树果,还卖过土鳖子、蝉的壳等。后来正苦于实在想不起来卖什么的时候,爸爸给我们出了个主意——挖地骨皮。周末爸爸还给我们带回来了一个挖地骨皮的工具——乡下刨花生的铁耙子。
地骨皮是一种中药,其实就是枸杞的根。挖地骨皮要到城外,农田边上,沟渠的沿上,古城墙的半坡,到处都是。下午放了学出去挖,到天黑时回来,就能挖上一篮子。回到家里,捡起一段段新挖的根放到石头上,用锤子轻轻地一砸,砸个皮开肉绽,把皮拣起来,摊到太阳底下凉晒,晒干了就可以去卖了。
那时每次去卖地骨皮,少则可以卖三四角钱,多则可以卖六七角。就这样,我和哥哥用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劳动,终于改变了家里接雨水,吃水难的状况。只是爸爸每每周末走的时候,依然把水缸担的满满的。
爸爸乐意我们通过劳动锻炼自己,可又不希望我们太累。
后来有一次去城外挖地骨皮,意外发现一滑坡处的土层里,裸露出一串串泛着绿色锈迹的铜钱,我们又紧张又激动地扑上去,又是捡,又是挖,把头上的帽子取下来把铜钱放进去,没有回家直接去了收购站。至今都忘不了铜钱倒入那个收购员的秤盘子里时“哗啦啦”的脆响。那次一共卖了7元7角6分钱,相当于爸爸一个月的五分之一的工资还多,五分钱一桶的水可以买150多桶。我和哥哥欢天喜地拿着钱跑回家,回到家就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给奶奶说了,还说爸爸以后可不用担水了。
周末爸爸回来听说后,果然现出兴奋的神色,朝哥哥伸出手:“钱呢?我看看。”待哥哥自豪地将钱递上,却不料爸爸数过之后,只把零头退还给了哥哥,一边把钱装人上衣口袋,一边说:“怎么能不担水呢……给你俩一人买一双解放鞋,喜不喜欢?”爸爸说着,担起水桶挑水去了。
看着爸爸出了大门,一旁的奶奶说:“还不是怕你们再去井里担水,不然一分都不会退给你们。”
04/…
十岁那年的那个暑假,爸爸调回了县城的小学。从此,爸爸再不用一次担满一缸水了。爸爸也禁止我和哥哥再捡破烂、采草药,要我们专心读书,好好学习。
1977年恢复停止了十年的全国高考,那时我和哥哥都在乡下知.青.农场劳动锻炼。四季度的时候,上面通知准备参加高考的可以回家复习,我和哥哥同时被爸爸招回城里复习功课。
爸爸暂时打消了翻修房子的念头,为我们提供安静的复习环境,并把他认识的县高的老师请到家里,给我们复习指导。
做梦都没想到,高考放榜,哥哥考了全县第一,我考了全县第五。那阵子我和哥哥倒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爸爸异常高兴,一时间成了小城街谈巷议人见人夸的名人。
随后,我到上海读书,哥哥去了北京。四年后大学毕业,正赶上重知识、重人才,我不但留在上海工作,而且单位里还分配我了两居室的房子。
清楚地记得,第一天单位报到,晚上一个人回到新房子里,兴致盎然地摆弄着厨房里的水龙头、洗浴间的淋浴花洒,脑海里瞬间浮现出童年时房檐下接水的映像——最难忘每每雨刚下起来的时候,由于盆盆罐罐都还空着,房檐上的水滴重重地砸在盆底罐底上,发出的声音五花八门,有的沉闷,有的清脆,有的像晨钟暮鼓,有的如铜锣铙钹。白天里,给浩浩欲沸的市声平添了生气,在夜晚,又给寂静的夜带来一些凄凉。和童年里瓦檐下的滴水一起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的,还有奶奶和爸爸对于我们的爱。
那一刻,我禁不住跑到大街上,给爸爸打了个公用电话,我说:“爸爸,我有房子了,你一定要来看看,就是别的什么都不看,也要来看看我屋里的自来水,永远都流不完的自来水……”
又过了三年,爸爸退了休,在我的再三催促下,爸爸终于来了上海。因为我向爸爸提起过我和女朋友经常一起做饭吃,结果爸爸来时候带了许多家乡的土特产,有芝麻香油,芝麻酱,花生米、腌野蒜、还有油条和我最爱吃的杨家糕点。那天我和女朋友小惠到虹桥火车站接他,取下爸爸胸前和后背上的大包小包,望着爸爸满头的白发和像风干了的橘子一样的满脸皱纹,望着爸爸因为长年担水造成的高低不平的左右肩,我真真切切地感到,爸爸老了。
妈妈去世后爸爸孑然一身,一直忙于工作和我们的成长,连家乡的省城都没去过。这一次,我特意请了三天假,加上星期天,我按四天时间,为爸爸设计了一次以“水”为主题的江河湖海游。其中,江是黄浦江、长江,河是苏州河,湖是淀山湖,海,当然就是东海了。
苏州河线路,除了观赏两岸的自然风光和一些优秀的历史建筑,还顺路参观了四行仓库遗址、上海造币博物馆和我的母校。1937年“淞沪会战”末期,国民党军队西撤,只留下400余人固守四行仓库,他们为和平直面炮火,以血肉之躯誓死坚守,彰显了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气节。爸爸感叹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叮嘱我要好好珍惜。地处苏州河畔的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上海造币博物馆,独树一帜的“造币工艺”展示和琳琅满目的产品相结合,让爸爸想起了当年他看得比命都重的每月36元,想起了依靠这点工资支撑起一家七口一路走来的艰难历程。望着橱窗里历代使用的古钱币,我不由得想起了那次卖给废品收购站、卖了7元7角6分钱的那一帽子铜板,看上去一模一样的孔方兄。在我的母校,参观完中西结合风格的校舍教楼,以及我曾经的宿舍和教室,傍晚在学生食堂体验学生餐,临走时爸爸把学生没关紧的水龙头一一关上。
黄浦江线路,游览了外滩、东外滩和吴淞口。站在外滩举目远眺或是徜徉其间,波光粼粼的江面上游轮川流不息,堤岸上中外游客熙熙攘攘。无论是风格迥异的万国建筑博览群,还是俏立于黄浦江于苏州河交汇处的外白渡桥,都是中国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是上海的地标之一。位于东外滩的上海杨树浦水厂,是中国第一座现代化水厂,于1883年建成。在随后的100多年里,随着沿“两江”更多的水厂、水库的建成,上海的原水供应,逐渐由原来70%黄浦江水、30%长江水,变成了70%长江水、30%黄浦江水,从而使上海自来水的水质大幅度提升。来到自来水展示馆,爸爸看得格外仔细,对水的净化流程、如何避免突发污染、如何应对咸潮入侵都要看个明白。吴淞口是黄浦江汇入长江的入江口。历史上曾经是扼守长江、黄浦江的重要军事基地,清政府曾在此建造水师炮台。站在江堤上,眺望着流经祖国大地11个省份的涛涛长江水就在眼前汇入东海,爸爸不由得发出“大江东去,浪淘尽”的感慨。
在上海陆域最东南处的南汇嘴看海时,正赶上海水落潮。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海水的咸湿味,一望无际的海面,漂泊的船只渺小得恍如尘埃。滩涂上,到处是捡泥螺、捉小蟹的赶海人。我和爸爸卷起裤管赤脚走在滩涂上,一边感受着脚下绵绵海沙的温馨,一边聊着关于大海的话题。爸爸说:“尽管地球上水的面积和陆地面积的比是7:3,但是地球上的淡水资源还不到总水量的3%。如果不节约用水,地球上的最后一滴水,将是人类的眼泪!”没想到,前一天在自来水展示馆看到的广告语,爸爸竟然一字不差地记下了。
淀山湖位于黄浦江上游,是上海最大的天然淡水湖泊,素有“风吹芦苇倒,湖上渔舟飘,池塘荷花笑”之美誉。游览中,我陪爸爸走到一段不设防的湖边,在一块礁石上坐下来。阳光洒在水面上,湖水水质清澈,水底小海螺爬过的印痕,宛如某个大书法家的笔迹。柔软的水草从水下悠悠浮出水面,像是书法家笔迹的延伸。爸爸用手掬一把清凉的湖水,久久地凝望。水从他如枯树皮的指缝里渗出来,一滴一滴,滴进湖里,滴水相融。
爸爸突然说:“你们用水,水管都是开到最大,洗手打肥皂也不关水管,水一直流。还有小惠洗菜,一个叶子一个叶子地洗。刷碗也是,反复地冲洗。”
我略微沉吟,解释说:“现在市面上卖的蔬菜,没虫眼的,上面可能残留有农药;有虫眼的,没打农药,上面可能粘附有虫卵,得仔细洗。”
几十只海鸥,在湖面上盘旋了一会儿,然后落下,围卧湖面,像是在开会。
“你奶奶也买过一次水。”爸爸望着远处那群开会的海鸥,沉浸在往事的回忆里,“那天早晨,你奶奶做饭,往水缸里舀水时,发现缸里漂了一只死老鼠。水不能吃了,又不能去别人家借水(家乡有不能向别人家借水的习俗),怎么办?奶奶只好把馒头烤烤,让你们就着咸菜吃了,再喝点开水,先让你们去上学。然后就等着卖水人的铃声……如果当时缸里掉的是一只菜虫,你奶奶会买水吗?”
奶奶是在我大一下期时去世的。奶奶是从那个社会走过来的人,奶奶是个小脚女人、家庭妇女,没见奶奶看过书写过字。但在我心里,从来没觉得奶奶是一个没文化的人,这不仅是因为她良好的品德和为人,更因为我对她这样的认知——她会识天气。在那几年吃水难的日子里,她能通过周围环境、天相和动植物的变化,准确地判断出未来天气的变化,下不下雨。她那些经常挂在嘴上的天气谚语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云彩南,水涟涟,云彩北,晒干坯”“久晴大雾雨,久雨大雾晴”“燕子低飞鸟洗澡,大雨随后到”“蚂蚁搬家蛇过道,大雨不久要来到”“水缸出汗蛤蟆叫,必有大雨到”……她的天气预报往往比家门口堂屋上方挂的那个方匣子里的人预报得还准。在我幼小的心里,奶奶就是一个气象专家。我曾经不止一次地问她:这么多天气谚语你是怎么知道的?
现在想来,那个时候,不但要接雨水补贴生活用水,而且天气的冷暖,还关乎着我们的穿衣,关乎着我们的身体健康。生活是压力也是动力,奶奶识天气的功夫,全然是被生活逼出来的。
用手握不住的,不止是水,还有时间。时光流逝,永不停歇,像秋风卷走落叶,它能卷走所有的人,奶奶就是其中之一。那一刻,想象着奶奶在那个不寻常的早上,颠着小脚前往巷口买水的艰难,我早已泣不成声。我说:“爸爸,您说得对……”
05/…
写下这些文字,父亲离开人世也已近十个年头。原来老屋的瓦檐草房,历经几次改造,如今,弟弟早已在原来的地基上盖起了三层楼房。同样,当年担水的那口水井,也早已被高楼大厦踩在脚下。还有,曾经的废品收购站,也在后来扩街时迁走而没了踪影……偶尔千里迢迢回到家乡,没有了奶奶,没有了爸爸,放眼四顾,全然不见童年的痕迹。然而那些关于接水、担水、买水的记忆,却历历在目,恍如昨日。遗憾那时年龄小,不理解奶奶和父亲的艰辛,遗憾长大后贪图自己小家的安逸,没能常回家看看,电话交流都少之又少。子欲孝而亲不在,多么希望能回到当年。
—— END ——
绛旓細鏈夊叧鎻忓啓姘寸殑鏁f枃3 杩欐槸涓绉嶅悕涓篐2O鐨勪笢瑗,濂规湁鏃犳暟鐨勫唴鍦ㄧ殑鐗瑰緛,浣嗙粰浜虹殑鍗拌薄鏈娣辩殑鑾繃浜庡ス鐨勬棤鑹层佹棤鍛,浠ュ強濂圭殑鏅惰幑閫忎寒銆傜粰浜鸿澶氬够鎯炽傛按鏈夊澶х殑浣滅敤,鍕块渶澶氳█,璺汉鐨嗙煡銆傚彜鏃舵湁璁稿鍚嶄汉浠ユ按鍠诲凡,鍙姘村湪浜哄績鐩腑鐨勫湴浣,鑰岀粰鎴戠暀涓嬫繁鍒璁板繂鐨勫垯鏄瓟瀛愮殑鈥滄按,鍚涘瓙鈥濈殑鎰熸叏,鎴戜滑浼熷ぇ鐨勫瓟澶瓙濡傛槸...
绛旓細鏁f枃鐨鐗圭偣鏄氳繃瀵圭幇瀹炵敓娲讳腑鏌愪簺鐗囨鎴栦簨浠剁殑鎻忚堪,琛ㄨ揪浣滆呯殑瑙傜偣銆佹劅鎯呫備綘鏈変簡瑙h繃鏁f枃鐨勫啓浣滃悧?涓嬮潰鏄垜鏀堕泦鏁寸悊鐨勬湁鍏冲啺蹇冪殑鏂囩珷鏁f枃,娆㈣繋闃呰,甯屾湜澶у鑳藉鍠滄銆 鍐板績鐨勬枃绔犳暎鏂 绡1 鍥犱负鎴戝枩娆㈡按,鎴戠埍鐪嬩竴鍒囩殑姹熸渤婀栨捣銆傛垜杩欎竴杈堝瓙,鍦ㄥ浗鍐呭浗澶,鐪嬭杩囪璁稿澶氱編涓界殑銆佸煎緱璁板繂鐨勬箹:鏈夌殑鏄北閬湀鏄,鍔...
绛旓細澶垵鏈夊瓧,浜庢槸姹夋棌鐨勫績鐏典粬绁栧厛鐨勫洖蹇鍜屽笇鏈涗究鏈変簡瀵勬墭銆傝濡傚嚟绌哄啓涓涓滈洦鈥濆瓧,鐐圭偣婊存淮,婊傛粋娌辨脖,娣呮穮娌ユ播,涓鍒囦簯鎯呴洦鎰,灏卞疀鐒跺叾涓簡銆傝瑙変笂鐨勮繖绉嶇編鎰,宀傛槸浠涔坮ain涔熷ソpluie涔熷ソ鎵鑳芥弧瓒?缈诲紑涓閮ㄣ婅緸婧愩嬫垨銆婅緸娴枫,閲戞湪姘寸伀鍦,鍚勬垚涓栫晫,鑰屼竴鍏モ滈洦鈥濋儴,鍙ょ宸炵殑澶╅鍗冨彉涓囧寲,渚挎倝鍦ㄦ湜涓,缇庝附鐨...
绛旓細鍘傚尯鐨勬按闂告爮(浜虹О:椹潏)鍜屽偍鏈ㄥ満鍌ㄥ瓨鐫涓夊崄涓囩珛鏂圭背鍘熸湪,濡傝嫢澶卞幓鎺у埗鍘熸湪闅忔按婕傛祦,灏嗘妸搴滄渤涓嬫父鎵鏈夌殑妗ユ鎽ф瘉鎾炲灝銆佹妸妗ュⅸ妗ヨ韩鎺缈绘墦鐑傘傚鑻ヨ鍘熸湪鍦嗘柟闃诲娌抽亾浣挎椽姘存郴娲笉鐣,娲按灏嗘饭娌″煄甯,鍏跺悗鏋滀笉鍫鎯炽傝繖鏃剁殑鎴愰兘鏈ㄧ患鍘傛棭宸茬粍缁囧伐浜轰滑姝e湪濂嬪姏鎶ゅ巶,浠栦滑淇濆崼浜嗗伐鍘傚畧鍗簡鍩庡競,浣挎垚閮借繖搴уぇ鍩庡競閬垮厤涓鍦...
绛旓細鎻忓啓姘寸殑鏁f枃锛屽墠涓嶄箙锛屾垜鐪嬪埌褰撲唬浣滃蹇典汉鐨勬湁鍏虫弿鍐欐按鐨勬暎鏂囥婃晠涔$殑姘淬嬩竴鏂囷紝璇ユ枃鐭皬绮惧共锛岃瘝璇紭缇庯紝鏂囩瑪绠娲侊紝鎶婃晠涔$殑姘存瘮鍠讳负濂舵眮鈥︹︽瘮鍠诲緱寰堢敓鍔ㄣ傜幇鎽樺綍涓嬫潵鐚粰浣狅紝鎰夸綘鍠滄锛佹晠涔$殑姘达紙鏁f枃锛夊康 浜 鏁呬埂鐨勬按锛屾槸鍏昏偛鎴戦暱澶х殑濂舵眮銆傚湪鎴鐨勮蹇閲岋紝鏁呬埂鐨勬按灏卞儚涓骞呯編涓界殑鍥剧敾锛屾部鐫濉...
绛旓細鏁f枃浣滄枃 绡6 澶忓ぉ鐨勭骞存绘槸閭f牱鐨勬棤蹇ф棤铏,閭f牱鐨勫ぉ鐪熺儌婕傝蹇嗕腑鐨勯偅娆℃按閲屽瑝鎴,璁板繂涓殑閭f鎹曡潐,璁板繂涓殑閭f鑽$鍗,鏈夋椂鍊欑敋鑷宠繛鍜屽皬浼欎即浠墦鏋堕兘鏄竴绉嶇編濂鐨勫洖蹇銆 閭f椂,鎴戜笉鐭ラ亾浠涔堝彨澶忓ぉ,涔熶笉鐭ラ亾浠涔堟槸绔嬪,鏇翠笉鐭ラ亾浠涔堟椂鍊欑珛澶,鎴戝彧鐭ラ亾褰撴瘝浜插湪搴婁笂閾轰笂甯瓙,鎸備笂铓婂笎,褰撶埗浜查湶琚掕兏闇蹭钩,鍏...
绛旓細璁板繂涔嬫按鍐嶄竴娆℃极鏃犺竟闄呰捣鏉ャ傛瘡鍒版槬澶,瀹朵埂鐨勫北灏辩儹闂硅捣鏉,閬嶅北鐨勮姳鑽変簤鐩镐寒鐩搞傚北涓婄殑閲庤彍澶,鏈変竴绉嶄織鍚嶁滈吀涓嶆簻鈥濈殑閲庤彍,鍏舵牴,绾㈢櫧鐩搁棿,鏋佽剢,鏋侀吀鐢溿傛槸瀛╁瓙浠槬澶╅噷鐨勭編鍛炽備竴鏀惧,灏辫揩涓嶅強寰呭湴璺戝埌灞变笂,鍘绘壘,鎸栧嚭鏉,鎻╀竴鎻╂偿鍦,渚挎ユュ湴鏀惧叆鍙d腑,鐢熸曡窇浜嗕技鐨勩傝剢鑴嗙殑澹伴煶浠庡彛涓紶鍑烘潵,閰哥敎鐨...
绛旓細浣,閭d唤缇庡凡缁忓彧鑳界弽钘忓湪璁板繂涓,娓愭笎瑜幓寰鏄旂殑鑹插僵,鏈鍚庡彧鑳芥槸涓骞曞箷榛戠櫧鐨勭敾闈備笉蹇嶅績灏辫繖鏍风瀹冭屽幓,浜庢槸,蹇冧腑寰堟兂鍙互鐢ㄦ暟鐮佺浉鏈烘妸瀹冪殑缇庝附姘歌繙鐨...2020-10-13 鍚嶅鍐姘寸殑鏁f枃 2020-12-18 鎻忓啓姘寸殑鏁f枃 2015-03-23 鍐欐按鐨勬姃鎯呯被鏁f枃500 4 2013-11-04 鎻忓啓绉嬪ぉ鐨勬暎鏂 442 2008-10-07 璋佹湁...
绛旓細瀹冨湪钄戣浠涔堬紵閭d笉鏄槑闀滆埇鐨勬箹娉婂悧锛熶綘鐪嬮偅锛屾鏌崇幆缁曪紝纰ф尝鑽℃季锛屾煶娴椈鑾猴紝鑾茶晩娓呴锛屽灏戞枃浜轰负瀹冿紝鍚熻瘲璧嬫瓕銆備絾鏄紝鍋滄粸涓嶅墠鐨勬箹娉婏紝姘磋川鐨勬贩娴婏紝濡傚悓涓绉嶇梾鎬佺殑缇庯紝鏄惧緱闆嶅鑰屽張鏈変簺鎲旀偞銆傚皬婧珯鍦ㄥ北鍧′笂鎷嶈捣绾磥锛岄洩鐧斤紝娓呮緢鐨勬按鑺憋紝鍍忔槸鍢茬瑧婀栨硦锛屼篃鍍忔槸鑷槻銆傚皬婧潥瀹氬湴璇达細鏃堕棿鐨勯暱娌冲皢...
绛旓細姣忎竴娆¢亣瑙,鎯崇潃鑻ユ妸榛勬渤姘存崸鍦ㄦ墜涓,鎵嬫帉浼氳鏌撴垚榛剕鑹,鎬庝箞鎽╀竴鎿﹂兘灏嗘棤娉曟仮澶璁板繂涓殑鑸掗傛劅銆傚叾瀹為粍娌虫按浠庢潵涓嶆浘姹℃煋杩囨垜鐨勬墜鎺,姣忎竴娆′粠姘翠腑涓鎶戒竴绂荤殑鎵嬫寚閮借繕鏄師鏉ョ殑棰滆壊銆傚彲,浜虹殑鎰熻濡傛鍙,鍙堟槸濡傛鐪熷疄,灏辨槸杩欐牱涓绉嶆劅瑙,澶氭闃绘鎴戣蛋杩戦粍娌崇殑姘,鍙兘绔欏湪宀歌竟鐪烘湜,鐚滄祴,鐒跺悗鎭㈠骞抽潤銆 骞兼椂,鍧愯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