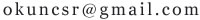亲有没有展昭儿时学艺的文啊? 猫鼠校园文 O(∩_∩)O谢谢
\u6709\u54ea\u4f4d\u4eb2\u77e5\u9053\u8fd9\u7bc7\u9f20\u732b\u6587\u53eb\u4ec0\u4e48\u5417?\u300a\u7231\u5728\u65e0\u8a00\u65f6\u300b
\u590d\u5236\u4e00\u6bb5\u5728\u767e\u5ea6\u641c\u4e00\u4e0b\u5c31\u6709\u4e86
\u732b\u9f20\u7684\u6587\u6709\u5f88\u591a\uff0c\u53ef\u662f\u6ca1\u6709\u5206\u7c7b\uff0c\u73b0\u4ee3\u53e4\u98ce\u4ec0\u4e48\u7684\u90fd\u6df7\u5728\u4e00\u8d77\u4e86\uff0c\u4eb2\u8fd8\u8981\u4e48O(\u2229_\u2229)O~
章一、绿杨芳草长亭外春暮之日,四更时分,三月雨来,黎明前夕。
万物沉睡在这朦胧春意中时,一束暗黄色的光芒穿透棱纸,最终熄灭在黎明时分。鸡叫不绝,狗鸣不已,实是有些饶人轻梦。开封府上下却早已整装,各司其职,又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碌。绛红色的官袍永远是开封府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每每看见,衙役们总是说着,展大人早出晚归,真是太过辛劳啦……
此时,一切如往常,唯独那席绛红迎风独立,心感不安。
“展护卫,该上朝了。”屋内传出一声,那人暗自叹了口气,转身回屋。此时才看得清楚些,他身着绛红官袍,系着纯黑腰带,长发高高系起,脚穿黑底官靴。身材挺拔,五官精致如名家笔下绘出一般,轮廓分明,线条清晰,眉宇间却有解不开的忧愁。
几步之遥,他已进屋,对一微胖老者略一欠身,抱拳道:“今日大人上朝,属下就不护送了。”
“展护卫可是有事?”身旁一书生问道。
略一思索,决定如实说了:“是,公孙先生,属下昨日收到一封书信,邀属下于春暮六更时分,前往开封城南门口,有事告知。”
老者问道:“有这等事?”那名被唤作‘展护卫’的男子点头。
白面书生顺了顺胡髯,若有所思道:“来者身份定然不小,否则展护卫也不会如此在意。”
展护卫摇头否认道:“不是,我至今不知何人来信。这是,那封信上以人血代笔墨,属下不得不在意。”
老者惊道:“人血?!”
展护卫道:“绝不会错,正是人血!”
白面书生走至窗前,望了一眼天际,已至破晓,再耽误下去便要误了早朝,书生提醒道:“大人,该进朝了!”
老者点头允了,同时对那男子关切道:“展护卫小心为上!”
“是!”
目送二人离去,展昭只觉得右臂一阵刺痛,眼前一眩,后退几步,站立不稳,一时跌坐在木椅上。其实事情远远不止他所说那般简单,那封信上还涂有毒药,且那毒药是江湖上失传已久的‘迷人醉’,未免他们担心,自己勉强压住伤势,不敢说出。信上有言,六更时分,逾期不待。看来,自己还必须即刻前往。其实也不尽是为了解药,他也想见见究竟是何人。
展昭连封几处大穴,疾步出府,前往开封城南。
开封城南。
天还未大亮,街上行人也是稀疏,各家各户大门紧闭,还在梦中。展昭卸下一身绛红官袍,换上一套蓝衫,可英伟气息不减。
冷风袭来,展昭身体强健,本是不怕这微寒,可如今身中奇毒,只觉整个右臂一阵酸痛,人像是掉进万年冰窖一般,奇寒无比,本想运功抵抗,岂料越抵越寒,他只得不住挫手,希望缓解严寒。
眼见五更越来越近,面上虽然平静,心中却暗自警惕。
果然,对方如约前来,一身黑衣在这样的地方本是及其耀眼,但时间尚早,各家各户都沉在梦中,也没有多少人注意他的打扮。来者身着黑衣,面上罩着黑巾,恰巧这城门未开,城南又地处偏僻,谁也没有太过在意。
展昭心中已经确定来者身份,上前问道:“阁下何人?”
只见他身材魁梧,不似女子。又听黑衣人笑道:“南侠不亏是南侠,身中剧毒却还先‘关心’在下。”话音一落,黑衣人利索地从怀中拿出一小瓶子,瓶口堵着红缨,黑衣人继续道,“这是‘迷人醉’的解药,只需服一次,一次三粒即可解毒。”黑衣人将瓶递上,展昭略一迟疑,但已伸手拿过,取出红缨,倒出三粒黑色药丸,仰首服下。
黑衣男子又大笑几声道:“不亏是南侠,就这份气度就足以令群雄低首。我受我家主人之命,特来告之南侠,三日之后,陷空岛芦花荡将被纵火,南侠去与不去,自行决定!”说罢,只见一道黑影从眼前闪过,黑衣男子便消失面前。展昭看得暗自咋舌,这黑衣人的轻功虽算不上绝顶高手,却也是厉害,但那黑衣人自称为仆,想必他家主人定然是号人物。真不知究竟是敌是友?
陷空岛纵火一事,仅凭这‘迷人醉’和那身轻功,展昭便已不敢怠慢。
匆匆回了开封府,留下书信,带上纹银,便速速骑马离去。
三日……
醒了,醉。
醉了,醒。
不知沉溺在这样的酒庄多少日子,只知道酒是辛的,是辣的,也是苦的。
“五爷,您还要喝啊?”那名活计端走几个空酒瓶,殷勤地擦了擦桌子,问道。
喝?他终于清醒了一点。扫了一眼满桌狼藉,长长叹了口气,拂手放下几定银裸子,顺手抄起斜靠桌的画影,大步流星迈出了这里。强烈的光线一时刺眼,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听得有些不顺耳,大街上人来人往,一派热闹繁华景象。他理了理衣襟,回首望向酒庄,看着金边镶嵌的牌匾,勾起深思……
在这里呆得太久了,五天,十天,还是一月,二月?
他自己都记不清楚了,自从苏虹走后,他甚至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
这种爱,是不是太过痛苦?
堂堂锦毛鼠,敢大闹东京的白玉堂,竟然也会有这样的一天?
果真,情是穿肠毒……
收拾了心情,他深深吸了口气,将连日纵酒的疲惫收起,以新的面貌重新走上江湖,感情既然已成过去,就要懂得放手。
是时候该回陷空岛了,见见众位哥哥,还有那只猫儿。不知他们都还好吗?
另一头,展昭快马加鞭,每五百里换匹马,昼夜兼程,如不出意外,应是能在三日内赶到。可是这一路上,他总是感觉有人在暗处跟踪,却不见其人,心下疑惑,却因陷空岛之事,而不敢怠慢,只得将这份疑惑暗自藏在心里。
这一路还算是顺利,阳春三月,无论城内城外,均是一派新气息。
古道之上,尘土飞扬,蹄声单调,唯那一席蓝衣,看得让人舒坦……
章二、年少抛人容易去
夜已深,微微风起,门窗‘咯吱’不断。房内的客人,也未入眠,平躺木床,双目微瞌,一脸风霜。显然连日的赶路已让自己疲惫不堪。本想早些入眠,却总是无法睡去。他叹了口气,起身坐在床边,并未点灯,借着月光,悠然倒了杯茶,呷了一口,陷入深思……
那黑衣汉子为何通知自己有人将火焚陷空岛,他怎得知?另他口中主人又是何方神圣,又怎会有‘迷人醉’这等毒药?陷空岛在江湖上也算是小有名气,何人又要在太岁头上动刀?这些如何解释……
展昭左手抵额,只觉心中烦闷。这些事情他整日思索却连头绪也没找到,他本打算一口气直奔陷空岛,然而两日赶路下来,他是练家子自然还撑得住,可胯下良驹却累倒,无法继续赶路。如此一来,只得歇息一晚,争取明日午时之前赶至。叫了上等客房,吩咐伙计寻千里良驹之后,便简单应付了晚饭,早早回房歇息。在床上辗转反侧,就是无法入眠。索性便不睡了,这样的夜晚赏月也是人生乐事。
他只得这样安慰着,努力让自己不要再去思索没有答案的问题,可思路就是不由自己。
望着一轮明月高挂半空,满天星斗皆失光芒,明月如玉,散发着柔和的月光,透进窗来,撒了一地。
不知不觉便忆起往昔……
那时自己年方弱冠,上山随师学艺短短几年便小有成就,匆匆下山回家探望,进门便被一少女当作贼抓,闹了天大的笑话。看那少女不过豆蔻年华,身材苗条,杏眼圆脸,小小的蒜头鼻格外可爱,适身的粉衣,束发的粉带尤为可爱。此时自家父亲开了药铺,虽算不上红火,却还能过日子,这少女性子活泼,耐不住女红的寂寞,便偷偷去了当地有名的武馆偷学武艺,却总是被抓,每次一顿拳打脚踢却并没有消减她的意志。那时自己坦明身份,少女狐疑了半晌,才叫来了家人。
“昭儿,真的是你啊!凌儿,还不见过二哥?!”母亲见了他,开始也有些不信,后来他拿出家传的龙纹玉佩,证明了身份,那丫头反而不认,说是要比划比划。无奈只得赔着这丫头胡闹了一场,这样可好,这丫头不干了,说是要他传授武功,还要拜他为师。这样一来,为了哄这三妹,不得不耽搁了些日子。师门有命武功不得外泻,于是便顺手拿出了当时归家路途上因救人性命得来的一本轻功秘笈,本打算有时间看看,但禁不住这丫头缠人的功夫,便索性送给了她。
“二哥,这秘笈是不是可以练的像你一样厉害啊?”丫头总是仰着脸问。
他当然又费了好一阵功夫解释,安慰,保证外加发誓一类,终于打消了这丫头的怀疑。
但这些日子在家里,和大哥三妹倒也合得来,尤其对这三妹,宠爱有加,舍不得让她受到一点伤害。
母亲总是说自己太过溺爱这孩子,然而他也说不清楚为何会对这丫头上心,大概这就是兄妹天性。
“凌儿,好一阵子不见你了,还在用功?”展昭最后一次见到这丫头是在后院小池旁。后院占地不过几亩,却布置的极为优雅,一条青石小道在这后院划了个半圆。圆外几座假山靠墙置放,圆内有张八仙桌,几把石椅靠放,再前些便是一汪清泉,泉水清澈见底,水中养了几条金色鲤鱼,整个后院看上去有说不出的闲适。
展凌正全神贯注地翻阅着书卷,听到他的声音,抬头望去,惊喜了好一阵子,拉着他坐下,问这问那的。“二哥,你说这个地方什么意思啊?还有这里,这里我看不大懂。”展昭的本意是希望她有一技之长防身,免得受人欺负,然看她如此痴迷,虽然与本意有些差别,但总归多学些也没什么不好,也就细细给她讲解。
这一讲解,便足足耗去了半日的光阴。本是来和这三妹告别,他要回师门复命。直到大哥进后院时,催促自己,他也才想起是时候回去了。展凌突然听见二哥要走,死活不让,可时间有限,只能安抚了她几句,便走了。
依稀记得最后几句话是这样的:
“二哥,你好不容易回来,多陪陪我好吗?我保证再也不会给你添乱了!”展凌说着眼中泛起水光。
他见了心有不忍,安慰道:“好了,下次二哥回来教你别的好吗?多大的丫头了,还哭哭啼啼的,你还当自己是孩子啊?”
“我本来就是嘛!死二哥,坏二哥,凌儿不理你了!”正说着,展凌突然回身,双手掩面,跑出了后院,连心爱的书也置之不顾,想来当真是伤心到了极点。展昭心下叹气,面上却依旧如故,交代了大哥几句,便离开了这里。
他从来不曾料得,这次的见面竟然是最后的永别。
当他学成归家之时,这里早已成了废弃的宅院。牌匾上的‘展家’二字已落满尘灰,蜘蛛网四处均有,他骇了一跳,急急寻人来问。哪知原来这展家的药铺几个月前被官府封了,说是吃死了人,之后县官大人查看之下,发现铁证如山,判了展父秋后斩立决。展母受不了刺激,一病不起,最终命归黄泉。他的兄长万般无奈,想要告上京师,但时不待人,最后居然被逼与展家三女展凌联手劫狱,却不料狱中早有重兵把守,不幸身死乱箭之下。展凌重伤逃脱,待展父处决之后,展凌一怒之下偷偷潜入官府,本意要杀那县官报一家之仇,却被师爷挡下,救了县官一命,如此一来,这展凌犯了律法,被迫亡命天涯,再也没有消息。展昭询问路人有关这件事的前后始末,得知这县官是名清官,受人爱戴。本打算出手取他性命,却又感此事有些蹊跷,且这县官也是难得清官,便忍下这个念头。
他漂泊江湖寻找三妹,暗地察访这件事情,却没有半点头绪。
后来遇到包大人,又……
“啊——”展昭猛地醒来,才发现已是日上三竿,他知道自己是睡过了头,拾剑便走,早点也未来得及用。
这次陷空岛的事情,他隐隐感觉到绝不寻常,也许与以往家变的事会有些联系。
章三、楼头残梦五更钟
午时将近,烈日当头。大街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好一派繁华景象。此处离陷空岛已不远,在直走百里,便可到通往陷空岛的码头。此时,一马,一人,一剑,自城门入街,直通大道,挥鞭催马,迅猛如风。来不及看清,便已消失在众人眼中。
绕过山路,行了几里,顿时眼前一亮。碧水当前,一眼望去竟不着边际,堤旁,垂柳随风起舞,婀娜多姿。凝目远眺,袅袅云烟环绕一座小岛。原来,这小岛便是江湖闻名的‘陷空岛’。陷空岛三面环水,一面环山。岛上有五位主人,人称‘陷空五义’,又唤‘五鼠’。曾经因展昭被封御猫一事,大闹东京,一时名震江湖,后又助开封屡破大案,更与御猫展昭惺惺相惜,成为莫逆之交。此番展昭急奔陷空岛,便是为了向他们报信。
走至湖边,见几艘摆渡小舟停靠,几名船夫打扮的人坐于凉棚,正划拳喝酒,好不尽兴。也难怪他们如此,这些日子无人拜岛,天气又热得惊人,无聊之下也就靠这些玩意打发度日。展昭上前询问道:“众位兄台,展某有急事上岛,劳烦开船。”
几名船夫瞧了瞧展昭的打扮,知道怠慢不得,但这天气十分恶劣,也无人愿意渡船,推让半天也没个结果,展昭已经按耐不住,距离纵火的时间将近,他心急如焚,哪有功夫在这里耽误,一抱拳道:“借船一用!”一跃身便落在一艘小舟上。挥巨阙挑船绳,拾船桨滑小舟。这些动作在一瞬间完成,待船夫反应过来,小船早已离岸几尺。
展昭心道:只愿还来得及。
谁知小舟刚一靠岸,便见前方茅草屋着火,这茅屋仅是为上岛客人纳凉所用,谁知竟然突起大火。展昭疾步上前,略一查看,屋内并无人在,心下松了口气。然仰首望去,黑烟直冲云霄,若蛟龙冲天一般,开始只是一小股,不消片刻,黑烟成股冒出。展昭皱眉道:“还是晚来一步!”嘴上虽说,可他脚下步伐却未减。跃上一棵百年松树的树尖,一眼望去,火势由岛中心逐渐四散,完全无法控制。即使如此,好歹也去看上一看。几个起落,展昭消失在这茂密的林中。
陷空岛,湖边。
“船家,怎么回事?!”正站于湖边观望岛上浓浓黑烟的船夫,忽然听闻一声历斥,只见一名青年男子手持宝剑,剑鞘华丽,几颗宝石红若滴血,剑穗呈淡黄色。整体观去,白衣胜雪,腰束玉带,脚踏云靴,鬓发散披于肩。再看五官,剑眉薄唇,鼻梁端正,星目中带几分焦虑。这,这不正是陷空岛的五义锦毛鼠白玉堂吗?
“五……五爷?”船夫不敢确定,这些月白玉堂不知跑去了哪儿,像是人间蒸发一样,几月未见,船夫也犹豫起来,才试探性地唤道。
白玉堂瞪眼问道:“陷空岛怎么着火了?”
船夫都面面相觑,不敢做答。其中胆子稍大的一个赤裸上身的男子道:“适才有一蓝衫人上岛,看样子非常着急,后来就……”
白玉堂嘀咕起来:“蓝衫人?那只猫?”稍作思考,他一个翻身稳落一艘船上,宝剑一挥,绳断船开。
他的动作和刚才的蓝衫人一模一样,船夫们也不知岛上发生何事,又开始喝酒赌牌。
“卢员外?”一到大殿,展昭四处寻找那五只老鼠,可除了慌张乱闯地仆人和庄客,根本寻不得五鼠半点踪迹,连卢岛主唯一的儿子也不知下落。展昭冷静地环顾四周,仆人庄客四散逃窜,每间房屋都沉在火海,有些屋子还有未逃出升天的人,可他此时也是顾得这顾不得那头。黑烟越加浓密,火势越加迅猛,人群越加慌乱。展昭一席蓝衫,立于殿前,俊美的面容浮上愧疚以及杀意。他恨自己何以晚来一步,造成如此大的伤亡,同时也愤怒是何人如此丧心病狂。他双手紧握成拳,发出咯吱的声音,脸色有些苍白,想是已愤怒到了极点。
此刻,一个熟悉的哭喊声传入耳中:“爹——二叔,救命哪!救命哪——”是,是卢天?展昭寻声望去,只见一少年锦衣绸缎,在大殿旁的屋内,惊恐大叫,哭声不断,却无人理他,只顾自己逃命。展昭飞身入屋,勉强蹲在这少年身旁,安慰着:“天儿,没事的。跟叔叔走吧!”之前卢方在国舅案中携着儿子曾经见过展昭,卢天自然认得,见展昭来了,心中欢喜,不住点头拍手道:“展叔叔您来了,快救救天儿吧!”
言罢,展昭起身正准备带卢天离开时,他背后突然有一根被烧断的横梁向他二人砸来。卢天惊叫道:“展叔叔,小心啊——”闻言展昭便迅速回身,运足内力狠击向横梁。
‘砰’——
一声巨响,横梁撞击在早已烧焦的枯木上,房梁一震,险些坍塌。刚才的猛击,也使他袖袍带火,急忙手旋几圈,将火熄灭。眼看这屋即将坍塌,展昭将卢天揽入怀中,寻得一丝空隙,猛蹬地向外扑去。
二人刚一扑出,身后房屋尽数倒塌,真是险到极点。
此时白玉堂也已赶至,看到这一幕,也是心惊胆战。见二人脱险,便上前关切问道:“猫儿,天儿,你们怎么样?”
展昭扶起卢天,心中有些感动,环顾了一下四周的情形,他道:“先离开此地再说!”话音刚落,白玉堂便已携着卢天跃出几丈,展昭查看了一下左手被火烧伤的程度,幸好只是袖袍被烧,一提真气,也随他们而去了……
离开陷空岛,就近找了一间客栈休息。白玉堂要了两间上房,他这脾气还是没改,做什么都要最好的。然后吩咐活计将饭菜送至房内,先让卢天好生吃一顿,压压惊,毕竟刚才这一幕,也着实让这孩子受了惊吓。
展昭将剑斜靠在桌子旁,理了理袖袍,问道:“白兄,你的几位兄长呢?”
白玉堂一愣,不解道:“你没有见过他们?不可能啊!这些日子我一直在酒庄,没有回去,最近想回去看看大哥他们,谁知一去就看见陷空岛着了火,瞧这火势,应是有人故意放火!谁要跟我们陷空岛过去呢?!”
卢天听着,放下手中筷子,道:“五叔,展叔叔,你们说我爹他们啊,我记得在被火烧的前一晚,我爹和三位叔叔就走了呢。”
展昭奇道:“什么事要你爹他们一起出去啊?”
卢天想了想,说:“哦,听爹爹说好像是,好像是收到一封信,还有,还有一件什么东西,然后爹爹他们就走了。连夜走得。”
“东西?!”白玉堂和展昭都莫名其妙。
卢天突然大叫起来:“我想起来了!是五叔你的白玉老鼠!!”
白玉堂一听,万分奇怪,可从身上一搜,那白玉老鼠的确是不见了。展昭问道:“真的不见了?”
白玉堂道:“是。可是我不记得有什么人拿走了白玉老鼠啊!”
展昭感到此事的严重性,便将有人告知自己三日后火焚陷空岛的事情说于了白玉堂。白玉堂大叫道:“你这蠢猫,怎不先飞鸽传书?”
展昭无奈道:“我传了,可是。”
卢天却道:“不对啊,我没听爹爹他们提起过有什么书信,这些天岛上没有鸽子飞进来啊!”
这下子,可算是明白了。原来有人故意先告知展昭陷空岛火焚的事情,然后引展昭前往,却又在中途拦下展昭的鸽子,这不是多此一举吗?之后拿走白玉堂的白玉老鼠作为信物交给陷空岛的人,引得其余四鼠出了陷空岛,最后火焚陷空岛。
这一连串的事情,又是为了什么呢?
为何要引展昭前往,又为何要火焚陷空岛,对他们又有什么好处?
白玉堂恨恨道:“如果让我五爷抓到那些混帐,看我不把他们拨皮拆骨!”
章四、花底离愁三月雨
匆促在客栈歇息了一晚,白玉堂和展昭都是武功高强之人,理应更加舒坦,却不知为何,浑身上下有说不出的难受。卢天这小子却睡得像只死猪,一个‘大’字形摆在床上,华被有一角被压在身下,大部分沾地,嘴边还流出几滴口水,看了着实让人发笑,在白玉堂的千呼万唤下,卢天终于揉了揉双眼,一脸睡意地问道:“怎么了?五叔。”
白玉堂扳起脸孔,正准备好生戏弄他一番时,展昭却像似想起了什么,忍不住问道:“天儿,你……你昨晚睡得怎样,有没有感觉。”话未问完,白玉堂便不耐烦地挥了挥手,笑道,“我说猫儿,你不是犯了猫颠疯吧?你瞧瞧天儿这睡姿,他肯定睡得比死猪还死猪!”
卢天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鼻子。白玉堂嚷嚷着要先去找四位哥哥,让仅裹着睡衣的卢天快些换衣,但卢天却要他二人出去,说是不好意思。白玉堂调侃几句也就乖乖出去了,展昭却显然若有所思。
卢天究竟是怎么回事?瞧瞧他之前的睡姿,显得及其随意,卢方纵然对他百般疼爱,却也不至于让他如此随意。之后又非要撵我们出来,说是不好意思,前后实在太过矛盾。除非,他……
“我说猫儿,你干嘛,虽然你说浑身上下有些难受,也不至于这个样子吧?”白玉堂道,突然窜了过去,附耳道,“你这只臭猫,在想些什么?是不是找到什么线索了?”
展昭却并未回答他,正经问道:“白兄,你上岛之后,未见我之前,白玉老鼠还在你身上吗?”
白玉堂看展昭神情,知道事关重大,细细回想,可上岛之后,他一心只在几位兄长上,哪有功夫去查管这些,只得摇头:“我记不得了。”
展昭深吸了口气,重新问道:“那白兄在出了酒庄之后白玉老鼠……”
“那个时候,好像……好像还在。对!还在!”白玉堂猛地想起,那时自己在付帐时还见过白玉老鼠别与腰间。他似乎也想起什么,喃喃着,“怪也,既然我出了酒庄白玉老鼠还在身上,那对方何时拿走白玉老鼠却能让我丝毫不知?难道……”
这下子,展昭完全确定了自己的想法,他压低声音,一字一字道:
“有!
——卢天!”
“展叔叔,白五叔,我换好衣服了,可以走了吗?”卢天推开了房门,蹦蹦跳跳地出来了。展昭和白玉堂相视一眼,面上浮起笑容。
白玉堂笑着迎了上去,与往常无二,摸了摸他的头,道:“好了,咱么走吧!先从城北的小道出城,然后走小路,先去汴京,把这事禀报给包大人知道。走吧……”卢天眼珠子一转,跟着二人走了出去。
这一路上,除去卢天说是内急耽误了点功夫,还算顺畅。
出了城门口,便见一条蜿蜒小道如蛇行,行了数十步,林子越加茂密,鸟叫声此起彼伏,却并未甜美,反倒给人一种幽深寂静的凄凉。不过几里,前面飘来阵阵似花香却又不像花香的味道,吸入少许,展昭和白玉堂忽然双腿一软,头脑一涨,直挺挺地倒了下去。卢天见状连忙上前呼唤了几声,见二人并未有回应,气息微弱,又狠狠踢了踢白玉堂几脚,还是没有反应,不禁冷笑道:“什么南侠锦毛鼠,还不是这么容易就着了道。大哥,你们出来吧!”
几名身手敏捷的男子应声而出,见了倒在地上的二人,俯掌大笑道:“哈哈,老六,你果真是厉害啊!堂堂南侠和锦毛鼠,就这样落网了!”
‘卢天’谦虚笑道:“诶,这是主子的计谋过人!以及大哥下毒下得及时。这两个傻瓜,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可爱的小侄子是我唐六!”
“好了,废话不多说了,挪,你们两个把这药给他俩服下!”那名被唤作‘大哥’的人从怀中拿出早已备好的几颗药丸,递给身后的两人,命令道。那两人也不惧展昭白玉堂,在他们眼里,现在这白玉堂和展昭无非是两具尸体。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从唐门的毒药中活命。
然而,当药丸即将入口时,事情却起了峰回路转的变化。
只见两人双目一睁,白玉堂一手抓住面前人的手腕,猛翻手腕只听得骨关节碎裂的声音和这人的惨叫声,然后放手又是一掌,当场毙命。展昭也下了狠手,一掌击向那人胸口,虽然只用了五成功力,却足以让眼前人毙命。得手后两人一跃,立起身来,望着剩余几人,面露杀意。
然而那几人却并未有惧怕的神色,只是眉头皱紧,像是有些不敢相信。
“你们……你们怎么会?”唐六一见二人起身,便立即站回他们人的身边,带着些许惊讶问道。
白玉堂冷哼一声,不屑道:“你们这些雕虫小技,哪能瞒得过五爷?我和猫儿早就闭气了……”
展昭接口道:“其实一开始我和白兄完全没有怀疑你是卢天,然而,你今日清晨的睡姿却让我生疑。的确,卢夫人以前管教天儿时不拘束于文人,很是随意,但后来你却要我二人出房。这点令展某不解。除非你装作这样的原因是为了掩饰自己昨夜给我二人下得毒吧。只可惜昨夜展某并未发觉。后来我与白兄交谈之下,得知白兄的白玉老鼠在出了酒庄之后还在身上,才明白过来。一则白兄若是在大醉时被偷,那情有可原,可若是在白兄清醒的状态下能偷走这白玉老鼠且不惊动他的,目前,世上能做到的只怕屈指可数。”展昭顿了顿,白玉堂万分满意地听着,面上带着几许笑容。然而展昭下一刻说的话,却着实被白玉堂气得七窍生烟。“然而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也不能太过笃定,屈指可数也就是说还是有人可以做到。展某自问不行,但展某家师却可以。二则即使有人在白兄出酒庄之后偷走白玉老鼠,然后送去陷空岛,断然三日之内是到不达的,何况唐六你说卢员外是在展某到达的前一夜和其余三鼠出的岛。那更是不可能。然而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飞鸽传书。但是,你又说过,岛上并未飞进过任何的鸽子,这不正好自相矛盾吗?就凭这两点,便可断定你非卢天,却在说谎!”
唐六听着,只觉得每条道理如此清晰,忍不住赞道:“不错不错。只是,白玉堂身上的白玉老鼠的确不在了,这你怎么解释?”
展昭平静道:“其实,那白玉老鼠应是阁下扮作卢天在被白玉堂携带出岛时拿走的。那时你已是‘卢天’,我们自然不会对你堤防。”
唐六点了点头,附掌赞道:“真是聪明啊!看来的确是我们轻敌了。”
展昭淡淡一笑道:“然而,展某也有几处不明。请指教一二:其一、凭你们刚才的毒药和你姓唐,展某猜测你们应是唐门中人,展某自问从未得罪你们,为何你们下此毒手?其二、你的易容
绛旓細灞曟槶椋炶韩鍏ュ眿,鍕夊己韫插湪杩欏皯骞磋韩鏃,瀹夋叞鐫:鈥滃ぉ鍎,娌′簨鐨勩傝窡鍙斿彅璧板惂!鈥濅箣鍓嶅崲鏂瑰湪鍥借垍妗堜腑鎼虹潃鍎垮瓙鏇剧粡瑙佽繃灞曟槶,鍗㈠ぉ鑷劧璁ゅ緱,瑙佸睍鏄潵浜,蹇冧腑娆㈠枩,涓嶄綇鐐瑰ご鎷嶆墜閬:鈥滃睍鍙斿彅鎮ㄦ潵浜,蹇晳鏁戝ぉ鍎垮惂!鈥濊█缃,灞曟槶璧疯韩姝e噯澶囧甫鍗㈠ぉ绂诲紑鏃,浠栬儗鍚庣獊鐒舵湁涓鏍硅鐑ф柇鐨勬í姊佸悜浠栦簩浜虹牳鏉ャ傚崲澶╂儕鍙亾:鈥滃睍鍙斿彅,灏忓績鍟...
绛旓細灞曟槶鍒濆叆寮灏佸簻涔嬫椂锛屽寘鍏浘缁忎翰鍙i棶杩鍗椾緺灞曟槶鍑鸿嚜鍝綅楂樹汉鐨勯棬涓锛熷睍鏄鍥炵瓟鑷繁鏇捐窡闅忚タ娲嬪墤瀹㈠鐜夊瀛﹁壓浜斿勾锛屽綋鐒朵篃璁稿睍鏄湁澶氫綅甯堝倕锛屼絾鏄鐜夊鏄剧劧鏄灞曟槶鐨鎺堣壓鎭╁笀涔嬩竴銆
绛旓細鍙ゅ吀鍚嶈憲銆婁笁渚犱簲涔夈嬪嚭鐜板睍鏄繖涓鑹锛屽瓧鐔婇锛屽皯骞磋渚狅紝浠楀墤鍥涙柟锛屽洜姝ゅ湪褰撴椂鍚嶉渿鍥涙柟锛屽洜闀垮眳鍦ㄦ睙鍗楄岃灏婄О涓衡滃崡渚犫濄傚睍鏄嚭鍦烘椂骞寸邯浜屽崄宀佸乏鍙筹紝鍠勮交鍔熴佷細琚栫銆佸墤娉曢珮瓒咃紝鍏靛垉涓哄悕鍓戝法闃欙紝鍚庡湪鑼夎姳鏉戜笌鍏跺涓佹湀鍗庡畾浜叉椂浜ゆ崲浜嗘箾鍗傚睍鏄负浜鸿唉鍜屻佸剴闆呫侀鏈夊悰瀛愪箣椋庯紝骞朵笖姝﹁壓楂樺己銆佸娆℃嫰鏁戝寘...
绛旓細灞曟槶锛屽瓧鐔婇锛屽父宸炲簻姝﹁繘鍘块亣鏉版潙浜烘皬銆傞娆″嚭鍦烘椂鏄鐢熸墦鎵紝鍏呮弧鑻遍泟姘旀锛岄潰甯︾潃渚犳皵锛屾皵瀹囪僵鏄傘傝嚜骞间範姝︼紝姝﹁壓楂樺己锛屽杽杞诲姛锛屼細琚栫锛屽墤娉曠粷浼︼紝鍏靛垉涓哄法闃欏墤銆傚悗鍦ㄨ寜鑺辨潙涓庡叾濡讳竵鏈堝崕瀹氫翰鏃朵氦鎹簡婀涘崲鍓戯紝璋﹀拰鏈夌ぜ銆佹矇绋冲ぇ姘斻佸繝鑲濅箟鑳嗭紝鍙椾汉灏婃暚锛屾槸鈥滀笁渚犫 閲岀殑鈥鍗椾緺鈥濓紝鍑哄満骞寸邯浜屽崄澶氬瞾...
绛旓細寮烘帹瀵规垜鏈夊府鍔 銆婂埌寮灏佸簻娣蜂釜鍏姟鍛樸嬧斺斿緢鑰鐨勬枃浜嗭紝褰撹宸紝鐢蜂富灞曟槶銆傘婇樋楹︿粠鍐涖嬧斺斿コ瀛愪粠鍐涙枃锛屼竴鐐瑰緢涓嶉浄锛屽緢鐑寰堝ぇ姘旓紝闈炲父鎺ㄨ崘锛併婃瀹夊槈璇濄嬮偅閭o細銆婂悰鐜嬩晶銆嬨婂啝缁濈瑧澶╀笅銆嬪畨鑻ョ伅锛氥婅渶濂冲磭鍢忎紶銆嬨婄帇灏嗐嬨婅儹鑴傛壂濞ョ湁銆嬪腑鏈堢罕锛氥婃矙鍦虹鐐瑰叺銆嬨婄姸鍏冩父銆嬨婁竴浠d綖鑷c嬨婇晣榄傝皟...
绛旓細銆婂拰浜插叕涓汇嬬殑鎻忓啓鎵嬫硶鏈変簺灏忕櫧,娌℃湁涓鑸┛瓒鏂囨枃缁夌粔鐨勭敤璇,娌℃湁銆婅瘲缁忋嬨佸攼璇椼佸畫璇嶇殑娉涙互,娌℃湁鐐銆婂ぇ涓嶅垪棰犵櫨绉戝叏涔︺,浣嗕粠鏂囧瓧鍗寸湅寰楀嚭浣滆呯殑蹇冪粏,瀛楀瓧鍙ュ彞閮芥潵鑷瀛愮殑鐢熸椿鍜屾濇兂銆傛鏉ㄧ殑琛屼负澶уぇ鍜у挧,缁欏埆浜虹湅鐨勯兘鏄ス鍧氬己鐨勯偅涓闈,鍝曟槸纭拺,浣嗗悓鏃跺ス鍙堟槸涓劅鎯呯粏鑵荤殑浜,鎴戞兂鎴戝氨鏄濂充富鐨勮繖...
绛旓細銆婂拰浜插叕涓汇嬬殑鎻忓啓鎵嬫硶鏈変簺灏忕櫧,娌℃湁涓鑸┛瓒鏂囨枃缁夌粔鐨勭敤璇,娌℃湁銆婅瘲缁忋嬨佸攼璇椼佸畫璇嶇殑娉涙互,娌℃湁鐐銆婂ぇ涓嶅垪棰犵櫨绉戝叏涔︺,浣嗕粠鏂囧瓧鍗寸湅寰楀嚭浣滆呯殑蹇冪粏,瀛楀瓧鍙ュ彞閮芥潵鑷瀛愮殑鐢熸椿鍜屾濇兂銆傛鏉ㄧ殑琛屼负澶уぇ鍜у挧,缁欏埆浜虹湅鐨勯兘鏄ス鍧氬己鐨勯偅涓闈,鍝曟槸纭拺,浣嗗悓鏃跺ス鍙堟槸涓劅鎯呯粏鑵荤殑浜,鎴戞兂鎴戝氨鏄濂充富鐨勮繖...
绛旓細鐪嬭捣鏉ュ儚鏄竴绡囨病鏂版剰鐨勫皬鐧芥枃,浣嗗疄闄呬笂鏂囩珷寰堜笉閿,铔悶绗戠殑銆傘婂澶氱泭鍠勩(瀹岀粨鏋剁┖HE):涓嶇敤璇翠簡,绌胯秺鐨勭粡鍏告枃,寰堣交鏉鐨勬枃鏂囥 鏂囨: 杞笘閲嶇敓鍒颁簡鍙や唬鏃剁┖,鍘熶互涓虹粓浜庡彲浠ュ績瀹夌悊寰楀湴鍋氫竴鍥炵背铏,鎬庢枡鍗存槸涓埞涓嶄翰銆佸涓嶇埍鐨勪富,鏃犲,鍙緱鑷姏鏇寸敓,鑹拌嫤鍒涗笟銆 鈥滈噾瀛愩佹埧瀛愩侀摵瀛愩佸瀛愩佺編鐢峰瓙!澶氬鐩婂杽...
绛旓細銆婂拰浜插叕涓汇嬬殑鎻忓啓鎵嬫硶鏈変簺灏忕櫧,娌℃湁涓鑸┛瓒鏂囨枃缁夌粔鐨勭敤璇,娌℃湁銆婅瘲缁忋嬨佸攼璇椼佸畫璇嶇殑娉涙互,娌℃湁鐐銆婂ぇ涓嶅垪棰犵櫨绉戝叏涔︺,浣嗕粠鏂囧瓧鍗寸湅寰楀嚭浣滆呯殑蹇冪粏,瀛楀瓧鍙ュ彞閮芥潵鑷瀛愮殑鐢熸椿鍜屾濇兂銆傛鏉ㄧ殑琛屼负澶уぇ鍜у挧,缁欏埆浜虹湅鐨勯兘鏄ス鍧氬己鐨勯偅涓闈,鍝曟槸纭拺,浣嗗悓鏃跺ス鍙堟槸涓劅鎯呯粏鑵荤殑浜,鎴戞兂鎴戝氨鏄濂充富鐨勮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