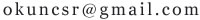求:余光中《塔》的原文,谢谢啦~! 文学学习的好处?
\u6587\u5b66\u7c7b\u6307\u54ea\u4e9b\u4e13\u4e1a\uff1f\u6587\u5b66\u7c7b\u4e13\u4e1a\u65e0\u975e\u4e09\u7c7b\uff0c\u4e2d\u6587\u3001\u5916\u8bed\u548c\u65b0\u95fb\u4f20\u64ad\uff0c\u6bcf\u4e2a\u5206\u7c7b\u4e0b\u7684\u5404\u79cd\u4e13\u4e1a\uff0c\u6240\u5b66\u4e0d\u540c\uff0c\u5c31\u4e1a\u65b9\u5411\u81ea\u7136\u4e5f\u4e0d\u540c\uff0c\u4eca\u5929\u54b1\u4eec\u5c31\u6765\u8be6\u7ec6\u804a\u804a\u3002
1\u3001\u63d0\u9ad8\u7d20\u517b\uff0c\u63d0\u5347\u81ea\u8eab\u7684\u54c1\u4f4d\u3002
2\u3001\u662f\u611f\u77e5\u793e\u4f1a\u7684\u89e6\u89d2\uff0c\u5404\u4e2a\u5b66\u79d1\u90fd\u662f\u878d\u4f1a\u8d2f\u901a\u7684\uff0c\u5b66\u4e60\u6587\u5b66\u80fd\u591f\u5728\u4e00\u5b9a\u7a0b\u5ea6\u4e0a\u63d0\u5347\u4e00\u4e2a\u4eba\u5206\u6790\u95ee\u9898\u7684\u80fd\u529b\uff0c\u8fd9\u6837\u624d\u80fd\u89e6\u7c7b\u65c1\u901a\u3002
3\u3001\u5b66\u4e60\u6587\u5b66\uff0c\u4e5f\u662f\u4e00\u79cd\u7f8e\u7684\u4eab\u53d7\uff0c\u6587\u5b66\u4e2d\u6240\u542b\u62ec\u7684\u667a\u6167\u3001\u4eba\u6587\u7cbe\u795e\u662f\u5176\u4ed6\u5b66\u79d1\u96be\u4ee5\u5ab2\u7f8e\u7684\u3002
4\u3001\u5b66\u4e60\u672c\u56fd\u6587\u5b66\uff0c\u5f53\u7136\u4e5f\u662f\u4e00\u79cd\u6587\u5316\u7684\u4f20\u627f\u3002\u6bcf\u4e00\u4e2a\u56fd\u5bb6\u90fd\u6709\u81ea\u5df1\u7684\u72ec\u7279\u7684\u6587\u5316\uff0c\u4f55\u51b5\u4f5c\u4e3a\u56db\u5927\u6587\u660e\u53e4\u56fd\u7684\u4e2d\u56fd\uff0c\u5176\u6587\u5316\u66f4\u662f\u6e0a\u6e90\u6d41\u957f\uff0c\u4f20\u627f\u8fd9\u4e9b\u6587\u5316\u7cbe\u9ad3\u2014\u2014\u6587\u5b66\u662f\u6bcf\u4e00\u4e2a\u534e\u590f\u4eba\u7684\u9690\u800c\u4e0d\u73b0\u4f46\u771f\u771f\u5b9e\u5b9e\u7684\u8d23\u4efb\u3002
\u6269\u5c55\u8d44\u6599\uff1a
\u6587\u5b66\u662f\u4e00\u79cd\u8bed\u8a00\u827a\u672f\uff0c\u662f\u8bdd\u8bed\u8574\u85c9\u4e2d\u7684\u5ba1\u7f8e\u610f\u8bc6\u5f62\u6001\u3002\u8bd7\u6b4c\u3001\u6563\u6587\u3001\u5c0f\u8bf4\u3001\u5267\u672c\u3001\u5bd3\u8a00\u3001\u7ae5\u8bdd\u7b49\u4e0d\u540c\u4f53\u88c1\uff0c\u662f\u6587\u5b66\u7684\u91cd\u8981\u8868\u73b0\u5f62\u5f0f\u3002
\u6587\u5b66\u4ee5\u4e0d\u540c\u7684\u5f62\u5f0f\u5373\u4f53\u88c1\uff0c\u8868\u73b0\u5185\u5fc3\u60c5\u611f\uff0c\u518d\u73b0\u4e00\u5b9a\u65f6\u671f\u548c\u4e00\u5b9a\u5730\u57df\u7684\u793e\u4f1a\u751f\u6d3b\u3002\u4f5c\u4e3a\u5b66\u79d1\u95e8\u7c7b\u7406\u89e3\u7684\u6587\u5b66\uff0c\u5305\u62ec\u4e2d\u56fd\u8bed\u8a00\u6587\u5b66\u3001\u5916\u56fd\u8bed\u8a00\u6587\u5b66\u53ca\u65b0\u95fb\u4f20\u64ad\u5b66\u3002
\u6587\u5b66\u662f\u5c5e\u4e8e\u4eba\u6587\u5b66\u79d1\u7684\u5b66\u79d1\u5206\u7c7b\u4e4b\u4e00\uff0c\u4e0e\u54f2\u5b66\u3001\u5b97\u6559\u3001\u6cd5\u5f8b\u3001\u653f\u6cbb\u5e76\u9a7e\u4e8e\u793e\u4f1a\u5efa\u7b51\u4e0a\u5c42\u3002\u5b83\u8d77\u6e90\u4e8e\u4eba\u7c7b\u7684\u601d\u7ef4\u6d3b\u52a8\u3002
\u6700\u5148\u51fa\u73b0\u7684\u662f\u53e3\u5934\u6587\u5b66\uff0c\u4e00\u822c\u662f\u4e0e\u97f3\u4e50\u8054\u7ed3\u4e3a\u53ef\u4ee5\u6f14\u5531\u7684\u6292\u60c5\u8bd7\u6b4c\u3002\u6700\u65e9\u5f62\u6210\u4e66\u9762\u6587\u5b66\u7684\u6709\u4e2d\u56fd\u7684\u300a\u8bd7\u7ecf\u300b\u3001\u5370\u5ea6\u7684\u300a\u7f57\u6469\u884d\u90a3\u300b\u548c\u53e4\u5e0c\u814a\u7684\u300a\u4f0a\u5229\u6602\u7eaa\u300b\u7b49\u3002
\u4e2d\u56fd\u5148\u79e6\u65f6\u671f\u5c06\u4ee5\u6587\u5b57\u5199\u6210\u7684\u4f5c\u54c1\u90fd\u7edf\u79f0\u4e3a\u6587\u5b66\uff0c\u9b4f\u664b\u4ee5\u540e\u624d\u9010\u6e10\u5c06\u6587\u5b66\u4f5c\u54c1\u5355\u72ec\u5217\u51fa\u3002\u6b27\u6d32\u4f20\u7edf\u6587\u5b66\u7406\u8bba\u5206\u7c7b\u6cd5\u5c06\u6587\u5b66\u5206\u4e3a\u8bd7\u3001\u6563\u6587\u3001\u620f\u5267\u4e09\u5927\u7c7b\u3002\u73b0\u4ee3\u901a\u5e38\u5c06\u6587\u5b66\u5206\u4e3a\u8bd7\u6b4c\u3001\u5c0f\u8bf4\u3001\u6563\u6587\u3001\u620f\u5267\u56db\u5927\u7c7b\u522b\u3002
\u6587\u5b66\u662f\u8bed\u8a00\u6587\u5b57\u7684\u827a\u672f\uff0c\u662f\u793e\u4f1a\u6587\u5316\u7684\u4e00\u79cd\u91cd\u8981\u8868\u73b0\u5f62\u5f0f\uff0c\u662f\u5bf9\u7f8e\u7684\u4f53\u73b0\u3002\u6587\u5b66\u4f5c\u54c1\u662f\u4f5c\u5bb6\u7528\u72ec\u7279\u7684\u8bed\u8a00\u827a\u672f\u8868\u73b0\u5176\u72ec\u7279\u7684\u5fc3\u7075\u4e16\u754c\u7684\u4f5c\u54c1\uff0c\u79bb\u5f00\u4e86\u8fd9\u6837\u4e24\u4e2a\u6781\u5177\u4e2a\u6027\u7279\u70b9\u7684\u72ec\u7279\u6027\u5c31\u6ca1\u6709\u771f\u6b63\u7684\u6587\u5b66\u4f5c\u54c1\u3002\u4e00\u4e2a\u6770\u51fa\u7684\u6587\u5b66\u5bb6\u5c31\u662f\u4e00\u4e2a\u6c11\u65cf\u5fc3\u7075\u4e16\u754c\u7684\u82f1\u96c4\u3002
\u6587\u5b66\u4ee3\u8868\u4e00\u4e2a\u6c11\u65cf\u7684\u827a\u672f\u548c\u667a\u6167\u3002\u6587\u5b66\uff0c\u662f\u4e00\u79cd\u5c06\u8bed\u8a00\u6587\u5b57\u7528\u4e8e\u8868\u8fbe\u793e\u4f1a\u751f\u6d3b\u548c\u5fc3\u7406\u6d3b\u52a8\u7684\u5b66\u79d1\uff0c\u5c5e\u793e\u4f1a\u610f\u8bc6\u5f62\u6001\u8303\u7574\u3002
\u53c2\u8003\u8d44\u6599\u6765\u6e90\uff1a\u767e\u5ea6\u767e\u79d1-\u6587\u5b66
《塔》——余光中
一放暑假,一千八百个男孩和女孩,像一蓬金发妙鬘的蒲公英,一吹,就散了。于是这座黝青色的四层铁塔,完全属他一人所有。永远,它矗立在此,等待他每天一度的临幸,等待他攀登绝顶,阅读这不能算小的王国。日落时分,他立在塔顶,端端在寂天寞地的圆心。一时暮色匍匐,万籁在下,塔无语,王亦无语,唯钢铁的纪律贯透虚空。太阳的火球,向马里兰的地平下降。
黄昏是一只薄弱的耳朵,频震于乌鸦的不谐和音。鸦声在西,在琥珀的火堆里裂开。西望是艳红的熔岩,自太阳炉中喷出,正淹没当日南军断肠之处,今日艾森豪的农庄。东望不背光,小圆丘上,北军森严的炮位,历历可数。华盛顿在南,白而直的是南下的州道。同一条公路,北驶三英里,便是葛底斯堡的市区了。这一切,这一圈连环不解的王国,完全属他一人所有。
葛底斯堡啊,葛底斯堡。他的目光抚玩着小城的轮廓。来这里半年,他已经熟悉每一条街,每一座有历史的建筑。哪哪,刺入晚空的白塔尖,是路德教堂。风雨打黑的是文学院的钟楼,雉堞上栖着咕咕的野鸽。再过去,是黑阶白柱的“老宿舍”,内战时,是北军骑兵秣马的营地。再过去,再过去该是他的七瓴古屋的绿顶了,虽然他的眼力已经不逮。
就在那绿顶下,他度过寥落又忙碌的半年,读书、写诗,写长长的航空信,翻译公元前的古典文学,为了那些金鬘的、褐鬘的女弟子,那些洋水仙。那些洋水仙。纳巴科夫称美国的小女孩做nymphet。他班上的女孩应该是nymph,他想。就在那绿得不可能的绿顶下,那些洋水仙,那些牛奶灌溉的洋水仙,像一部翻译小说的女角那样,走进去,听他朗吟缠绵的《湘夫人》,壮烈的《国殇》。笑他太咸的鱼,太淡的黑莓子酒。他为她们都取了中国名字。金发是文葩。粟发是倪娃。
金中带栗的是贾翠霞。她们一来,就翻出他的牙筷,每样东西都夹一下。最富侵略性的,是文葩,搜他的冰箱,戴他的雨 帽,翻他的中文字典,皱起眉毛,寻找她仅识的半打象形文字。他戏呼她们为疯水仙,为希腊太妹,为bacchanals。他始终不能把她们看清楚,因为她们动得太快,晃得太厉害。因为碧睛转时,金发便跟着飘扬。她们来时,说话如吟咏,子音爽脆,母音婉柔。她们走后,公寓里犹晃动水仙的影子。他总想教她们停下来,让他仔细阅读那些瞳中的碧色,究竟碧到什么程度。
但塔下只有碧草萋萋。晚风起处,脚下的新枫翻动绿阴。这是深邃的暑假,水仙们都已散了,有的随多毛的牧神,有的,当真回欧洲去了。翠霞要嫁南方的羊蹄人。文葩去德国读日耳曼文学。终于都散了,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散了,正如当初,莫名其妙地聚拢来一样。偌大的一片校园,只留下几声知更,只留下,走不掉而又没人坐的靠背长椅,怔怔对着花后的木兰。
牧神和水仙践过的芳草,青青如故。一觉醒来,怎么小城骤然老了三十岁?第一次,他发现,这里的居民多么龙钟,满街是警察、店员、保险商、收税吏、战场向导、面目模糊的游客。闷得发慌的下午,暑气炎炎,蟠一条火龙在林肯方场的顶空。车祸频起,救护车的警笛凄厉地宰割一条大街。
所以水仙们就这么散了。警笛代替了牧歌。羊蹄踹过的草地上,只留下一些烟蒂。临行前夕,神与兽,纷纷来叩门。“我们会惦记你的,”柯多丽说。“愿你能回来,再教我们。”倪娃拿走他的底片。一下午,羊蹄不断踢他的公寓。虬髯如盗的霍豪华,金发童颜的贝伯纳,邀他去十英里外,方丈城的一家德国餐馆,叫Hofbrauhaus的,去大嚼德国熏肉和香肠,豪饮荷兰啤酒。熏肉和香肠他并不特别喜欢,但饮起啤酒来,他不醉不止。
笨重而有柄的史泰因大陶杯,满得欲溢的醇醪,浮面酵起一层滃滃的白沫,一口芳冽,顿时有一股豪气,自胃中冲起,饮者欲哭欲笑,欲拔剑击案而歌。唱机上回旋着德意志的梦,舒伯特的梦,舒曼的梦。绞人肚肠的一段小提琴,令他想起以前同听的那人,那人慵懒的鼻音。他非常想家。他尖锐地感到,离家已经很久,很远了。公寓里的那张双人床,那未经女性的柔软和浑圆祝福过的,荒凉如不毛的沙漠。那夜他是醉了。昏黄的新月下,他开车回去,险些撞在一株老榆树上。
第二天,他起得很迟。坐在参天的老橡阴下,任南风拂动鬓发,宿酲中,听了一下午琐琐屑屑细细碎碎申申诉诉说说的鸟声。声在茂叶深处渗出漱出。他从来没有听过那样好听的鸣禽,也从未像那天那么想家。他说不出是知更还是画眉。鸣者自鸣。聆者欢喜赞叹地聆听。他坐在重重叠叠浓浓浅浅的绿思绿想中。他相信自己的发上淌得下沁凉的绿液。城春。城夏。
草木何深深。泰山耸着。黄河流着。……东方已有太多的伤心,又何必黯然,为几个希腊太妹?他想起,好久,好久没接触东方的温婉了。隐身的歌者仍在歌着。他幻想,自己在抚弄一只手,白得可以采莲的一只手。而且吟一首《念奴娇》向一只娇小的耳朵,乌发下的耳朵。隐身的歌者仍在歌着。
她来后。她来后。她来后。他的生命似乎是一场永远的期待,期待一个奇迹,期待一个蜃楼变成一座俨然的大殿堂。期待是一种半清醒半疯狂的燃烧,使焦灼的灵魂幻觉自己生活在未来。灵魂,不可能的印第安雷鸟①,不可能柔驯地伏在此时此刻的掌中,它的翅膀更喜欢过去的风,将来的云。
他钦羡英雄和探险家,羡他们能高度集中地孤注一掷地生活在此时此地,在血的速度呼吸的节奏,不必,像他那样,经常病态地生活在回忆和期待。生死决斗的武士,八肢互绞的情人,与山争高的探险家,他钦羡的是这些。他更钦羡阿拉伯的劳伦斯,同一只手,能陷城,也能写诗,能测量沙漠,也能探索灵魂,征服自己,且征服敌人。
第三天,停车场上空落落的,全部走光了。因是废园。城是死城。他缓缓走下无人的林阴道,感到空前的疲倦。只有他不能离开,七月间,他将走得更远。他将北上纽约,循传说中惧内猎人的足迹,越过凯茨基山,向空阔的加拿大。但在那之前,他必须像一个白发的老兵,独守一片古战场。小城四郊的墓碑,多于铜像,铜像多于行人。
至少墓碑的那一面很热闹,自虐而自嘲地,他想道。至少夜间比昼间热闹。夜间,猫眼的月为鬼魂唱一整个通宵,连窗上的雏菊也失眠了。电影院门首的广告画,虚张声势,探手欲攫迟归的行人。只有逃不掉的邮筒,患得患失地伫立在街角。子夜后的班车,警铃叮叮,大惊小怪地踹过市中心,小城的梦魇陷得更深。为何一切都透明得可怕?这里没有任何疆界。现在覆叠着将来。
他走过神学院走过蜡像馆走过郁金香泣血的方场,但大半的时间,他走在梦里走在国内走在记忆的街上。这种完整而纯粹的寂寞,是享受,还是忍受,他无法分辨。冰箱充实的时候,他往往一星期不讲一句话。信箱空洞的时候,他似乎被整个世界所遗忘,且怀疑自己的存在。立在塔顶,立在钢铁架构的空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时人亦冷漠而疏远。
何以西方茫茫,东方茫茫?寂寞是国,我是王,自嘲兼自慰,他想。她来后,她来后便是后,和我同御这水晶的江山。她来后,一定带她来塔顶,接受寂寞国臣民的欢呼,铜像和石碑的欢呼,接受两军铁炮冥冥的致敬,鼓角齐奏,鬼雄悲壮的军歌。她来后,一定要带她去那张公园椅上,告诉她,他如何坐在那椅上,读她的信。也要她去抚摸街角的那个信箱,那是他所有航空信的起站。她来后,一定要带她去那家德国餐馆,要她也尝尝,那种冰人肺腑的芳冽,他想。
但此刻,天上地下,只剩下他一人。鸦已栖定。落日已灭亡。剩下他,孤悬于回忆和期待之间,像伽利略的钟摆,向虚无的两端逃遁,而又永远不能逸去。剩下他,血液闲着,精液闲着,泪腺汗腺闲着,愤怒的呐喊闲着。剩下他,在恐惧之后回顾恐惧,危险之前预期危险。对于他,这是过渡时期,渡船在两个岸间飘摆。这是大征伐中,一段枕剑的小小假寐。
因为他的战场,他的床,他的沙漠在中国,在中国,在日落的方向,他的敌人和情人和同伴同伴。自从他选择了笔,自从他选择了自己的武器,选择了蓝色的不是红色的血液,他很久没有享受过深邃安详如一座寺院的暑假,如他现在所享受的一样。暑假是时间的奢侈品,属于看云做梦的少年。
他用单筒的记忆,回顾小时候的那些暑假,当夏季懒洋洋地长着,肥硕而迟钝如一只南瓜,而他,悠闲如一只蝉。那些椰荫下的,槐阴下的,黄桷树阴下的暑假。读童话,读神话,读天方夜谭的暑假。那时,母亲可靠如一株树,他是树上唯一的果子。那时,他有许多“重要”的同学,上课同桌,睡觉同床,记过时,同一张布告,诅咒时,以彼此的母亲为对象。那些暑假呢?那些母亲呢?那些重要的伙伴呢?
至少他的母亲已经死了,好客的伯母死了,在另一座塔下。那里,时间毫无意义地流着,空间寄托在宗教的租界。是处梵呗如呓,香火在神龛里伸着懒腰。他来自塔的国度。古老的上国已经陆沉,只留下那些塔,兀自顽强地自尊地零零落落地立着,像一个英雄部落的遗族。第二次大战后,他和母亲乘汽船,顺长江东下。船泊安庆。
母与子同登佛寺的高塔,俯瞰江面的密樯和城中的万户灰甍。塔高风烈。迷蒙的空间晕眩的空间在脚下,令他感觉塔尖晃动如巨桅,而他是一只鹰,一展翅一切云都得让路。十九岁的男孩,厌倦古国的破落与苍老。外国地理是他最喜欢的一门课。
暑假的下午,半亩的黄桷树阴下,他会对着诱人的地图出神,怔怔望不厌意大利在地中海濯足,多龙的北欧欲噬丹麦,望不厌象牙海岸,尼罗河口,江湖满地的加拿大,岛屿满海的澳洲。从一本日历上,他看到一张风景照片,一列火车,盘旋而上庞伟的落基山,袅袅的黑烟曳在空中。他幻想自己坐在这车上,向芝加哥,向纽约,一路阅览雪峰和连嶂。去异国。去异国。去遥远的异国,永远离开平凡的中国。
安庆到葛底斯堡,两座塔隔了二十年。立在这座钢筋的了望塔上,立在二十年的这一边,他抚摸二十年前的自己,自己的头发,自己的幼稚,带着同情与责备。世界上最可爱最神秘最伟大的土地,是中国。踏不到的泥土是最香的泥土。远望岂能当归,岂能当归?就如此刻,山外是平原,平原之外是青山是青山。俄亥俄之外是印第安纳之外是艾奥瓦是内布拉斯加是内华达,乌鸦之西仍是乌鸦是归巢的乌鸦。
唯他的归途是无涯是无涯是无涯。半世纪来,多少异乡人曾如此眺望?胡适之曾如此眺望。闻一多如此眺望。梁实秋如此眺望。五四以来,多少留学生曾如此眺望。珊瑚色渐渐吸入加稠的怅青,西南仍有一派依恋的余光。葛底斯堡的方向,灯火零零落落地亮起。值得怀念的小城啊,他想,百年前的战场,百年后的公园,葛底氏之堡,林肯的自由的殿堂。一列火车正迤迤逦逦驶过市中心。
当日林肯便乘这种火车,来这里向阵亡将士致敬,且发表那篇演说。他预感得到,将来有人会怀念这里,在中国,怀念这一段水仙的日子,寂寞又自由的日子,在另一个战场,另一种战争之中。这次回去,他将再度加入他的同伴,他将投身历史滔滔的浊流,泳向旋涡啊大旋涡的中心。因为那也是一种内战。文化的内战,精神的内战,我与自己的决斗,为了攻打中国人偏见的巴士底狱,解放孔子后裔的想像力和创造的生命。也许他成功。也许他失败。但未来的历史将因之改向。
但在回去之前,他必须独自保持清醒的燃烧。就如那边的北极星,冷静地亮着,不失自己的方向,且为其他的光,守住一个定点。夜色部署得很快,顷刻间,恫吓已呈多面,从鼠灰到黝青到墨黑。但黑暗只有加强星的光芒。星的阵图部署得更快,在夜之上,在万籁之上之上,各种姓名的光,从殉道的红到先知的皎白透青,一一宣布自己的方位。他仰面向北,发现大熊和小熊开阔而灿明,如一面光之大纛,永不下半旗,那角度,比国内所见的高出许多。
抓住冻手的栏杆,他感到金属上升的意志和不可动摇的力量。他感到,钢铁的生命,从他的掌心、脚心上升,如忠于温度的水银,逆流而且上升,达于他的四肢,他的心脏。在一个疯狂的豁然的顷刻,他幻觉自己与塔合为一体,立足在坚实的地面,探首于未知的空间,似欲窃听星的谜语,宇宙大脑微妙的运行。一霎间,他欲引吭长啸。
但塔的沉默震慑住他。挺直的脊椎,纵横的筋骨,回旋梯的螺形回肠,挣扎时振起一种有秩序的超音乐。寂寞啊寂寞是一座透明的堡,冷冷地高,可以俯览一切,但离一切都那么遥远。鸟与风,太阳与霓虹,都从他架空的胸肋间飞逝,留下他,留下塔,留下塔和他,在超人的高纬气候里,留下一座骄傲的水晶牢,一座形而上的玻璃建筑,任他自国,自毁,自拯,或自卫。
1965年6月17日,葛底斯堡
扩展资料:
余光中的《塔》是一篇抒情散文,抒发了海外游子对祖国、故乡、亲人的思恋,通过内心的决斗和痛苦衬托出作者思恋之重,多种修辞手法融于叙事、状物、写景与明理之中,表现了作者才力富厚,左右逢源的大家风彩。
余光中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自称为自己写作的“四度空间”,被誉为文坛的“璀璨五彩笔”。驰骋文坛逾半个世纪,涉猎广泛,被誉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其文学生涯悠远、辽阔、深沉,为当代诗坛健将、散文重镇、著名批评家、优秀翻译家。现已出版诗集 21 种;散文集 11 种;评论集 5 种;翻译集 13 种;共 40 余种 。代表作有《白玉苦瓜》(诗集)、《记忆像铁轨一样长》(散文集)及《分水岭上:余光中评论文集》(评论集)等,其诗作如《乡愁》、《乡愁四韵》,散文如《听听那冷雨》、《我的四个假想敌》等,广泛收录于大陆及港台语文课本。
人物评价:
1、从诗歌艺术上看,余光中被誉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诗人”。他的作品风格极不统一,一般来说,他的诗风是因题材而异的。表达意志和理想的诗,一般都显得壮阔铿锵,而描写乡愁和爱情的作品,一般都显得细腻而柔绵。
2、其文学生涯悠远、辽阔、深沉,且兼有中国古典文学与外国现代文学之精神,创作手法新颖灵活,比喻奇特,描写精雕细刻,抒情细腻缠绵,一唱三叹,含蓄隽永,意味深长,韵律优美,节奏感强。他因此被尊为台湾诗坛祭酒。他的诗论视野开阔,富有开拓探索的犀利朝气;他强调作家的民族感和责任感,善于从语言的角度把握诗的品格和价值,自成一家。 [24] (人民网评)
3、余光中是个复杂而多变的诗人,他写作风格变化的轨迹基本上可以说是中国整个诗坛三十多年来的一个走向,即先西化后回归。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他开始认识到自己民族居住的地方对创作的重要性,把诗笔“伸回那块大陆”,写了许多动情的乡愁诗,对乡土文学的态度也由反对变为亲切,显示了由西方回归东方的明显轨迹,因而被台湾诗坛称为“回头浪子”。 [25] (中国台湾网评)
4、在新诗领域,余光中是艺术至上的拥护者;而在散文中,他认为,通过教育的普及,在大众化的基础上,文学是有机会兼顾艺术化的。他将五四运动以来的散文,以口语入文的散文和大众化划上等号,而称艺术化的散文为现代散文,意味着这类散文兼具现代人的生活内涵和创作形式上的现代手法。
5、余光中教授是一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学大师,以现代诗和散文享有盛誉。余教授的诗作多抒发诗人的悲悯情怀,对土地的关爱,以及对一切现代人、事、物的透视、解析与捕捉。此外,余教授还从事评论、编辑、翻译,皆有杰出成就。余教授毕生创作、治学,诲人不倦,于艺文,于学术,于社会,贡献深远;哲人其萎,范典永垂。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余光中
《塔》——余光中
一放暑假,一千八百个男孩和女孩,像一蓬金发妙鬘的蒲公英,一吹,就散了。于是这座黝青色的四层铁塔,完全属他一人所有。永远,它矗立在此,等待他每天一度的临幸,等待他攀登绝顶,阅读这不能算小的王国。日落时分,他立在塔顶,端端在寂天寞地的圆心。一时暮色匍匐,万籁在下,塔无语,王亦无语,唯钢铁的纪律贯透虚空。太阳的火球,向马里兰的地平下降。黄昏是一只薄弱的耳朵,频震于乌鸦的不谐和音。鸦声在西,在琥珀的火堆里裂开。西望是艳红的熔岩,自太阳炉中喷出,正淹没当日南军断肠之处,今日艾森豪的农庄。东望不背光,小圆丘上,北军森严的炮位,历历可数。华盛顿在南,白而直的是南下的州道。同一条公路,北驶三英里,便是葛底斯堡的市区了。这一切,这一圈连环不解的王国,完全属他一人所有。
葛底斯堡啊,葛底斯堡。他的目光抚玩着小城的轮廓。来这里半年,他已经熟悉每一条街,每一座有历史的建筑。哪哪,刺入晚空的白塔尖,是路德教堂。风雨打黑的是文学院的钟楼,雉堞上栖着咕咕的野鸽。再过去,是黑阶白柱的“老宿舍”,内战时,是北军骑兵秣马的营地。再过去,再过去该是他的七瓴古屋的绿顶了,虽然他的眼力已经不逮。就在那绿顶下,他度过寥落又忙碌的半年,读书、写诗,写长长的航空信,翻译公元前的古典文学,为了那些金鬘的、褐鬘的女弟子,那些洋水仙。那些洋水仙。纳巴科夫称美国的小女孩做nymphet。他班上的女孩应该是nymph,他想。就在那绿得不可能的绿顶下,那些洋水仙,那些牛奶灌溉的洋水仙,像一部翻译小说的女角那样,走进去,听他朗吟缠绵的《湘夫人》,壮烈的《国殇》。笑他太咸的鱼,太淡的黑莓子酒。他为她们都取了中国名字。金发是文葩。粟发是倪娃。金中带栗的是贾翠霞。她们一来,就翻出他的牙筷,每样东西都夹一下。最富侵略性的,是文葩,搜他的冰箱,戴他的雨帽,翻他的中文字典,皱起眉毛,寻找她仅识的半打象形文字。他戏呼她们为疯水仙,为希腊太妹,为bacchanals。他始终不能把她们看清楚,因为她们动得太快,晃得太厉害。因为碧睛转时,金发便跟着飘扬。她们来时,说话如吟咏,子音爽脆,母音婉柔。她们走后,公寓里犹晃动水仙的影子。他总想教她们停下来,让他仔细阅读那些瞳中的碧色,究竟碧到什么程度。
但塔下只有碧草萋萋。晚风起处,脚下的新枫翻动绿阴。这是深邃的暑假,水仙们都已散了,有的随多毛的牧神,有的,当真回欧洲去了。翠霞要嫁南方的羊蹄人。文葩去德国读日耳曼文学。终于都散了,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散了,正如当初,莫名其妙地聚拢来一样。偌大的一片校园,只留下几声知更,只留下,走不掉而又没人坐的靠背长椅,怔怔对着花后的木兰。牧神和水仙践过的芳草,青青如故。一觉醒来,怎么小城骤然老了三十岁?第一次,他发现,这里的居民多么龙钟,满街是警察、店员、保险商、收税吏、战场向导、面目模糊的游客。闷得发慌的下午,暑气炎炎,蟠一条火龙在林肯方场的顶空。车祸频起,救护车的警笛凄厉地宰割一条大街。
所以水仙们就这么散了。警笛代替了牧歌。羊蹄踹过的草地上,只留下一些烟蒂。临行前夕,神与兽,纷纷来叩门。“我们会惦记你的,”柯多丽说。“愿你能回来,再教我们。”倪娃拿走他的底片。一下午,羊蹄不断踢他的公寓。虬髯如盗的霍豪华,金发童颜的贝伯纳,邀他去十英里外,方丈城的一家德国餐馆,叫Hofbrauhaus的,去大嚼德国熏肉和香肠,豪饮荷兰啤酒。熏肉和香肠他并不特别喜欢,但饮起啤酒来,他不醉不止。笨重而有柄的史泰因大陶杯,满得欲溢的醇醪,浮面酵起一层滃滃的白沫,一口芳冽,顿时有一股豪气,自胃中冲起,饮者欲哭欲笑,欲拔剑击案而歌。唱机上回旋着德意志的梦,舒伯特的梦,舒曼的梦。绞人肚肠的一段小提琴,令他想起以前同听的那人,那人慵懒的鼻音。他非常想家。他尖锐地感到,离家已经很久,很远了。公寓里的那张双人床,那未经女性的柔软和浑圆祝福过的,荒凉如不毛的沙漠。那夜他是醉了。昏黄的新月下,他开车回去,险些撞在一株老榆树上。
第二天,他起得很迟。坐在参天的老橡阴下,任南风拂动鬓发,宿酲中,听了一下午琐琐屑屑细细碎碎申申诉诉说说的鸟声。声在茂叶深处渗出漱出。他从来没有听过那样好听的鸣禽,也从未像那天那么想家。他说不出是知更还是画眉。鸣者自鸣。聆者欢喜赞叹地聆听。他坐在重重叠叠浓浓浅浅的绿思绿想中。他相信自己的发上淌得下沁凉的绿液。城春。城夏。草木何深深。泰山耸着。黄河流着。……东方已有太多的伤心,又何必黯然,为几个希腊太妹?他想起,好久,好久没接触东方的温婉了。隐身的歌者仍在歌着。他幻想,自己在抚弄一只手,白得可以采莲的一只手。而且吟一首《念奴娇》向一只娇小的耳朵,乌发下的耳朵。隐身的歌者仍在歌着。
第三天,停车场上空落落的,全部走光了。因是废园。城是死城。他缓缓走下无人的林阴道,感到空前的疲倦。只有他不能离开,七月间,他将走得更远。他将北上纽约,循传说中惧内猎人的足迹,越过凯茨基山,向空阔的加拿大。但在那之前,他必须像一个白发的老兵,独守一片古战场。小城四郊的墓碑,多于铜像,铜像多于行人。至少墓碑的那一面很热闹,自虐而自嘲地,他想道。至少夜间比昼间热闹。夜间,猫眼的月为鬼魂唱一整个通宵,连窗上的雏菊也失眠了。电影院门首的广告画,虚张声势,探手欲攫迟归的行人。只有逃不掉的邮筒,患得患失地伫立在街角。子夜后的班车,警铃叮叮,大惊小怪地踹过市中心,小城的梦魇陷得更深。为何一切都透明得可怕?这里没有任何疆界。现在覆叠着将来。他走过神学院走过蜡像馆走过郁金香泣血的方场,但大半的时间,他走在梦里走在国内走在记忆的街上。这种完整而纯粹的寂寞,是享受,还是忍受,他无法分辨。冰箱充实的时候,他往往一星期不讲一句话。信箱空洞的时候,他似乎被整个世界所遗忘,且怀疑自己的存在。立在塔顶,立在钢铁架构的空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时人亦冷漠而疏远。何以西方茫茫,东方茫茫?寂寞是国,我是王,自嘲兼自慰,他想。她来后,她来后便是后,和我同御这水晶的江山。她来后,一定带她来塔顶,接受寂寞国臣民的欢呼,铜像和石碑的欢呼,接受两军铁炮冥冥的致敬,鼓角齐奏,鬼雄悲壮的军歌。她来后,一定要带她去那张公园椅上,告诉她,他如何坐在那椅上,读她的信。也要她去抚摸街角的那个信箱,那是他所有航空信的起站。她来后,一定要带她去那家德国餐馆,要她也尝尝,那种冰人肺腑的芳冽,他想。
她来后。她来后。她来后。他的生命似乎是一场永远的期待,期待一个奇迹,期待一个蜃楼变成一座俨然的大殿堂。期待是一种半清醒半疯狂的燃烧,使焦灼的灵魂幻觉自己生活在未来。灵魂,不可能的印第安雷鸟①,不可能柔驯地伏在此时此刻的掌中,它的翅膀更喜欢过去的风,将来的云。他钦羡英雄和探险家,羡他们能高度集中地孤注一掷地生活在此时此地,在血的速度呼吸的节奏,不必,像他那样,经常病态地生活在回忆和期待。生死决斗的武士,八肢互绞的情人,与山争高的探险家,他钦羡的是这些。他更钦羡阿拉伯的劳伦斯,同一只手,能陷城,也能写诗,能测量沙漠,也能探索灵魂,征服自己,且征服敌人。
但此刻,天上地下,只剩下他一人。鸦已栖定。落日已灭亡。剩下他,孤悬于回忆和期待之间,像伽利略的钟摆,向虚无的两端逃遁,而又永远不能逸去。剩下他,血液闲着,精液闲着,泪腺汗腺闲着,愤怒的呐喊闲着。剩下他,在恐惧之后回顾恐惧,危险之前预期危险。对于他,这是过渡时期,渡船在两个岸间飘摆。这是大征伐中,一段枕剑的小小假寐。因为他的战场,他的床,他的沙漠在中国,在中国,在日落的方向,他的敌人和情人和同伴同伴。自从他选择了笔,自从他选择了自己的武器,选择了蓝色的不是红色的血液,他很久没有享受过深邃安详如一座寺院的暑假,如他现在所享受的一样。暑假是时间的奢侈品,属于看云做梦的少年。他用单筒的记忆,回顾小时候的那些暑假,当夏季懒洋洋地长着,肥硕而迟钝如一只南瓜,而他,悠闲如一只蝉。那些椰荫下的,槐阴下的,黄桷树阴下的暑假。读童话,读神话,读天方夜谭的暑假。那时,母亲可靠如一株树,他是树上唯一的果子。那时,他有许多“重要”的同学,上课同桌,睡觉同床,记过时,同一张布告,诅咒时,以彼此的母亲为对象。那些暑假呢?那些母亲呢?那些重要的伙伴呢?
至少他的母亲已经死了,好客的伯母死了,在另一座塔下。那里,时间毫无意义地流着,空间寄托在宗教的租界。是处梵呗如呓,香火在神龛里伸着懒腰。他来自塔的国度。古老的上国已经陆沉,只留下那些塔,兀自顽强地自尊地零零落落地立着,像一个英雄部落的遗族。第二次大战后,他和母亲乘汽船,顺长江东下。船泊安庆。母与子同登佛寺的高塔①,俯瞰江面的密樯和城中的万户灰甍。塔高风烈。迷蒙的空间晕眩的空间在脚下,令他感觉塔尖晃动如巨桅,而他是一只鹰,一展翅一切云都得让路。十九岁的男孩,厌倦古国的破落与苍老。外国地理是他最喜欢的一门课。暑假的下午,半亩的黄桷树阴下,他会对着诱人的地图出神,怔怔望不厌意大利在地中海濯足,多龙的北欧欲噬丹麦,望不厌象牙海岸,尼罗河口,江湖满地的加拿大,岛屿满海的澳洲。从一本日历上,他看到一张风景照片,一列火车,盘旋而上庞伟的落基山,袅袅的黑烟曳在空中。他幻想自己坐在这车上,向芝加哥,向纽约,一路阅览雪峰和连嶂。去异国。去异国。去遥远的异国,永远离开平凡的中国。
安庆到葛底斯堡,两座塔隔了二十年。立在这座钢筋的了望塔上,立在二十年的这一边,他抚摸二十年前的自己,自己的头发,自己的幼稚,带着同情与责备。世界上最可爱最神秘最伟大的土地,是中国。踏不到的泥土是最香的泥土。远望岂能当归,岂能当归?就如此刻,山外是平原,平原之外是青山是青山。俄亥俄之外是印第安纳之外是艾奥瓦是内布拉斯加是内华达,乌鸦之西仍是乌鸦是归巢的乌鸦。唯他的归途是无涯是无涯是无涯。半世纪来,多少异乡人曾如此眺望?胡适之曾如此眺望。闻一多如此眺望。梁实秋如此眺望。五四以来,多少留学生曾如此眺望。珊瑚色渐渐吸入加稠的怅青,西南仍有一派依恋的余光。葛底斯堡的方向,灯火零零落落地亮起。值得怀念的小城啊,他想,百年前的战场,百年后的公园,葛底氏之堡,林肯的自由的殿堂。一列火车正迤迤逦逦驶过市中心。当日林肯便乘这种火车,来这里向阵亡将士致敬,且发表那篇演说。他预感得到,将来有人会怀念这里,在中国,怀念这一段水仙的日子,寂寞又自由的日子,在另一个战场,另一种战争之中。这次回去,他将再度加入他的同伴,他将投身历史滔滔的浊流,泳向旋涡啊大旋涡的中心。因为那也是一种内战。文化的内战,精神的内战,我与自己的决斗,为了攻打中国人偏见的巴士底狱,解放孔子后裔的想像力和创造的生命。也许他成功。也许他失败。但未来的历史将因之改向。
但在回去之前,他必须独自保持清醒的燃烧。就如那边的北极星,冷静地亮着,不失自己的方向,且为其他的光,守住一个定点。夜色部署得很快,顷刻间,恫吓已呈多面,从鼠灰到黝青到墨黑。但黑暗只有加强星的光芒。星的阵图部署得更快,在夜之上,在万籁之上之上,各种姓名的光,从殉道的红到先知的皎白透青,一一宣布自己的方位。他仰面向北,发现大熊和小熊开阔而灿明,如一面光之大纛,永不下半旗,那角度,比国内所见的高出许多。抓住冻手的栏杆,他感到金属上升的意志和不可动摇的力量。他感到,钢铁的生命,从他的掌心、脚心上升,如忠于温度的水银,逆流而且上升,达于他的四肢,他的心脏。在一个疯狂的豁然的顷刻,他幻觉自己与塔合为一体,立足在坚实的地面,探首于未知的空间,似欲窃听星的谜语,宇宙大脑微妙的运行。一霎间,他欲引吭长啸。但塔的沉默震慑住他。挺直的脊椎,纵横的筋骨,回旋梯的螺形回肠,挣扎时振起一种有秩序的超音乐。寂寞啊寂寞是一座透明的堡,冷冷地高,可以俯览一切,但离一切都那么遥远。鸟与风,太阳与霓虹,都从他架空的胸肋间飞逝,留下他,留下塔,留下塔和他,在超人的高纬气候里,留下一座骄傲的水晶牢,一座形而上的玻璃建筑,任他自国,自毁,自拯,或自卫。
1965年6月17日,葛底斯堡
一放暑假,一千八百个男孩和女孩,像一蓬金发妙鬘的蒲公英,一吹,就散了。于是这座黝青色的四层铁塔,完全属他一人所有。永远,它矗立在此,等待他每天一度的临幸,等待他攀登绝顶,阅读这不能算小的王国。日落时分,他立在塔顶,端端在寂天寞地的圆心。一时暮色匍匐,万籁在下,塔无语,王亦无语,唯钢铁的纪律贯透虚空。太阳的火球,向马里兰的地平下降。黄昏是一只薄弱的耳朵,频震于乌鸦的不谐和音。鸦声在西,在琥珀的火堆里裂开。西望是艳红的熔岩,自太阳炉中喷出,正淹没当日南军断肠之处,今日艾森豪的农庄。东望不背光,小圆丘上,北军森严的炮位,历历可数。华盛顿在南,白而直的是南下的州道。同一条公路,北驶三英里,便是葛底斯堡的市区了。这一切,这一圈连环不解的王国,完全属他一人所有。
葛底斯堡啊,葛底斯堡。他的目光抚玩着小城的轮廓。来这里半年,他已经熟悉每一条街,每一座有历史的建筑。哪哪,刺入晚空的白塔尖,是路德教堂。风雨打黑的是文学院的钟楼,雉堞上栖着咕咕的野鸽。再过去,是黑阶白柱的“老宿舍”,内战时,是北军骑兵秣马的营地。再过去,再过去该是他的七瓴古屋的绿顶了,虽然他的眼力已经不逮。就在那绿顶下,他度过寥落又忙碌的半年,读书、写诗,写长长的航空信,翻译公元前的古典文学,为了那些金鬘的、褐鬘的女弟子,那些洋水仙。那些洋水仙。纳巴科夫称美国的小女孩做nymphet。他班上的女孩应该是nymph,他想。就在那绿得不可能的绿顶下,那些洋水仙,那些牛奶灌溉的洋水仙,像一部翻译小说的女角那样,走进去,听他朗吟缠绵的《湘夫人》,壮烈的《国殇》。笑他太咸的鱼,太淡的黑莓子酒。他为她们都取了中国名字。金发是文葩。粟发是倪娃。金中带栗的是贾翠霞。她们一来,就翻出他的牙筷,每样东西都夹一下。最富侵略性的,是文葩,搜他的冰箱,戴他的雨帽,翻他的中文字典,皱起眉毛,寻找她仅识的半打象形文字。他戏呼她们为疯水仙,为希腊太妹,为bacchanals。他始终不能把她们看清楚,因为她们动得太快,晃得太厉害。因为碧睛转时,金发便跟着飘扬。她们来时,说话如吟咏,子音爽脆,母音婉柔。她们走后,公寓里犹晃动水仙的影子。他总想教她们停下来,让他仔细阅读那些瞳中的碧色,究竟碧到什么程度。
但塔下只有碧草萋萋。晚风起处,脚下的新枫翻动绿阴。这是深邃的暑假,水仙们都已散了,有的随多毛的牧神,有的,当真回欧洲去了。翠霞要嫁南方的羊蹄人。文葩去德国读日耳曼文学。终于都散了,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散了,正如当初,莫名其妙地聚拢来一样。偌大的一片校园,只留下几声知更,只留下,走不掉而又没人坐的靠背长椅,怔怔对着花后的木兰。牧神和水仙践过的芳草,青青如故。一觉醒来,怎么小城骤然老了三十岁?第一次,他发现,这里的居民多么龙钟,满街是警察、店员、保险商、收税吏、战场向导、面目模糊的游客。闷得发慌的下午,暑气炎炎,蟠一条火龙在林肯方场的顶空。车祸频起,救护车的警笛凄厉地宰割一条大街。
所以水仙们就这么散了。警笛代替了牧歌。羊蹄踹过的草地上,只留下一些烟蒂。临行前夕,神与兽,纷纷来叩门。“我们会惦记你的,”柯多丽说。“愿你能回来,再教我们。”倪娃拿走他的底片。一下午,羊蹄不断踢他的公寓。虬髯如盗的霍豪华,金发童颜的贝伯纳,邀他去十英里外,方丈城的一家德国餐馆,叫Hofbrauhaus的,去大嚼德国熏肉和香肠,豪饮荷兰啤酒。熏肉和香肠他并不特别喜欢,但饮起啤酒来,他不醉不止。笨重而有柄的史泰因大陶杯,满得欲溢的醇醪,浮面酵起一层滃滃的白沫,一口芳冽,顿时有一股豪气,自胃中冲起,饮者欲哭欲笑,欲拔剑击案而歌。唱机上回旋着德意志的梦,舒伯特的梦,舒曼的梦。绞人肚肠的一段小提琴,令他想起以前同听的那人,那人慵懒的鼻音。他非常想家。他尖锐地感到,离家已经很久,很远了。公寓里的那张双人床,那未经女性的柔软和浑圆祝福过的,荒凉如不毛的沙漠。那夜他是醉了。昏黄的新月下,他开车回去,险些撞在一株老榆树上。
第二天,他起得很迟。坐在参天的老橡阴下,任南风拂动鬓发,宿酲中,听了一下午琐琐屑屑细细碎碎申申诉诉说说的鸟声。声在茂叶深处渗出漱出。他从来没有听过那样好听的鸣禽,也从未像那天那么想家。他说不出是知更还是画眉。鸣者自鸣。聆者欢喜赞叹地聆听。他坐在重重叠叠浓浓浅浅的绿思绿想中。他相信自己的发上淌得下沁凉的绿液。城春。城夏。草木何深深。泰山耸着。黄河流着。……东方已有太多的伤心,又何必黯然,为几个希腊太妹?他想起,好久,好久没接触东方的温婉了。隐身的歌者仍在歌着。他幻想,自己在抚弄一只手,白得可以采莲的一只手。而且吟一首《念奴娇》向一只娇小的耳朵,乌发下的耳朵。隐身的歌者仍在歌着。
第三天,停车场上空落落的,全部走光了。因是废园。城是死城。他缓缓走下无人的林阴道,感到空前的疲倦。只有他不能离开,七月间,他将走得更远。他将北上纽约,循传说中惧内猎人的足迹,越过凯茨基山,向空阔的加拿大。但在那之前,他必须像一个白发的老兵,独守一片古战场。小城四郊的墓碑,多于铜像,铜像多于行人。至少墓碑的那一面很热闹,自虐而自嘲地,他想道。至少夜间比昼间热闹。夜间,猫眼的月为鬼魂唱一整个通宵,连窗上的雏菊也失眠了。电影院门首的广告画,虚张声势,探手欲攫迟归的行人。只有逃不掉的邮筒,患得患失地伫立在街角。子夜后的班车,警铃叮叮,大惊小怪地踹过市中心,小城的梦魇陷得更深。为何一切都透明得可怕?这里没有任何疆界。现在覆叠着将来。他走过神学院走过蜡像馆走过郁金香泣血的方场,但大半的时间,他走在梦里走在国内走在记忆的街上。这种完整而纯粹的寂寞,是享受,还是忍受,他无法分辨。冰箱充实的时候,他往往一星期不讲一句话。信箱空洞的时候,他似乎被整个世界所遗忘,且怀疑自己的存在。立在塔顶,立在钢铁架构的空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时人亦冷漠而疏远。何以西方茫茫,东方茫茫?寂寞是国,我是王,自嘲兼自慰,他想。她来后,她来后便是后,和我同御这水晶的江山。她来后,一定带她来塔顶,接受寂寞国臣民的欢呼,铜像和石碑的欢呼,接受两军铁炮冥冥的致敬,鼓角齐奏,鬼雄悲壮的军歌。她来后,一定要带她去那张公园椅上,告诉她,他如何坐在那椅上,读她的信。也要她去抚摸街角的那个信箱,那是他所有航空信的起站。她来后,一定要带她去那家德国餐馆,要她也尝尝,那种冰人肺腑的芳冽,他想。
她来后。她来后。她来后。他的生命似乎是一场永远的期待,期待一个奇迹,期待一个蜃楼变成一座俨然的大殿堂。期待是一种半清醒半疯狂的燃烧,使焦灼的灵魂幻觉自己生活在未来。灵魂,不可能的印第安雷鸟①,不可能柔驯地伏在此时此刻的掌中,它的翅膀更喜欢过去的风,将来的云。他钦羡英雄和探险家,羡他们能高度集中地孤注一掷地生活在此时此地,在血的速度呼吸的节奏,不必,像他那样,经常病态地生活在回忆和期待。生死决斗的武士,八肢互绞的情人,与山争高的探险家,他钦羡的是这些。他更钦羡阿拉伯的劳伦斯,同一只手,能陷城,也能写诗,能测量沙漠,也能探索灵魂,征服自己,且征服敌人。
但此刻,天上地下,只剩下他一人。鸦已栖定。落日已灭亡。剩下他,孤悬于回忆和期待之间,像伽利略的钟摆,向虚无的两端逃遁,而又永远不能逸去。剩下他,血液闲着,精液闲着,泪腺汗腺闲着,愤怒的呐喊闲着。剩下他,在恐惧之后回顾恐惧,危险之前预期危险。对于他,这是过渡时期,渡船在两个岸间飘摆。这是大征伐中,一段枕剑的小小假寐。因为他的战场,他的床,他的沙漠在中国,在中国,在日落的方向,他的敌人和情人和同伴同伴。自从他选择了笔,自从他选择了自己的武器,选择了蓝色的不是红色的血液,他很久没有享受过深邃安详如一座寺院的暑假,如他现在所享受的一样。暑假是时间的奢侈品,属于看云做梦的少年。他用单筒的记忆,回顾小时候的那些暑假,当夏季懒洋洋地长着,肥硕而迟钝如一只南瓜,而他,悠闲如一只蝉。那些椰荫下的,槐阴下的,黄桷树阴下的暑假。读童话,读神话,读天方夜谭的暑假。那时,母亲可靠如一株树,他是树上唯一的果子。那时,他有许多“重要”的同学,上课同桌,睡觉同床,记过时,同一张布告,诅咒时,以彼此的母亲为对象。那些暑假呢?那些母亲呢?那些重要的伙伴呢?
至少他的母亲已经死了,好客的伯母死了,在另一座塔下。那里,时间毫无意义地流着,空间寄托在宗教的租界。是处梵呗如呓,香火在神龛里伸着懒腰。他来自塔的国度。古老的上国已经陆沉,只留下那些塔,兀自顽强地自尊地零零落落地立着,像一个英雄部落的遗族。第二次大战后,他和母亲乘汽船,顺长江东下。船泊安庆。母与子同登佛寺的高塔①,俯瞰江面的密樯和城中的万户灰甍。塔高风烈。迷蒙的空间晕眩的空间在脚下,令他感觉塔尖晃动如巨桅,而他是一只鹰,一展翅一切云都得让路。十九岁的男孩,厌倦古国的破落与苍老。外国地理是他最喜欢的一门课。暑假的下午,半亩的黄桷树阴下,他会对着诱人的地图出神,怔怔望不厌意大利在地中海濯足,多龙的北欧欲噬丹麦,望不厌象牙海岸,尼罗河口,江湖满地的加拿大,岛屿满海的澳洲。从一本日历上,他看到一张风景照片,一列火车,盘旋而上庞伟的落基山,袅袅的黑烟曳在空中。他幻想自己坐在这车上,向芝加哥,向纽约,一路阅览雪峰和连嶂。去异国。去异国。去遥远的异国,永远离开平凡的中国。
安庆到葛底斯堡,两座塔隔了二十年。立在这座钢筋的了望塔上,立在二十年的这一边,他抚摸二十年前的自己,自己的头发,自己的幼稚,带着同情与责备。世界上最可爱最神秘最伟大的土地,是中国。踏不到的泥土是最香的泥土。远望岂能当归,岂能当归?就如此刻,山外是平原,平原之外是青山是青山。俄亥俄之外是印第安纳之外是艾奥瓦是内布拉斯加是内华达,乌鸦之西仍是乌鸦是归巢的乌鸦。唯他的归途是无涯是无涯是无涯。半世纪来,多少异乡人曾如此眺望?胡适之曾如此眺望。闻一多如此眺望。梁实秋如此眺望。五四以来,多少留学生曾如此眺望。珊瑚色渐渐吸入加稠的怅青,西南仍有一派依恋的余光。葛底斯堡的方向,灯火零零落落地亮起。值得怀念的小城啊,他想,百年前的战场,百年后的公园,葛底氏之堡,林肯的自由的殿堂。一列火车正迤迤逦逦驶过市中心。当日林肯便乘这种火车,来这里向阵亡将士致敬,且发表那篇演说。他预感得到,将来有人会怀念这里,在中国,怀念这一段水仙的日子,寂寞又自由的日子,在另一个战场,另一种战争之中。这次回去,他将再度加入他的同伴,他将投身历史滔滔的浊流,泳向旋涡啊大旋涡的中心。因为那也是一种内战。文化的内战,精神的内战,我与自己的决斗,为了攻打中国人偏见的巴士底狱,解放孔子后裔的想像力和创造的生命。也许他成功。也许他失败。但未来的历史将因之改向。
但在回去之前,他必须独自保持清醒的燃烧。就如那边的北极星,冷静地亮着,不失自己的方向,且为其他的光,守住一个定点。夜色部署得很快,顷刻间,恫吓已呈多面,从鼠灰到黝青到墨黑。但黑暗只有加强星的光芒。星的阵图部署得更快,在夜之上,在万籁之上之上,各种姓名的光,从殉道的红到先知的皎白透青,一一宣布自己的方位。他仰面向北,发现大熊和小熊开阔而灿明,如一面光之大纛,永不下半旗,那角度,比国内所见的高出许多。抓住冻手的栏杆,他感到金属上升的意志和不可动摇的力量。他感到,钢铁的生命,从他的掌心、脚心上升,如忠于温度的水银,逆流而且上升,达于他的四肢,他的心脏。在一个疯狂的豁然的顷刻,他幻觉自己与塔合为一体,立足在坚实的地面,探首于未知的空间,似欲窃听星的谜语,宇宙大脑微妙的运行。一霎间,他欲引吭长啸。但塔的沉默震慑住他。挺直的脊椎,纵横的筋骨,回旋梯的螺形回肠,挣扎时振起一种有秩序的超音乐。寂寞啊寂寞是一座透明的堡,冷冷地高,可以俯览一切,但离一切都那么遥远。鸟与风,太阳与霓虹,都从他架空的胸肋间飞逝,留下他,留下塔,留下塔和他,在超人的高纬气候里,留下一座骄傲的水晶牢,一座形而上的玻璃建筑,任他自国,自毁,自拯,或自卫。
1965年6月17日,葛底斯堡
《文星》编者附记:谢谢周弃子先生!本文在《文星》第九十三期发表的次日,他就写来这样一封信。
白帆老棣:
光中兄大作《塔》附注②的问题解决了。安庆江边的那座寺和塔叫迎江寺振风塔。这是我的朋友廖寿泉告诉我的,他是安徽望江县人,在安庆住了很久。他古典诗作得极好。
请写信便中告诉光中,并代致想念!
1965年7月2日
绛旓細姹:浣欏厜涓婂銆嬬殑鍘熸枃,璋㈣阿鍟~!銆婂銆嬧斺斾綑鍏変腑涓鏀炬殤鍋,涓鍗冨叓鐧句釜鐢峰鍜屽コ瀛,鍍忎竴钃噾鍙戝楝樼殑钂插叕鑻,涓鍚,灏辨暎浜嗐備簬鏄繖搴ч粷闈掕壊鐨勫洓灞傞搧濉,瀹屽叏灞炰粬涓浜烘墍鏈夈傛案杩,瀹冪煑绔嬪湪姝,绛夊緟浠栨瘡澶╀竴搴︾殑涓
绛旓細鎬讳箣锛屻婂銆浠ユ儏鎰熶负涓荤嚎锛屽彊浜嬨佺姸鐗╁啓鏅佹槑鐞嗙┛鎻掑叾涓紝鐒跺悗浣溾滀簲姝ヤ竴宀楋紝鍗佹涓妤尖濈殑鐐圭紑鍜屽畨鎺掞紝澶氱淇緸鍜屽瘜浜庤叮鍛崇殑缁嗚妭鑱旇鑰屾潵锛岀粶缁庝笉缁濓紝娓呴啋鐨勬剰璇嗗拰鏈﹁儳鐨勬綔鎰忚瘑浜ゆ浛鍑虹幇锛屾惁鍗冪浜庣瑪绔紝鎶氬洓娴蜂负涓鐬紝娴戠劧濡傛ⅵ澧冿紝濂旀祦姹规秾濡傛尝娑涳紝琛ㄧ幇浜浣欏厜涓鎵嶅姏瀵屽帤锛屽乏鍙抽㈡簮鐨勫ぇ瀹堕閲囥
绛旓細鎴戠殑蹇冩槸涓冨眰濉妾愪笂鎮寕鐨勯閾 鍙挍鍙挍鍜 姝よ捣褰艰惤 鏁插彥钁椾竴涓汉鐨勫悕瀛 鈥斺斺斾綘鐨勫涓婁篃鎰熷埌寰渿鍚? 杩欐槸瀵傞潤鐨勮剦鎼 鏃ュ涓嶅仠 浣犲惉瑙佷簡鍚 鍙挍鍙挍鍜? 杩欐伡浜虹殑闊宠皟绂佷笉鑳滅 闄ら潪鍙墍鏈夌殑椋庨兘鏀归亾 閾冮兘鎽樻帀 濉旈兘鎺ㄥ 鍙洜鎴戠殑蹇冩槸楂橀珮浣庝綆鐨勯閾 鍙挍鍙挍鍜 姝よ捣褰艰惤 鏁插彥钁椾竴涓汉鐨勫悕瀛 --- ...
绛旓細鏈熷緟鏄竴绉嶅崐娓呴啋鍗婄柉鐙傜殑鐕冪儳锛屼娇鐒︾伡鐨勭伒榄傚够瑙夎嚜宸辩敓娲诲湪鏈潵銆浣欏厜涓婂銆銆傛渶濂界殑鐢熸椿锛屾槸鎷夸竴鐢熺弽閲嶅湴瀵瑰緟涓涓汉鎴栦竴浠朵簨鍦ㄥ钩鍑$殑鏃ュ瓙閲岋紝娲诲嚭娣辨儏涓庣湡鎰忋備綑鍏変腑銆傝繖鏄槬澶╁憿锛岃繖鏄彂鍛嗙殑瀛h妭銆備綑鍏変腑銆備綘瑕佷細娴佹唱锛屼細瀛よ韩涓浜虹殑鍧愬湪榛戞殫閲岋紝鍚激鎰熺殑闊充箰銆備綘瑕佹噦寰楁璧忔偛鍓э紝鎮插墽锛岃兘涓板瘜浣...
绛旓細鎴戠殑琛绯讳腑鏈変竴鏉¢粍娌崇殑鏀祦 榛勬渤澶喎 闇瑕佹笚澶ч噺鐨勯厭绮 娴姩鍦ㄦ澂搴曠殑鏄垜鐨勫璋 鍠! 鍐嶆潵鏉珮姊 鎴戠殑鎬掍腑鏈夌嚙浜烘皬 娉腑鏈夊ぇ绂 鎴戠殑鑰充腑鏈夋犊楣跨殑榧撳0 浼犺绁栫埗灏勮惤浜嗕節鏀お闃 鏈変竴浣嶅彅鍙旂殑鍚嶅瓧鑳藉悡閫鍗曚簬 鍚娌℃湁? 鏉ヤ竴鐡堕珮绮 鍗冮噾瑁樺湪鎷嶉粍琛岀殑姗辩獥 鎸傝憲 褰撴帀浜旇姳椹彧鍓╀笅鍏宠妭鐐 鍐嶆病鏈...
绛旓細瀹冩槸闅忎綔鑰呯悊鎬х殑鎬濊冿紝涓嶆柇寰楀埌鎻愰珮鍜屽崌鍗庛傚瘋瀵炴棦鏄竴鍓傝嫤鑽紝涔熸槸鍏堢煡浠櫘搴︿紬鐢熺殑涓鍓傝壇鑽紝浣滆呯敱绌鸿櫄璧板悜鍐呭績绮剧涓栫晫鐨勫厖瀹烇紝骞舵媴褰撹捣鍏堢煡鑰呯殑璐d换锛屽ぇ鈥滄垜鈥濈粓浜庢垬鑳滀簡鈥滆嚜宸扁濓紝鈥滄垜鈥濆彲浠ュ湪鈥滈獎鍌茬殑姘存櫠鐗⑩濅腑鈥滀换浠栬嚜鍥氾紝鑷瘉锛岃嚜鎷紝鎴栬嚜鍗濄傝繖鏄垜瀵銆婂銆嬬殑涓鐭ュ崐瑙c
绛旓細绗竴锛屽彯鍜涘彯鍜涘挍 姝よ捣褰艰惤锛屾暡鍙╃潃涓涓汉鐨勫悕瀛 浣犵殑濉涓婁篃鎰熷彈鍒板井闇囦簡鍚楋紵绗簩锛1.浜鸿绉嬭壊涔嬩腑,鑴氫笅韪╃殑,鍙戜笂鎴寸殑,鑲╀笂浼兼湁鎰忔棤鎰忛鍧犵殑,鑾潪鏄庤壋鐨勯噾榛勪笌榛勯噾.鈥斺浣欏厜涓宸︽墜鐨勬帉绾广嬬涓夛紝2.閭i洩,鐧藉緱铏氳櫄骞诲够,鍐峰緱娓呮竻閱掗啋,閭h偂鐨戠殤涓嶇粷涓浠伴毦灏界殑姘斿娍,鍘嬪緱浜哄懠鍚稿洶闅,蹇冨瘨...
绛旓細浣欏厜涓鏈鐭殑璇楁湁 1銆併婃槦涔嬭懍銆嬫祬钃濊壊鐨勫婧㈣繘绐楁潵澶忔枱寰楀お婊★紝 钀ょ伀铏殑灏忓鐏仛鐫姊 姊﹁鍞愬姊﹁杩介愮殑杞荤綏灏忔墖锛 姊﹁鍙︿竴涓澶滀竴棰楁槦鐨勮懍绀 姊﹁涓闂厜鐨勪几寤朵笌娑堢伃锛 浠ュ強浣犵殑鎯婂懠鎴戠殑鍥為【鍜岀墖鍒荤殑鎰鐒舵棤璇 2銆併婇粍鏄忋嬪樿嫢榛勬槒鏄竴閬撳瘋瀵炵殑鍏筹紝 瑗块棬鍏冲悜鏅氶湠鐨 鍖嗗寙鐨勯瀺涓婂鍟婏紝涓轰綍...
绛旓細涓昏璇椾綔鏈夈婁埂鎰併嬨併婄櫧鐜夎嫤鐡溿嬨併婄瓑浣狅紝鍦ㄩ洦涓嬬瓑锛涜瘲闆嗘湁銆婄伒娌炽嬨併婄煶瀹や箣姝汇嬨銆婁綑鍏変腑璇楅夈嬬瓑锛涜瘲璁洪泦鏈銆婅瘲浜涔嬪銆嬨併婅瘲鐨勫垱浣滀笌閴磋祻銆嬬瓑銆傚叾涓婁埂鎰併嬩竴璇楋紝鍥犱负褰㈣薄鑰屾繁鍒绘姃鍙戜簡娓稿瓙娈峰垏鐨勬濅埂涔嬫儏骞跺瘜鏈夋椂浠f劅鑰屽彈鍒颁汉浠殑鍠滅埍娌宠禐璧忋備粬鐨勮瘲锛屽吋鏈変腑鍥藉彜鍏告枃瀛︿笌澶栧浗鐜颁唬鏂囧涔...
绛旓細璇楅泦锛氥婃瓕銆嬶紝閲庨锛1952銆傘婃闄靛皯骞淬嬶紝鏂囨槦锛1967銆傘婂ぉ鍥界殑澶滃競銆嬶紝涓夋皯锛1969銆傘婃暡鎵撲箰銆嬶紝钃濇槦璇楃ぞ锛1969銆傘婂湪鍐锋垬鐨勫勾浠c嬶紝钃濇槦璇楃ぞ锛1969銆傘婄櫧鐜夎嫤鐡溿嬶紝澶у湴锛1974銆傘婂ぉ鐙兼槦銆嬶紝娲寖锛1976銆傘婁笌姘告亽鎷旀渤銆嬶紝娲寖锛1979銆銆婁綑鍏変腑璇楅夛紙1949-1981锛夈嬶紝娲寖锛1981銆傘婇殧姘磋闊炽嬶紝娲寖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