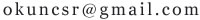枪口为什么不能对着自己
为什么即使是枪膛内没子弹,也不能把枪口对准自己人啊?
\u67aa\u53e3\u4e3a\u4ec0\u4e48\u4e0d\u80fd\u671d\u4e0b\uff1f
\u9632\u6b62\u67aa\u652f\u4e0d\u614e\u8d70\u706b\uff0c\u4e00\u662f\u76f4\u63a5\u4f24\u53ca\u81ea\u5df1\u7684\u8eab\u4f53\uff0c\u4e8c\u662f\u9632\u6b62\u5b50\u5f39\u5728\u5730\u9762\u786c\u7269\u4e0a\u5f39\u56de\u95f4\u63a5\u4f24\u53ca\u81ea\u5df1\u3002
\u8fd9\u662f\u9053\u5fb7\u95ee\u9898\u3002\u3002\u3002
\u56e0\u4e3a\u7528\u67aa\u6307\u7740\u4eba\u5c31\u662f\u4e00\u79cd\u5a01\u80c1\u2014\u2014\u4f1a\u4ee4\u4eba\u4ea7\u751f\u6050\u60e7\u611f\u2014\u2014\u542c\u8bf4\u8fc7\u6050\u60e7\u611f\u53ef\u4ee5\u6740\u6b7b\u4eba\u5417\uff1f\uff1f\u2014\u2014\u4e0d\u662f\u6240\u6709\u4eba\u90fd\u50cf\u8759\u8760\u4fa0\u524d\u4f201\u91cc\u97e6\u6069\u4e00\u6837\u3002\u3002\u3002
\u8fd8\u6709\uff0c\u5f53\u8fc7\u5175\u7684\u90fd\u77e5\u9053\uff0c\u62ff\u67aa\u6307\u7740\u4eba\uff0c\u5c24\u5176\u662f\u81ea\u5df1\u4eba\uff0c\u662f\u4e00\u79cd\u5f88\u574f\u5f88\u574f\u7684\u4e60\u60ef\u2014\u2014\u5373\u4f7f\u6ca1\u5b50\u5f39\uff0c\u88ab\u53d1\u73b0\u4e5f\u8981\u53d7\u5230\u5904\u7f5a\u3002\u3002\u3002
\u53cd\u6b63\u6211\u597d\u6015\u522b\u4eba\u62ff\u67aa\u6307\u7740\u6211\u3002\u3002\u3002\u3002\u3002
\u770b\u5f97\u8981\u5413\u6b7b\u6765\u7740\u3002\u3002\u3002\u3002\u3002
\u4e07\u4e00\u91cc\u9762\u8fd8\u6709\u5b50\u5f39\uff0c\u5bf9\u9762\u5f00\u73a9\u7b11\u7684\u4e00\u6263\u6273\u673a\u2014\u2014\u554a\uff01\uff01\uff01\uff01\uff01\uff01\uff01\uff01\uff01\uff01\uff01\uff01\uff01\uff01\uff01\uff01\u6211\u4e0d\u88ab\u6253\u6b7b\uff0c\u4e5f\u88ab\u5413\u6b7b\u3002\u3002\u3002\u3002\u3002
\uff08\u62b1\u6b49\uff0c\u6211\u597d\u6015\u75bc\u7684\uff09
华敬革走近公安局大门时,夜色已经相当稀薄,东天边依稀有天亮前的征兆。这时候大街上正是一段稀有的肃静冷清,再过个把钟头,就该有早起拜年的人影晃动了。华敬革在门口住了脚,目光在公安局的门牌上停留了一阵。门牌上的黑漆字在夜色里显得很暧昧。他深吸了口气,然后把烟头扔在地上。地很凉,烟头瑟缩了一下,翻了个身。刘敬革脚上的皮鞋迟疑了一下,然后就把它覆盖了。 华敬革走进大门。马路对过,一个鞭炮突如其来地炸响了,夜色打了个激灵,忽然淡了许多。 整个公安局办公楼只有一楼东首的窗口亮着灯,灯很孤独,发出的光亮就有些苍白。华敬革经常来,知道那是值班室。 推开值班室的门,一股汹涌的酒气朝华敬革扑过来。值班室里只有一个人,歪在沙发上,鼾声如雷。沙发前的茶几上躺着个空酒瓶,一些猪头肉花生米不成模样地散落着。华敬革寻到个椅子,坐了一会,冲睡觉的人喊:老魏。停了停又喊:老魏。这回声音提高了不少。被喊作老魏的人,均匀的呼噜被这喊声沉闷地撞了一下,很不情愿地打住了。老魏的嘴角先扯动了几下,然后就睁开了眼。 老华啊。老魏吧嗒了几下嘴,摸起桌上的水杯灌了几口,说:老华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值夜班?大年三十拈了个这阄,他妈的这手气。接着又半眯了眼说:到底是老哥们儿了,你这么早过来给哥哥拜年,够意思,比我们当官的强多了。对,呆会回去给全家捎个好儿,老少平安。老魏是公安局内保科的科长,因为工作上的关系,跟华敬革经常碰面,很熟。我杀人了。华敬革说。 大过年的,说什么不好,干吗开这玩笑,不吉利啊老华。老魏的眼皮很舒服地趴着,一动不动。喝高了?要不咱哥俩再整瓶二锅头透一下。 华敬革把五四式手枪搁在茶几上。手枪很小心,但它身子很重,落在玻璃茶几面上还是发出当的一声响。老魏睁开眼,看着灯光下乌油油的枪身,眼里涌出陌生和茫然。几秒钟之后,老魏肥大的身躯毫无预兆地从沙发上弹起。沙发冷丁一个趔趄,发出撕裂般的痛苦呻吟。老魏落地后,双脚踩着沙发的呻吟声,以非常难看的姿势迅捷无比地向门口斜去,踉踉跄跄夺门而出。枪冷酷地笑了一下。华敬革也苍白地笑了一下。枪真是个恐怖的东西,即使它保持沉默。他想。 昨天上午行长高明看见枪时也是一副的模样。其实那天华敬革是无意而为。昨天他跟运钞车押款回来的路上,心里老琢磨头天晚上办公室主任无意中透出的话。越琢磨越觉得窝囊,越琢磨越坐立不安,他决定找行长问个明白。心里头乱乱地,一下运钞车就直奔三楼行长办公室。 行长正跟一个客户谈工作,华敬革就只好站在走廊里等。小北风从走廊里打着旋儿晃荡,华敬革浑身的皮肤紧一下,再紧一下。几分钟后客户走了,华敬革敲开行长的门。行长豪华厚重的门很威严地给华敬革闪开了道缝隙,华敬革的身子从缝隙里挤进去。行长的身子深深地陷落在阔大的真皮转椅里,行长正专心致志地看报纸上的新闻。华敬革进门时,行长微微抬了一下头,又深深地陷落在报纸里。行长兀自笑了一下。什么事老华。高行长那什么,我想问件事,我听说、听说咱们单位今年有个下岗指标?啊?啊。听谁说的? 行长从报纸上探出头来,眼神里满是挥之不去的问号。问号从行长眼里挨挨挤挤地飘出来,像许多又细又长的环,一圈一圈往华敬革身上套去。啊,没,是听人瞎传传,乱听的。这个指标怎么确定? 行长收回了问号,指指老板台前面的椅子说,老华你坐。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了?本来呢,今天就年三十了,我想年后再跟你谈谈。对,你说的下岗指标,也确有此事。我们银行正处在这样一个向现代商业银行转轨的时代,这种事情在改革的进程中在所难免,可以说很正常。行长捏起一直烟给华敬革。说实话老华,这是块烫手的山芋,搁到哪个单位手上都难受,班子几个人研究好几次了,这事一直是个难题,相当难呐。你说论工作,论感情,哪个人行里都难以割舍。可是上级行十二道金牌催着,这是硬性指标,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难呐老华。行长肥白的手拍拍真皮转椅,转椅很沉稳地响了几下。这个位子你来坐坐,你就知道什么叫难了。华敬革点点头。这我理解。 行长感慨地说:到底是老同志,老党员,军转干部,觉悟就是不一样。你能有这样的认识,我心里就踏实了。老华,你是咱们行里公认的优秀职工,你看这样啊,咱们商量一下,你能不能发扬一下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神,在这个节骨眼上,为班子分忧解难,也算是帮我一把。这个下岗呢,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下岗,就是个流动岗,目的就是让员工对目前的机构人员改革有个清醒的认识。 华敬革摇摇头。这、这,恐怕不行。我老婆是下岗职工,我再下了岗,这个家靠、靠什么过? 一见领导或生人,华敬革的语言中枢神经就指挥不动嘴巴,两下里配合就常常出问题,说话就显得磕磕巴巴。 行长笑了:老华,行里不会亏你的。对你的付出和牺牲,班子心里有数,流动岗工资每月六百元,跟在岗的工资差额是七百元,这个好办。你不是兼着咱们单位的电工吗,原来是义务工,以后行内每月补贴你八百元,收入实际是明降暗升的。怎么样?考虑考虑。 华敬革肚里有句话窜到了嗓子眼,硬硬地想冲出来,喉头的两扇门却关得很紧,那句话在华敬革肚子里东一头西一头撞了几下,又极其不甘地退了回去。华敬革想笑笑,缓解一下情绪。可笑声从嗓子里挤出来时,水分都挤跑了,声音很干巴,还冷飕飕的。华敬革说:我,我想不通。你不能单拣软柿子捏。 行长略偏了头盯着华敬革,行长的耳朵像架斜支着的网,把华敬革每个字都很仔细地捕捉住了。老华,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仅供参考,没有谁强迫你。不过你这态度可不对,怎么叫捏软柿子?谁是硬柿子?看问题不要偏激,不能无中生有想当然嘛。这态度对自己是无益的。在这件事上,行里是有政策有办法的,我哪,不过是跟你做个私下交流而已。 华敬革抬起头看行长。行长的目光和华敬革的目光在空中相遇了。行长的眼光很硬,并且弹力十足,华敬革的眼光被撞了一下,倏地缩回来了,有点隐隐地痛。 华敬革脸白了一白,说:对不起,我,我不是这意思。枯坐了几分钟,想说点什么,满肚子搜索,却找不到合适的话,就有点手足无措和坐立不安,就起身告辞。他犹豫了一下,说:只要政策公平公正,就是砸到我头上,我也认了。 转身要走时,华敬革无意中扫了行长一眼,却意外地看见行长脸上的表情相当古怪,行长面部肌肉发僵,眼睛发直,脸上保养得很好的红润正一点点消褪,整个表情很瓷。他一时摸不着头脑。楞怔了一阵,下意识地沿着行长的目光看,就看到了自己腰上枪套里那把睡着的手枪。 只觉得脑子里嗡的一声响,华敬革脸也白了,身子一点点僵硬,他叉着两手,感觉很多余,不知道放哪好。 行长,不是,我这枪是刚才押款回来,忘记入库了。我,我绝对不是故意带到你办公室来的。绝对不是。 行长瘪了一下嘴,盯着华敬革的枪,似乎没注意华敬革说什么。过了一阵,行长似乎放松了,他想端起架子说两句威严些的话,脑子却很木,抓不住一个字,于是他抬起手,指了指门的方向。行长的胳膊有些虚脱,已经没有了伸直一些的力气,这使得他前指的姿势很涣散,甚至,有些丑陋。行长一定意识到了,他缩了缩身子,做了一些努力,胳膊又前伸了一下,可很快他明白这点努力是徒劳的。 华敬革脑子也很木,他没想到以这样的结局结束这次跟行长的会面。他脚步沉重地走出行长办公室。 走到家,见老婆正数落儿子:说你多少次了,也不长记性!那个小牲口,咱惹不起还躲不起?满院的孩子,你不会找别人玩去? 儿子脸上有两块青紫,眉头有擦痕,泛着血晕色。华敬革说:孙大坚又欺负你了?你说真是,都十来岁的孩子了,该懂事了,这孙勇怎么也不管管孩子?孙勇是华敬革同事,跟华敬革住一排房。孙勇老婆是东北人,表面清爽秀气,内里却是地道的东北虎。儿子孙大坚把虎的基因继承了,打小就厉害,揍华敬革的儿子比喝面条还平常,尽管儿子比孙大坚高出半个脑袋。华敬革的老婆给儿子上了点药水,就愤愤地说:我找他们理论理论去。 算了算了。华敬革摆摆手,那个夜叉,咱别惹她吧。上几次的事你还不记得,吃亏的不都是咱。再说,她脸一抹一百不论,香臭不分,咱哪陪得起她丢这个人。 华敬革老婆脸上就罩了层灰黑。上次她因为儿子被欺负,孙家那边一声不响,她拉孩子去找孙勇。孙勇老婆刚好不在家,孙勇训斥了儿子几句,又买了鸡蛋水果到了华敬革这边道歉。下午孙勇老婆冲进华敬革家,摔了水果砸了鸡蛋,把华敬革家的墙弄成了现代派大师的绘画。然后跳上了华敬革的小房,赤裸了上半身,把华敬革长眠地下的先人几乎无一遗漏地翻晒出来,骂了个狗血喷头。 华敬革老婆终于没敢出门,回身叹了口气:马善人骑人善人欺,你说咱们摊上这么个灾星,往后的日子咋过,就该叫人骑脖子上拉屎咋地? 坐了一阵,华敬革对老婆说:今晚我要值班。明天白天休班,要不你先带军军回老家?老婆说:你看这满脸花,爷爷奶奶问起怎么说?本该一家老少欢天喜地的日子,弄了一肚子气,你说这叫过年? 天快黑时,华敬革到超市里花一千元买了个购物卡。小县城过年,不可避免地沾染了乡村的气息,走在街上,放爆竹的声响此起彼伏,单位门口挂起了灯笼插上了彩旗,不少人忙活着贴春联,营造出一个凡俗而真切的年味来。走到一个拐角处,华敬革驻了脚,听了一会爆竹声响,觉得很遥远,进而觉得年味也很远,觉得这个年跟自己好像没任何关联。走到行长家门口,华敬革犹豫了一下,心里打怵,就想往回返,手和脚这时却背离了思想,脚迟迟疑疑地往前挪动了几步,手则犹犹豫豫地按响了门前那个正冷眼相觑的门铃。 门铃耐住性子响了几下。就在华敬革几乎丧失继续坚持勇气的瞬间,豪华防盗门上叭地弹起个小窗口,窗口后面贴上一只眼睛。眼睛里很快蒙上了一层霜雪,霜雪向华敬革飘洒过来,华敬革的浑身皮肤紧了一紧。 高行长在家吗,我……有点事跟他谈谈。华敬革说。他的话没说完,小窗口叭地关闭了,很锋利地切断了华敬革的话,华敬革的声音撞到防盗门上,又空洞地弹回来,落到冰凉的水泥地上,碎了。 从行长家出来,华敬革没往家拐,直接去了金库的值班室。转业到银行八年来,华敬革几乎每天都是第一个接班,第一个到岗,今天却迟到了。走进值班室,发现值白班的小陈小张已经走了,今晚跟他同班的小崔还没到,倒是保卫科长老曹正坐沙发上抽烟。老华。老曹摆摆手,示意华敬革坐下。老曹递给华敬革一支烟,自己也摸出一支,点上。 老华啊。老曹的声音有些低沉。咱俩搭伙计这么久,我了解你,踏实,卖力,能吃屈,不好言语,可这回,你处理事的方法太过激了些。要冷静啊,头脑发热只会把事弄糟。咱们都是转业干部,部队上摔打了这些年,你应该明白。 华敬革摇头。上午完全是误会。你说我怎么会有那种想法?怎么会拿枪威胁行长?绝对不会。我是昨天听到些传言,满脑子净装着这事了,押款回来忘了先把枪交接入柜。要说我操作违章,这责任我承担,其他的想法,我是绝对没有的。你该知道。老曹说:这话我信。你做事沉稳,我也觉得你不会如此莽撞。 老曹又说:一会儿要开党总支会,通知让我列席,估计是研究你今天这个事,我会把意思给他们亮明。 老曹走后,华敬革坐了半小时,小崔还没到。值班室的便池堵塞了,华敬革这会没心思清理,他上了三楼的厕所。出来的时候,他看见了小会议室门缝泻露的灯光。窄窄的一线光,很吝啬。华敬革看了一会儿,门忽然就开了,老曹和副行长姜斌一前一后走出来。华敬革就闪到楼梯口的暗影里。姜行长,这样处理我觉得对老华有点过。走到厕所门口时,老曹对姜斌说。姜斌说,你还不知道他脾气吗,老华人太老实。 姜斌说,要说这次调离保卫岗位,也没啥大不了的,我看他还有后手棋。不是正为一个下岗指标犯愁吗,这回材料往上一报,老华是没有悬念的了。姜斌顿了顿说,哪座庙里没有屈死鬼啊。 华敬革回到值班室时,小崔已经到了。小崔拎来两瓶酒,一只烧鸡。华哥,过年了,值班室这熊地方连个电视也没有,咱俩别干耗着,喝两杯。小崔一面拆分烧鸡一面嘟囔。 华敬革没什么量,喝了几口就觉得上头。华哥你真是个大好人,我们几个说闲话时常讲,像华哥这样的人真是太少了。小崔说。可是您看这年月,不兴好人过了。我们都是小兵出身,您可是正经转业干部,这些年在单位工作没少干,力没少出,大伙公认的老黄牛,可你看现在,华哥你得到什么了?要我说,你这年龄了,甭下死劲干了,悠着点,怎么高兴怎么来,怎么舒服怎么来。你说哪,华哥。 电话粘粘糊糊地响了,小崔奔过去。小崔说话声音甜腻绵软,话筒像患上软骨病似的摊在小崔的手掌跟下巴之间,很受用的模样。小崔的女朋友数量比较可观,成分也比较复杂,小崔像尾兴致勃勃的鱼,游走嬉戏在茂盛的水草之间乐此不疲。因为经常通过多种方式替小崔遮掩,华敬革跟其中几个女孩甚至已经很熟悉。 华敬革喝掉一杯,再一杯。头两杯晕的感觉很重,再喝几杯后好像冲淡了些,思维一下活跃起来,像一群刚离水的鱼虾。他有些兴奋。原来喝酒也有几个层面的感觉,需要过几道门坎的,原来自己就没发现,仅仅在头道门外徘徊,华敬革感觉以前喝酒真是亏了。 小崔兴冲冲地出去时,华敬革冲他摇手招呼了一下,不过基本没往脑子里进什么信息。他那会儿正开始喝第二瓶酒,他开始体会到一种感觉:飘。整个身体变成了一片云,悬在高高的半空,阳光给云朵洒上了一层迷蒙的金色,飘飘悠悠,不知所终地在半空中游荡,失去了方向和重量。 飘这个字出自他的一个战友,在当时纪律严明的军队,他却令人难以置信地染上了毒瘾,就在被部队发现,强令戒毒的前几天,他跟华敬革谈到吸毒的感受时,就用了这个字。 当时华敬革没怎么往心里去,只是不久他就对这个字有了体会。1979年华敬革随东线部队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他是通讯班班长,说是上前线,其实并不在枪林弹雨的第一线。那天晚上华敬革值班时,前方的通讯设施突然出现故障,他跟另一个线路员冒雨走了几十里山路赶了去,等故障排除困意朦胧往回赶时,因天黑路滑,失足滚入山沟,大腿上挂了道口子,血咕嘟咕嘟地冒,线路员死命摁都摁不住。那一阵华敬革就有了飘的感觉。觉得身子一点点变轻,酥软,透明,松松散散,每块骨头里都充满了向上飘升的气体。在被抬上担架时,华敬革已经说不出话来,在失去记忆以前,他脑子里忽然闪过了战友的话,他迷迷糊糊地想,这是吸毒以后那种飘吗。当然这个念头只是闪了一闪,他试图往深处辨认一下时,就没有了意识。 这样想着的时候,华敬革就看见了右手上的枪,和左手里的几颗子弹,枪和子弹都慵倦地摊在他手掌上,睡意朦胧。华敬革感觉很恍惚。这把枪不是在枪柜里存放着的吗,它怎么就跑到了自己手上?还有这子弹,那不是有次单位组织打靶时,自己偷偷藏下的几颗吗,它本来在家里书橱最底层的小抽屉内隐居着啊。刚才到家里去过吗?好像是。对,刚才出去吐过一次酒,经过家门口时,忽然想起要拿点东西,那么,就是去寻找这几颗子弹了? 华敬革把枪口翻转过来,对着自己。这把枪尽管已经有些苍老了,枪管前半部和手柄都有些斑驳,但保养得还比较好,依然保持着一把枪应有的威严。在日光灯下,枪口边缘反射的几丝光有些苍白冰冷。从枪洞口往里看,深不可测,里面是浓得化不开的黑暗,好像世界上所有的夜色都浓缩到了洞中。洞口很小,却透着无边的森森寒气,叫人不寒而栗,就像只无形的大手,一下就把人给抓住了。华敬革和枪洞对视了很久,心里慢慢地空旷起来,像是走进了一片荒漠,有种极度的虚空。虚空里慢慢就有了一点活物,先是几个小黑点,若有若无地蠕动,有些飘渺,后来那点活物不知怎地就突兀膨胀起来,生长的速度相当惊人,很快就占领了所有的空间,把他意识里另外的东西挤压成了一张薄纸。 华敬革从后门走出来,向三楼看去,办公室的灯还亮着,灯光从窗帘缝里挤出来,冷冷地乜斜着眼瞧华敬革。不断有零星的鞭炮声炸响,还有电视里春节晚会的欢快乐曲,都很远,若有若无的很飘忽。华敬革在办公楼下走过来又走过去,他想停下来,双脚却好像拒绝指挥,执拗地前后摆动,直到一声突如其来的狗叫声打断了他。他扭脸望去,看见一团壮硕的黑影已扑到眼前,一双眼高深莫测地望着自己。华敬革没有闪避,狗有点意外,就住了脚望着华敬革。华敬革和狗对望了一阵,然后想继续走自己的路,狗却一跃而起挡在前面,站到距华敬革两步远的地方,也不吠叫,就那么阴阴地望着他。华敬革辗转躲避了几次,总也闪不掉,四下望了望,想就近找个树枝砖瓦什么的对付狗,这么一想才发觉手上拎着枪。狗日的。华敬革咕哝了一句,把子弹上了膛。枪本来睡着,这时忽然就惊动了,凛冽的空气让它一点点清醒过来。枪打了个长长的呵欠,犹犹豫豫地对准了狗的脑袋。狗忽然很有底气地狂吠了两声,华敬革就看见有人立在了狗的身后。 立在狗身后的是孙勇老婆。华敬革认出来了,枪也认出来了。枪瑟缩了一下,慢慢垂下了头。 华敬革转身欲走,一声冷笑就向华敬革射过来。打啊,你他妈的不是想打姑奶奶的狗吗。有种跟姑奶奶真刀真枪的来,哼,就你那点出息,也就是背后跟个狗叫叫劲儿呗。 华敬革就住了脚,回头看孙勇的老婆。孙勇老婆说,拿着枪你就鸡巴硬了?有种你给姑奶奶来一枪!狗也跟着狂叫几声,冷眼瞧着华敬革手上的枪,一副盛气凌人的模样。枪吸了口冷气,忽然重新抬起了身子,对准了孙勇的老婆。孙勇老婆向前跨了一步。华敬革向后退了一步。 不敢打你就一孙子!孙勇老婆的手指住华敬革的鼻子,说:姑奶奶借你俩胆儿!个熊包模样,裤裆里的家伙都硬不起来,你也算个男人? 枪很冲动地响了。孙勇的老婆伸出的胳膊还没有收回,就像截木头一样向前倒下了。华敬革哆嗦了一下,看看孙勇的老婆,看看手上的枪,脑子里一片空白。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他想,我本没想开枪,为什么它就那么干脆而决绝的响了?我没想杀人啊,那么,是不是我的身体背叛了我的思想?零落的鞭炮声里,华敬革陷入了无边的虚空和寂寥。他抬头望了望行长办公室苍白的灯光,长叹一声,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 也许过不了几天,我就要被押赴刑场了,一审结果下来后,我没有提出上诉。我心里很平静,就是这几天我老做梦。原来我以为我会做打死孙勇老婆的梦,可是没有,一次也没有。我总是梦见那只枪,深不见底黑洞洞的枪口总是对着我,每次我都会在梦中惊醒,汗流浃背,每次醒来我都百思不得其解。 我叫华敬革,原来我不是这个名字,原来的名字是我爷爷给取的。我爷爷念过私塾,是村里最有学问的先生,村里孩子取名都找他。我的辈分是敬,爷爷说,君子勤以修身,俭以养德,所以就给我取名叫敬修。这名字却给我带来了麻烦。小学五年级时正赶上斗资批修,我的名字成了同学攻击的靶子,大家都说,大家都在批修,你还敬修,你是什么立场?尽管是小孩子斗口,没有上纲上线,我觉得也非常别扭,哭着闹着把名字改了。 小时候我想做个好孩子,长大了我想做个好公民。生活是个舞台,我不想被舞台拒绝,不想作旁观者,我想尽心尽力演好自己的角色,我觉得自己一直很踏实很努力,可我不知道为什么,生活好像从来没有对我阳光灿烂过。我1976年应征入伍,一年后成了师里的技术标兵,应该是提干的首选,到节骨眼上却被人给顶了;1979年对越反击战我第一批报名请战,立了个二等功,下战场后跟我同等条件的都被保送上了军校,独有我又分到了连队,我上军校是后来凭那点文化根底自己考上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部队裁员时,原本可以留在部队,我积极响应号召转业到地方,正营职的干部到了银行却成了一般办事员;到银行后我勤勤恳恳,处处谨慎,处处小心,没请过一天假,没休过一天公休,本职的工作抢着干,还发挥自己懂线路的特长,给单位兼了8年的义务电工,不争名利,不要待遇,以至别人给了我个“大傻”的绰号,到最后却成了下岗的人选!我不知道到底是哪出问题了,是别人,是我自己,还是我所处的生活和时代?我想了很多答案,不过哪个都不敢肯定。 那还是我刚转业回来,老婆还在乡下,行内分给我一间房,跟孙勇搭邻居。那天孙勇请我到到他家吃饭,孙勇酒量大,我喝酒不行,但人家孙勇盛情难却,一杯一杯的干,那天都喝多了。饭桌上孙勇老婆不断拿话撩我,我晕晕乎乎的,没怎么往心里去,不是都高了吗。从孙勇家出来时我手脚已经不好使,只能摸着墙根儿走。孙勇老婆很殷勤地搀我到家,我屁股刚挨床,谁知这女人三下五除二就把自己扒光了,接着就往我身上贴。我哪见过这阵仗啊,再说孙勇就隔墙邻居,你说这女人咋会恁大胆,他就不怕有个风吹草动吗。我那天那个狼狈,一面抓着腰带抵挡招架,酒就吓醒了一半。孙勇老婆见我这德行,冷笑着往我档里摸了一把,就住了手,然后一口痰射到我脸上说:就这熊样,你也算个男人?! 其实我很正常,各项功能都没问题,不过我从心里怵这个女人了。打那以后,只要跟孙勇老婆照面,我就很不自然,好像欠了她似的不好意思。女人倒是心气壮的很,常常不错眼珠的看我,要不就甩给我一脸的鄙夷,再不就指桑骂槐地寻事。再往后,儿子就成了我的替罪羊。我从小就不会跟人斗口,也不善言辞,与人为善、吃亏是福一直是我做人的准则。那年我买了副装裱精致的对联,内容是句古训:让三分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每遇到不平事,我就强迫自己默诵对联,读着读着火气就减了,心气就平了。不过回过头来看看,我的克制和忍让、温和与善良并没有给我带来风平浪静和海阔天空,我的生活空间被别人一寸一寸掠夺和挤压,别人一步步进逼,我一步步倒退,正如老婆经常唠叨的那样,我活得很窝囊。真的是窝囊。也许这种压抑的生活日积月累,终于把我逼到了爆发的临界点。那天我真想杀死高明行长的,只是多年的思维惯性一直阻碍着我的行动,我始终没有迈出最后一步的决心。说真的,要不是半道上杀出个孙勇老婆,或许那天晚上还会风平浪静一如既往。 我感觉对不住的,除了老爹老娘、老婆孩子,还有个人就是孙勇。孙勇是个实诚人,跟我还算合得来,只是他摊上那样的女人,也是难为他了,也许他活得比我还要压抑,要不为啥早早就失去了男人的基本功能了呢,老婆的死对他是不是一种解脱呢。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本来想自己送自己上路的,后来我想,总归都是一死,我不能死得不明不白,我死了,老婆孩子还要生活,我的死对他们就是一种致命的打击了,我不能再让他们活在别人的猜忌和议论里,我要通过法律的审判程序还给他们一个清白。 我就要上路了。在我们这个生存空间之外,有没有一个叫天堂的地方呢?咳,没有最好,要不万一在那里还有相互倾轧、蔑视、妒忌、自私呢,还是化成一撮灰最好,什么都没有了,我就彻底轻松了。我活得真是太累了。
涓轰粈涔瑕佷弗绂佸皢楂樺帇绌烘皵鍑烘皵鍙瀵瑰噯鑷繁鎴栦粬浜?
绛旓細涓ョ灏嗛珮鍘嬬┖姘斿嚭姘斿彛瀵瑰噯鑷繁鎴栦粬浜烘槸浠庡畨鍏ㄦ柟闈㈣冭檻鐨勶紝闃叉鍥犲帇鍔涜繃楂樺柗鍑洪珮鍘嬮犳垚浼ゅ鐨勩
鎰忓ぇ鍒╁皠鍑诲啝鍐涙剰澶栬蛋鐏嚮涓鑷繁韬骸,濡備綍閬垮厤杩欑鎰忓浜嬫晠鐨勫彂鐢...
绛旓細鏋敮鏈潵灏辨槸鍗遍櫓鍝侊紝璇ョ敺瀛愬湪寮叞鎹″瓙寮圭殑鏃跺欙紝涓嶅皬蹇冨嚮涓簡鑷繁鐨勮吂閮紝鎵浠ュ鑷存偛鍓х殑鍙戠敓锛屾兂瑕侀伩鍏嶈繖绉嶆儏鍐碉紝閭d箞瑕佹纭娇鐢ㄦ灙鏀紝涓嶈鎶婃灙鍙e鍑嗚嚜宸卞拰浠栦汉銆傝繖璧蜂簨鏁呯殑鍙戠敓涓昏鏄洜涓轰粬浠湪鎰忓ぇ鍒╂瘮钀ㄩ檮杩戣繘琛岀嫨鐚庣殑娲诲姩锛岃鐢峰瓙璺熶粬浠殑鍚屼即鍦ㄨ繖涓湴鏂瑰鎵剧寧鐗╄繘琛屽皠鍑伙紝鑰屽綋鏃跺洜涓洪渶瑕佽ˉ鍏呭瓙寮癸紝浠栧氨...
鏋彛涓轰粈涔堜笉鑳藉鐫鑷繁
绛旓細鐪嬮棶棰樹笉瑕佸亸婵,涓嶈兘鏃犱腑鐢熸湁鎯冲綋鐒跺槢銆傝繖鎬佸害瀵硅嚜宸辨槸鏃犵泭鐨銆傚湪杩欎欢浜嬩笂,琛岄噷鏄湁鏀跨瓥鏈夊姙娉曠殑,鎴戝摢,涓嶈繃鏄窡浣犲仛涓涓嬩氦娴佽屽凡銆 鍗庢暚闈╂姮璧峰ご鐪嬭闀裤傝闀跨殑鐩厜鍜屽崕鏁潻鐨勭洰鍏夊湪绌轰腑鐩搁亣浜嗐傝闀跨殑鐪煎厜寰堢‖,骞朵笖寮瑰姏鍗佽冻,鍗庢暚闈╃殑鐪煎厜琚挒浜嗕竴涓,鍊忓湴缂╁洖鏉ヤ簡,鏈夌偣闅愰殣鍦扮棝銆 鍗庢暚闈╄劯鐧戒簡涓鐧,...
涓轰粈涔鍗充娇鏄灙鑶涘唴娌″瓙寮,涔涓嶈兘鎶鏋彛瀵瑰噯鑷繁浜哄晩?
绛旓細鍥犱负鐢ㄦ灙鎸囩潃浜哄氨鏄竴绉嶅▉鑳佲斺斾細浠や汉浜х敓鎭愭儳鎰熲斺斿惉璇磋繃鎭愭儳鎰熷彲浠ユ潃姝讳汉鍚楋紵锛熲斺涓鏄墍鏈変汉閮藉儚铦欒潬渚犲墠浼1閲岄煢鎭╀竴鏍枫傘傘傝繕鏈夛紝褰撹繃鍏电殑閮界煡閬擄紝鎷挎灙鎸囩潃浜猴紝灏ゅ叾鏄鑷繁浜猴紝鏄竴绉嶅緢鍧忓緢鍧忕殑涔犳儻鈥斺斿嵆浣挎病瀛愬脊锛岃鍙戠幇涔熻鍙楀埌澶勭綒銆傘傘傚弽姝f垜濂芥曞埆浜烘嬁鏋寚鐫鎴戙傘傘傜湅寰楄鍚撴鏉...
銆婇暱娲ユ箹銆嬮噷闈,鏈鍊煎緱娣辨濈殑璇,鏄摢涓鍙?
绛旓細杩欏彞璇濆叾瀹炰篃浠h〃浜嗘垜鏂圭殑绔嬪満銆傝繖涓嶆槸渚电暐鎬х殑鎴樹簤锛岃屾槸涓鍦轰繚瀹跺崼鍥界殑鎴樹簤銆傛垜浠彧鎯冲畧鎶よ嚜宸辩殑鍦熷湴锛屽畧鎶や笌浜蹭汉鐨勫畨瀹氱敓娲汇傛垜浠殑鍐涢槦涓嶆槸渚电暐鑰咃紝鎴戜滑鍐涢槦鏄湁浜烘х殑銆傛垜浠粠涓嶅ぇ鎼炲睜鏉銆傝繕璁板緱褰辩墖寮澶村悧锛熷湴鏂逛负浜嗚拷瀵昏儨鍒╃殑蹇劅锛屽氨楠戠潃椋炴満鍚戝案浣撶柉鐙傛壂灏勩傛垜浠殑鍐涢槦鍦ㄨ儨鍒╁悗鐨勫杽鑹笌涔嬪舰鎴...
浣犲姹ゆ櫘妫綋鍒濇妸鏋彛瀵瑰噯鑷繁鎴樺弸鐨勫仛娉曟庝箞鐪?涓轰粈涔?绛旀_鐧惧害鐭...
绛旓細鍦ㄤ娇鐢ㄦ灙鏀殑鏃跺欙紝瑕佹眰鍋氬埌涓嶅緱鏋彛瀵逛汉锛岃繖鏄负浜嗛槻姝㈡灙璧扮伀浼や汉銆傝繖鏍风殑浜嬩欢鍑轰簡寰堝锛屼粠涔犳儻鍋氳捣锛屼娇鍐涗汉鍏绘垚鏋彛涓嶅浜虹殑涔犳儻銆傚彧鑳藉鏁屼汉杩涜灏勫嚮銆鏋彛瀵瑰噯鎴樺弸寮鐜╃瑧锛屾槸涓ラ噸杩濆弽鏋敮瀹夊叏瑙勫畾锛岃鏍规嵁鏈汉鐨勮璇嗘佸害杩涜澶勭悊锛屽鏋滄病鏈夐犳垚鍚庢灉锛屼互鎵硅瘎鏁欒偛涓轰富锛屼篃鍙湪鍐涗汉澶т細涓婁綔妫鏌ワ紝浠ユ暀鑲叉湰浜...
鎾鏋彛涓浠涔鎰忔?
绛旓細鐩存帴鎰忔濇槸鑷繁鎾炲湪鏋彛涓婁簡銆傝繖涓剰鎬濆お澶氫簡锛屾瘮濡傝鏈杩戞濂戒弗鏌ラ厭椹撅紝浣犲枬閰掑紑杞︼紝琚煡浜嗭紝杩樻姉娉曪紝杩欏氨鍙挒鏋彛涓婁簡銆
鑷繁寰鏋彛涓婃挒鎹㈠彞璇存硶
绛旓細NO浣淣O姝汇傚線鏋彛涓婃挒鏄寚鏄庢槑寰堝嵄闄╋紝浣嗚繕鏄富鍔ㄥ噾涓婂幓锛岃嚜鎵惧嵄闄┿備篃灏辨槸NO浣淣O姝汇傚ぇ澶氬舰瀹逛竴涓緢鍗遍櫓鐨勫湴鏂癸紝浣嗘槸鏌愪簺浜烘槑鏄庣煡閬擄紝鍗寸‖鏄噾杩囧幓锛岃繘鍏ュ嵄闄╁鍦帮紝鏆楁寚缂哄績鐪兼垨鑰呭偦鍌汇備汉寰鏋彛鎾烇紝缁濅笉鏄佹锛岃屾槸瀵逛簬鑷繁鐨勮嚜淇°
鎬庝箞鍥炲鏈嬪弸,閭d綘灏涓嶈鎾鏋彛?
绛旓細鏈嬪弸璇翠綘灏涓嶈鎾鏋彛浜嗭紝寰堟樉鐒舵湅鍙嬪叧蹇冪殑鏄綘鐨勫畨鍗憋紝浠ュ強浣犵幇鍦ㄦ墍澶勭殑澶勫銆傛墍浠ワ紝浣犺繖涓椂鍊欏彲浠ュ洖澶嶆湅鍙嬭锛屼互鍚庢垜浼氭敞鎰忕殑锛屾灙鎵撳嚭澶撮笩锛屾垜涓嶄細褰撻偅涓笩鐨勩
鎴愬勾浜虹敤鏋嚜鏉鏃,鍑犱箮閮戒細鐬勫噯鑷繁鐨勮剳琚 涓轰粈涔
绛旓細浣嗘槸瀹冧篃鏈夌己鐐癸紝鍥犱负寮逛父鍒濋熼珮锛岃川閲忓ソ锛屽洜姝ゅ懡涓箣鍚庡線寰鏄撲簬璐氾紝鍒涘彛鍏夋粦锛屼竴鎵撲袱涓溂锛瀵鍛ㄨ竟缁勭粐鐮村潖涓澶э紝鍦ㄦ潃浼ゅ姏涓婁笉濡備腑鍥界殑涓寮忋傜櫧鍒冩垬涓紝杩欎釜缂虹偣鏇翠负绐佸嚭锛屽洜涓虹櫧鍒冩垬涓弻鏂逛汉鍛樺線寰浜掔浉閲嶅彔锛屼娇鐢ㄤ笁鍏紡锛岃疮閫氬悗缁忓父鏉浼鑷繁浜猴紝鑰屼笖锛岀敱浜庤疮閫氬悗寮逛父閫熷害闄嶄綆锛屼簩娆″嚮涓悗寮逛父浼氬舰鎴愮炕婊...
扩展阅读:
上甘岭战役用身体堵住枪口 ...
用手指堵住枪口会怎样 ...
枪不能对着自己人 ...
梦到坏人枪口对着自己 ...
中国为什么禁枪在害怕什么 ...
《别把枪口对着我电竞》 ...
枪口对着摄影师的图片 ...
手指堵住枪口会炸膛吗 ...
枪口永远不要对着自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