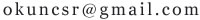张中晓的故人怀念 文学类指哪些专业?
\u6587\u5b66\u5305\u62ec\u54ea\u4e9b\u65b9\u9762\uff1f\u5305\u62ec\u620f\u5267\u3001\u8bd7\u6b4c\u3001\u5c0f\u8bf4\u3001\u6563\u6587\u7b49\u3002
1\u3001\u4e2d\u56fd\u6587\u5b66\u5956
\u8001\u820d\u6587\u5b66\u5956\u3001\u8305\u76fe\u6587\u5b66\u5956\u3001\u9c81\u8fc5\u6587\u5b66\u5956\u3001\u66f9\u79ba\u620f\u5267\u6587\u5b66\u5956\u5e76\u79f0\u5f53\u4ee3\u4e2d\u56fd\u56db\u5927\u6587\u5b66\u5956\u3002
2\u3001\u6587\u5b66\u5de8\u5320
\u53e4\u5e0c\u814a\u8bd7\u4eba\u8377\u9a6c\uff1b \u610f\u5927\u5229\u8bd7\u4eba\u4f46\u4e01\uff1b \u5fb7\u56fd\u8bd7\u4eba\u3001\u5267\u4f5c\u5bb6\u3001\u601d\u60f3\u5bb6\u6b4c\u5fb7\uff1b \u82f1\u56fd\u79ef\u6781\u6d6a\u6f2b\u4e3b\u610f\u8bd7\u4eba\u62dc\u4f26\uff1b \u82f1\u56fd\u6587\u827a\u590d\u5174\u65f6\u671f\u620f\u5267\u5bb6\u3001\u8bd7\u4eba\u838e\u58eb\u6bd4\u4e9a\uff1b \u6cd5\u56fd\u8457\u540d\u4f5c\u5bb6\u96e8\u679c\uff1b \u5370\u5ea6\u4f5c\u5bb6\u3001\u8bd7\u4eba\u548c\u793e\u4f1a\u6d3b\u52a8\u5bb6\u6cf0\u6208\u5c14\uff1b \u4fc4\u56fd\u6587\u5b66\u5de8\u5320\u5217\u592b.\u6258\u5c14\u65af\u6cf0\uff1b \u82cf\u8054\u65e0\u4ea7\u9636\u7ea7\u6587\u5b66\u7684\u5960\u57fa\u4eba\u9ad8\u5c14\u57fa\uff1b \u4e2d\u56fd\u73b0\u4ee3\u4f1f\u5927\u7684\u6587\u5b66\u5bb6\u3001\u601d\u60f3\u5bb6\u9c81\u8fc5\u3002
\u6587\u5b66\u7c7b\u4e13\u4e1a\u65e0\u975e\u4e09\u7c7b\uff0c\u4e2d\u6587\u3001\u5916\u8bed\u548c\u65b0\u95fb\u4f20\u64ad\uff0c\u6bcf\u4e2a\u5206\u7c7b\u4e0b\u7684\u5404\u79cd\u4e13\u4e1a\uff0c\u6240\u5b66\u4e0d\u540c\uff0c\u5c31\u4e1a\u65b9\u5411\u81ea\u7136\u4e5f\u4e0d\u540c\uff0c\u4eca\u5929\u54b1\u4eec\u5c31\u6765\u8be6\u7ec6\u804a\u804a\u3002
《青春祭:记张中晓与胡风》
本文作者:梅志(胡风夫人)
《我与胡风》①一书,原是约请与胡风同案的友人们来回忆过去,并叙述自己及家人亲友因此而遭到的种种悲惨境遇,为的是希望这一段曾经残害了这些有远大抱负、革命热情的进步青年的青春以至生命的历史永不再重演!
但是,自1955年被定为“反革命”案件起至1980年平反时,已有好几位友人含冤死去了,他们已不能亲自叙述他们的冤情和不幸,将真相告诉人们了。只得由他们的亲人来追叙往事,寄托哀思。
但是张中晓,这位被捕时年仅二十五岁的青年,不但没有妻子儿女,也没有留下什么遗著。至于他是如何死的,哪年哪月死的,那是更弄不清了。可是,在一九五五年揭发的材料中,却给他扣上了一大堆不堪入目的诬陷和莫须有的罪名,至今仍使一些人莫明其究竟。这就使我们这些幸存者感到十分沉痛,觉得有责任将所知道的关于他的一切都写出来,这才是对他的最好的悼念。
我记得朋友中最早和张中晓通信的,大概是梅林。那时,梅林在编上海《文汇报》和《文学界》,中晓可能是投稿者。梅林很赏识他,向我介绍说他对胡风很钦佩,谈到一些问题要我去信回答他。我和他通信后,知道他是绍兴人,年纪很轻,由于严重的肺病已卧床数年。他对胡风的理论尤其是对鲁迅先生的著作都有着很独特的见解。于是,我就让他直接和胡风通信了。
这一切,开始得就是这么简单。
我被捕两三个月后,一切他们需要了解的我都自认是如实地交代了,但每次都还严厉地训斥我,总认为我还有“大西瓜”没有交出来。因此,我失眠了,几乎整夜不能合眼,思前想后,实在想不出什么反革命的“大西瓜”来。这样的情形,继续了好久。
一天,审讯员突然向我亮出了一张王牌。那天已快到深夜,我早已被命令上床睡觉了,这时又被叫了起来押往大厅。审讯员鼓着眼睛盯了我一会,我知道这是心理战术,但我心里没鬼,所以这盯视是无效的。
最后他问:“你说过你知道的都交代了。我问你,中央公布要交信后,你们烧了哪些信?”
我说:“没有呀!我们只将信整理了一下,准备交出。”
“嘿!你还替胡风隐瞒!他都交代了。”
我无言对答,只好沉默。
“你记不起来了?好,那我提示你,可不算你但白交代的啰。你们烧了张中晓的信,对吧?你当然知道,我们早说过烧信是不行的,要以毁灭罪证论处。你害怕了是不是?但你只要将那信的内容交代出来,你们就可以从轻发落。”
我记起来了,胡风在整理信时,取出了张中晓在好久前给胡风看的一封信。那是他以个人的名义向党中央汇报下面的一些情况并向党中央提意见的(意思是响应胡风)。但胡风看后觉得没这个必要,同时,一些问题也无法说清,就将信搁下了,只去信劝他不必写这种信。这时,胡风将信重新翻了出来,又看了一遍,觉得如果交出去对张中晓显然会很不利。我也感到,张中晓身体这么坏,只有半边肺,是受不起“批判”和打击的。就这样,胡风把这封信烧掉了。现在要我交代它的内容,我实在记不起来,就当作一封一般的应酬信来复述它的内容。当然,还得承认烧信是有罪的。这自然是过不了关的。最后,我只好将当时的情况,胡风和我所想到的对张中晓可能产生很不利的顾虑,如实说了。审问拖了差不多两三个小时,回屋已快天亮了。这次审问使我的心情更坏了。心想,如果这样一个个问题问下来,我怎么办?我怎么交代得出“反革命”?这是不能编造的。我们没有“反革命”,没有“大西瓜”? .。这时,我脑海中出现了延安来人说到过的“抢救”运动、整风运动的情况。我不是怕皮肉受苦,而是怕精神支持不住。想到这些后,曾几次走向床前的一张硬木大条桌边,想一头撞在那桌子角上。我知道,如果对准太阳穴,那是可以致命的。使我最终下不了这决心的,是因为想到我那时只八岁的小儿子和陪我苦了多年的年迈八十的老母亲,我不能使他们在不幸上又加不幸。我赶紧掉过头去,不敢再看那以死神面孔诱惑我的桌子角。但我实在想不通,不由得在一张纸片上写了“已开始逼供了”几个字。很快,这纸片被看守我的女同胞发现,并抄走了。
几天以后,我又被提审,针对这句话严厉地责问我。我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心情说了(当然没有提到自杀的念头),一边说一边哭了起来。最后,我一再申明,如果这样地要我交代反革命罪行我是交代不出的,随你们判我罪吧。
看来,审讯员也冷静下来了,并且还表示出很诚恳的态度说:“我们并没有强迫你交代你所不知道的事情。如有,你指出来!”
我就将张中晓信件的事提了出来。我说,“要我完全背出这封信来是不可能的,可你就认为我是有意隐瞒,包庇胡风和张中晓。”说到这里,我又哭了:“张中晓是一个病人,我不能乱说害他,他身体受不了的。你们说我包庇,我承担就是了。”
这时,他却说:“我们不要你乱说,乱说也是犯罪。你可以如实地说你所知道的。”
我就提出不能像他所要求的那样把一切都说得那么确切,很多问题,我只能用“不知道”、“可能”、“好像”、“似乎”这类字眼来答复,由你们再根据具体材料去核实。我只能这样交代,我还要申明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反革命罪行。
我想,这话大概又要使他大发雷霆了。还好,他只是对我进行了一番开导。
他问我:“你们反对周扬吧?”
我说:“那是的。”
“你们应当知道周扬是代表党的。”
“知道。”
“那么,你们反周扬不就是反党吗?”
我不敢吱声了。
“反党不就是反革命吗?”
原来如此!经他的推理法这么一推,才使我恍然大悟!所谓反革命只是对某位党内领导人的反对,并不是专指“叛徒”、“国特”而言!时间过得真快!十年、二十年? .过去了。我和胡风在狱中有时想起一些友人,怀念他们,猜测他们可能遇到的不幸,除了叹息外,别无他法。对张中晓,胡风总是说到他的性格倔强,怕经受不住打击。
一九七九年胡风恢复自由,一九八○年我们回到了北京。我到处打听张中晓的情况,只知道他与我们同时被捕,“文革”时被迫害死去,详情则谁也说不清,真令我们痛心和遗憾!
前面已说过,是梅林介绍我和他开始通信的。那大约是在一九五○年批判《武训传》之前。后来才知道,他对《文艺报》对胡风《安魂曲》的批评有不同看法,还写了信去责问《文艺报》。
关于他的身世,他曾在给胡风的信中详细地介绍过,这可算是了解他的第一手材料了,故摘抄如下:
我生于一九三○年,出身是“读书人”家庭,家里有二十来亩田,一所在乡下的房子,这在绍兴是算小康之家的。我的父亲是邮局里的职员,是一个非常之诚实、忠厚的人,他靠旧社会给他的善良的、超人的德性生活到今天,他在邮局中做事已有二十七八年了。抗战的几年,我家里变得很穷,父亲没有本领赚“外快”,一月收入只有二三斗米,连自己也不能维持,我家就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我家那时有五个弟弟、两个妹妹、一个母亲、一个老祖母、一个没有了儿女的残废的姑婆)。我在十四岁的一年读过一年初中,以后,失学了。为了生活,我曾做过一些小生意,摆过香烟摊、糖摊、杂粮摊等等。挨过日本人和“和平佬”①的巴掌(这里在沦陷时,老百姓没有一个不挨过打的),还被“梅机关”②和伪军捉去过一次,随军走了二十多天。
在中学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先生(他是校中的教师),他藏有许多书,现在能记忆的是:鲁迅先生的书差不多都有,有一套《译文》,里面的插画使我惊奇,还有几本《七月》和几本“剪报”。我离开学校的时候,还一直和他在一起,每天有一点空,我总是去看他的。《希望》,我也在他那里看到的,只有一本,仿佛是第二期,书面是没有了,很破碎。
那时,我当然是看不懂。但,本能地觉得这些是与我的生活有着关联的,这里面,这个先生对于我的帮助是很大的,他往往用这些书里的意义鼓励我,向我启发。话是极平常的,但我那时感觉到他的话有着与平常不同的见解。他的英文很好,我跟他学英文(一律都没有报酬)。总之,这个先生对我帮助是很大的,除了学问之外,他的诚实、但白、单纯的性格,使我或多或少地感染了一些的。可怜得很,这个先生在抗战胜利前五个月(一九四五年三月)被日本宪兵队拿去了,原因是他的一位表姐是共产党。后来,又在他那儿搜出了犯“禁”的书。
抗战胜利后,我的叔父回家了,国民党做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由于他的帮助,我在一九四六年北碚考进了相辉学院(西迁时复旦旧址),那时,我的英文自修到已能读《莎氏乐府本事》,我想读外文系,我的叔父要我读农艺系,于是我进了农艺系,第二年转入重大。
这二年,我除了“正经功课”之外,读了一点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读了几部西洋名著。重庆和北碚对我帮助很大的。重庆的“旧书摊”、北磅的图书馆,我从那里读了不少的书籍。我有五本《希望》、十多本《七月》。桂林版的《山水文丛》(你的《死人复活的时候》)、《人与文学》也是那时买的。还有你的论文集《看云人手记》(《密云期风习小纪》)、《在混乱里面》等等。我对你们接近的原因,是因为你们所理解的人生,是使我感诚和亲切,和我息息相关。
① 指汪伪的和平军。
可惜,这些书我回家时都抛了。
一九四八年五月,我突然吐血(据医生诊断是已有五六年历史的肺结核)很厉害,血吐了二大面盆,原因大概是过去几年的困苦和两年来的“用功”。于是,回家。现在,又两年了。
现在,身体已可动动。两年来,虽然是睡在床上,但也读了一些书。你的《论现实主义的路》和《逆流的日子》,就是在这段时间内读的。此外,我还读些《蚂蚁》、《荒鸡》,《鲁迅全集》读了十多卷,还读了《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精神的搏斗记录,有助于我战胜肺结核的进攻。
我过去曾写过一些杂文和诗,现在,待身体较再好一点,我准备再写。两年来,我脾气变了许多,几乎恨一切人。两年来,我睡在床上,家中情形也不甚好,我是用最大的力量战胜肺结核的,我想,这是使我恨一切的原因。两年来,我所受的苦难比从前的一些日子多,我懂得了什么叫做贫穷!什么叫做病,什么叫做挣扎!? .对这个社会秩序,我憎恨!
人受苦越多,对甜味渴望得越厉害,而且,会诚实地接受“糖衣毒药包”的。去年,我被政治上的彩云震昏了!就学习文艺方面来说,我从生活费里省下几块钱来订了半年《文艺报》(第一卷),我想,这里面该集合全国文艺的精华吧!但,谁知上了当:越看越讨厌。起初,总以为我还没有被“改造”,感情合不来的缘故(这是照现在的说法)。后来,在第十二期上看了沙鸥的压轴戏,我就从讨厌变成憎恶了。
我从这封一九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张中晓给胡风的信中原封不动地抄录下了近两干字(由于原信破损,有两处无法抄清字句,只得以□代之)。
应该说明的是,这封信长达四五千字,而《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仅仅只摘引了“我过去曾写过一些杂文和诗,现在待身体较再好一点,我准备再写。两年来,我脾气变了许多,几乎恨一切人? .对这个社会秩序,我憎恨。”这几句列为第三批材料第“六七”封信的摘录。也就是全部材料的最后一封,向善良的人们揭出这位“反革命分子”的“狰狞面目”。
从这封介绍自己的信中,胡风理解了他的心情。并且,从他另外的信(原信已找不着了)中知道,他家聚族而居的房子正在拍卖,各房为了争夺财产暴露出的尔虞我诈使他很失望,因此常在信中说出“封建势力正在杀人”这类活。至于“对这个社会秩序,我憎恨”云云,很明显是一个卧病在床的病人变态了的悲观世界观的反映,他病态的所感所见的周围的小社会。但因为他还只是一个小青年,就有着这样阴暗的心情,是不好的。胡风就写信去劝慰他开导他。
大约是一九五二年吧,他由梅林(当时任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约请,经社长同意,来到刚成立不久的新文艺出版社任编辑。这时,我才第一次见到他。好像是由他的同事罗洛陪同来的。他高高的个儿,面目很清秀,但看得出他的肩膀一边高一边低,这是由于肋骨被折断五根将半个肺部都压缩了的结果。就座后,他显得很腼腆,说话很少。而罗洛也是一个不爱多说话的文静青年。这可使我这位主人很不安,冷场总不好呀。幸好,我的小儿子进来了,他“罗叔叔”“张叔叔”地叫着,问这问那,才使得气氛热闹了起来。
这之后,到星期天有时间他们就会来坐坐。那时,胡风基本上是住在北京,听取对他的批评。所以,他们来时我就告诉他们一些胡风在京的情况。
这时我才发现张中晓很容易激动,常说出一些很尖锐的话,一反平常的温和和沉默。他对一些事物的看法,尤其是对文艺思想文艺作品的评论,很使我佩服。而且,我从梅林那里得知他的编辑工作也做得很出色,对稿件提出的意见常得到同事们的赏识。《铁道游击队》的原稿就是经他看过并提出修改意见的。这时,他的工作和生活都很顺利,工资不算低,身体健康多了。我曾很关心地向他提过,应该给家里寄点钱。他说,家里已好过多了,弟妹们都长大了,工作的工作,出嫁的出嫁,只两个小弟弟在家读书,他有时寄点钱或衣物给家里。
他来我家的谈话,有时我写信告诉胡风,胡风也经常和他通信。可能是肺病患者的特点吧,他在谈问题时常显出过敏的偏激,用词有时也过分夸张,例如关于《讲话》的一些不敬的评语。这本来是私人通信。一个人世不深的青年人还没有学会隐瞒自己的想法,就直白地在给胡风的信上用了“图腾”和“屠杀生灵”这类过于刺激人的字眼。等到我们被逮捕抄出一切信件后,这些对伟大领袖不敬的话加上了怒气冲天的编者按,就成了胡风和他罪大恶极的罪状之一。我们敬爱的领袖对这个张中晓是印象很深的,幸好他可不是封建帝王,而是宽宏大量的领袖,知道人头不是韭菜,砍掉是长不出来的,张中晓和我们这些人才没有身首异处!
一九五三年,我们举家离开了上海定居北京。中晓很关心胡风和路翎等朋友的情况,常来信谈论他们的作品和文艺界的情形。一九五四年秋未,他趁回家探亲的时间,到北京来看我们,想同胡风面谈自己的一些看法。在这期间,他和胡风、芦甸、路翎谈过几次话,并且看了“三十万言”的初稿。他很同情胡风和路翎等友人的处境,回去后才想到用个人名义给党中央写信,为他们抱不平。这就是公安机关要我交代的那封信的来历。
一九七九年,胡风知道他(张中晓)已去世的消息后,非常难过,曾想在了解详细情况后写篇悼念文章以纪念他。但后来,胡风的心因性精神病复发,我就再也不敢同他提起张中晓这个名字了。
我想方设法探询中晓那些年的情况,后来同他的父亲通了信。知道他家很穷困,就请王元化同志(一直很爱护他的新文艺出版社时的上级)向上海市出版局要到了五百元的抚恤金。我们只能为老人家尽这一点点力。
一九八一年我陪胡风在上海就医时,中晓的一位弟弟到旅馆来看我。他是一九五七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时由于在向党提意见的座谈会上表示了对“胡风分子”的同情,而被打成“右派”分子,罪名是“替胡风反革命分子张中晓鸣不平”。毕业后,充军发配到新疆去服劳役。沉冤二十年,直到四十岁才作为一名教师走上了讲台。这次他趁回家探亲之便找到母校党委,要求为他落实政策“割尾巴”。总算给他重新写了“改正结论”。
从他那里我才知道了他大哥的一些情况。他大哥大约是一九五×年(?)由公安机关批准回家养病。生活很是困苦,但还是想方设法找书看,翻出了一些古旧书籍,还作了不少的笔记杂感。说到这里,他从绿帆布包里取出一沓乱纸交给我。
那是一些旧帐本和学生练习本的空页,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毛笔小字,很难看清。可见当时中晓是穷到连笔记本都买不起,为了省纸费了多大劲来写!他弟弟还说,他曾将上半截已穿成满是破洞的背心剪下较完整的下半截来改成一条短裤,就这样地度过一个夏天。那时,母亲到在江西当干部的二弟那里去了,家里只靠老父的一点退休金要养活两个小弟弟,困难是相当大的。
他弟弟告诉我,“哥哥对我的学习还是挺关心的,常问问我的功课。尤其是对小弟,他喜欢画画,哥哥就常鼓励他,并给他一些批评指导。”中晓给他弟弟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解放前他是追求进步的,且勤奋好学。一九五0 年刚满二十岁就在当时的《文汇报》副刊上发表长篇文章。他与胡先生的交往,也是解放后才开始的。一九五五年报载三批材料,说他们组成了一个‘反革命集团’,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在遣返回乡带罪养病时我曾私下里问过他,他自己讲,‘我写恨一切人,是指恨一切人身上所有的落后习性;写憎恨这个社会秩序,是指恨制度上的缺陷(封建残余)。我想给他(指胡先生)写信可以写得尖刻坦率些,怎么会料到这些信后来都成了反革命的材料。? .我并没有反对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但我觉得毛主席的文艺观点是有时代局限性的。谁知这些看法被截头去尾加上按语,都成了反革命的罪行!’”
这是事隔若干年后他所做的自我批判吧,今天已经没有解释的必要了。这些话难道触犯了刑律吗?结果却连他的弟弟都遭到了充军新疆二十余年的无妄之灾,这谁能想得到呢?
“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勒令他返回上海,放在新华书店的库房里劳动。由于劳累过度和营养不良,使得他肺病复发,又得不到任何治疗,终于吐血不止,送进医院后,不久就死了。
真情是否如此,谁也无法调查。只有他本人才能说出身受的折磨和痛苦,但这一点已无法办到了。他死时,大约还不到四十岁。
张中晓信上的一些话是否是反动言论,可惜他早死了,无法来解释或申辩,只有待历史重新评说。他连后人都没有,也没有留下遗物或遗著。我手头有他唯一的一张照片,是他到北京后芦甸请他游北海公园时,和我小儿子三人合照的。不幸三人中幸存的只有当时仅八岁的小孩了。那一沓笔记,本来我们请何满子同志给他整理,看能否辑成文章和过去的文章合编出来,以留个纪念。满子兄很热心地答应了。但后来他弟弟又遵父命另请别人整理,因此直拖到现在也还没能整理出来,真令人感到遗憾。
他和胡风二人之间的通信,至今我们只找到几封他写给胡风的信,而胡风写给他的信(仅《二批材料》中就有十一封),据公安部门说,应该是发还给收信人了。但既然收信人已不在了,那究竟发还给谁了呢?不得而知。我希望能够早日找到这些材料,因为它们能够证实胡风和张中晓的“反革命”言论的实质。
今天,由我来为这位年轻的“同案犯”写这招魂式的追忆,心情实在是很伤痛的,惟愿他的灵魂在天堂地府都能得到安息!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八日夜
注释:① 《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六人回忆》一书,约六十万字,已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绛旓細寮犱腑鏅撶殑淇′欢涓彁鍙婁簡浠栧悜鍏氫腑澶眹鎶ョ殑鎯呭喌锛岃儭椋庡嚭浜庨【铏戝皢鍏堕攢姣侊紝杩欐垚涓哄璁腑鐨勯噸瑕佺嚎绱傛蹇楁彁鍒板紶涓檽鐨勬ф牸鍊斿己锛岃韩浣撶姸鍐典笉浣筹紝濂逛笉鑳界紪閫犱换浣曚笉瀹炵殑浜嬫儏鏉ラ櫡瀹充粬銆備竴涔濅竷涔濆勾鑳¢鑾烽噴锛屼粬浠鎵惧紶涓檽鐨勪笅钀斤紝寰楃煡浠栧湪鈥滄枃闈┾濅腑涓嶅垢鍘讳笘锛岃繖璁╀粬浠劅鍒扮棝蹇冨拰閬楁喚銆傚紶涓檽鐨勪俊浠朵腑娴侀湶鍑哄绀句細鍜...
绛旓細涓涔濅竷涔濆勾,鑳¢鐭ラ亾浠(寮犱腑鏅)宸插幓涓栫殑娑堟伅鍚,闈炲父闅捐繃,鏇炬兂鍦ㄤ簡瑙h缁嗘儏鍐靛悗鍐欑瘒鎮煎康鏂囩珷浠ョ邯蹇典粬銆備絾鍚庢潵,鑳¢鐨勫績鍥犳х簿绁炵梾澶嶅彂,鎴戝氨鍐嶄篃涓嶆暍鍚屼粬鎻愯捣寮犱腑鏅撹繖涓悕瀛椾簡銆傛垜鎯虫柟璁炬硶鎺㈣涓檽閭d簺骞寸殑鎯呭喌,鍚庢潵鍚屼粬鐨勭埗浜查氫簡淇°傜煡閬撲粬瀹跺緢绌峰洶,灏辫鐜嬪厓鍖栧悓蹇(涓鐩村緢鐖辨姢浠栫殑鏂版枃鑹哄嚭鐗堢ぞ鏃剁殑涓婄骇)鍚戜笂...
绛旓細浠ュ墠鏃╂湁璺簡,浠ュ悗涔熻姘歌繙鏈夎矾銆71. 寰浜,鎴栬鏁呬汉,灏卞儚閭h惤鍙朵竴鏍,鍦ㄦ垜鐢熷懡鐨勭椋庨噷,浠庨粦鏆椾腑椋樿浆杩涙槑浜,浠庢槑浜腑閫冮亖杩涢粦鏆椼傚湪鏄庝寒涓殑,鎴戠湅瑙佷粬浠,鍦ㄩ粦鏆楅噷鐨勬垜鍙湁鎯宠薄浠栦滑,渚濋潬閭d簺椋樿浆杩涙槑浜腑鐨勫幓鎯宠薄閭d簺閫冮亖杩涢粦鏆楅噷鐨勩傛垜鏃犳硶鐪嬪埌榛戞殫閲屼粬浠殑鐪熷疄,鍙兘鐪嬪埌鎯宠薄涓粬浠殑鏍峰瓙鈥斺旈殢鐫鎴戠殑鎯宠薄浠栦滑椋...
绛旓細璁烘浌鎿嶆ф牸 鏇规搷鏄婁笁鍥芥紨涔夈嬭繖閮ㄦ垜鍥戒紭绉鐨勯暱绡囧彜鍏稿皬璇寸殑浠h〃涔嬩綔銆傚湪杩欓儴浣滃搧閲屼綔鑰呭閫犱簡涓鎵瑰吀鍨嬭岃壓鏈殑浜虹墿褰㈣薄銆傚悓鍏朵粬鍑犻儴鍙ゅ吀鍚嶈憲鐩告瘮锛屽湪浣滆呯殑绗斾笅锛岃繖浜涗汉鐗╁舰璞℃槸鍦ㄥ巻鍙蹭笂鐪熷疄瀛樺湪鐨勪汉鐗┿備粖澶╂垜浠兂璁ㄨ鐨勬槸銆婁笁鍥芥紨涔夈嬩腑浜夎姣旇緝澶氱殑涓涓汉鐗╋紝鏇规搷銆傛浌鎿嶅湪鎬ф牸涓婄殑绻佸銆佽兘鍔涚殑鍏ㄩ潰銆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