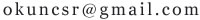谁有《自剖》原诗 走着走着,就散了,回忆都淡了;到底是谁的诗?徐志摩还是席慕蓉...
\u8c01\u6709\u5f90\u5fd7\u6469\u7684\u6240\u6709\u8bd7\uff1f\u8bd7\u96c6\u8457\u6709\uff1a\u300a\u5fd7\u6469\u7684\u8bd7\u300b\uff0c\u300a\u7fe1\u51b7\u7fe0\u7684\u4e00\u591c\u300b\u3001\u300a\u731b\u864e\u96c6\u300b\u3001\u300a\u4e91\u6e38\u300b\uff1b
\u6563\u6587\u96c6\u6709\uff1a\u300a\u843d\u53f6\u300b\u3001\u300a\u5df4\u9ece\u7684\u9cde\u722a\u300b\u3001\u300a\u81ea\u5256\u300b\u3001\u300a\u79cb\u300b\u3001\u300a\u8f6e\u76d8\u300b\uff1b
\u5c0f\u8bf4\u300a\u6625\u75d5\u300b\uff1b
\u620f\u5267\u300a\u535e\u6606\u5188\u300b\uff08\u4e0e\u9646\u5c0f\u66fc\u5408\u5199\uff09\uff0c\u65e5\u8bb0\u300a\u7231\u7709\u5c0f\u672d\u300b\u3001\u300a\u5fd7\u6469\u65e5\u8bb0\u300b\uff1b
\u8bd1\u8457\u300a\u66fc\u6b8a\u6590\u5c14\u5c0f\u8bf4\u96c6\u300b\u7b49\u3002
\u662f\u5f90\u5fd7\u6469\u7684
\u8d70\u7740\u8d70\u7740\uff0c\u5c31\u6563\u4e86\uff0c\u56de\u5fc6\u90fd\u6de1\u4e86\uff1b
\u770b\u7740\u770b\u7740\uff0c\u5c31\u7d2f\u4e86\uff0c\u661f\u5149\u4e5f\u6697\u4e86\uff1b
\u542c\u7740\u542c\u7740\uff0c\u5c31\u9192\u4e86\uff0c\u5f00\u59cb\u57cb\u6028\u4e86\uff1b
\u56de\u5934\u53d1\u73b0\uff0c\u4f60\u4e0d\u89c1\u4e86\uff0c\u7a81\u7136\u6211\u4e71\u4e86\u3002
\u552f\u7f8e\u6d6a\u6f2b\u7684\u7231\u60c5\uff0c\u603b\u662f\u8ba9\u4eba\u5411\u5f80\u4e0d\u5df2\u3002\u9519\u7efc\u590d\u6742\u7684\u60c5\u8282\uff0c\u603b\u662f\u8ba9\u4eba\u671f\u76fc\u4e0d\u5df2\uff0c\u60b2\u51c4\u9057\u61be\u7684\u7ed3\u5c40\uff0c\u603b\u662f\u8ba9\u4eba\u550f\u5618\u4e0d\u5df2\u3002\u5584\u826f\u7eaf\u771f\u7684\u5973\u5b69\uff0c\u6709\u591a\u5c11\u4eba\u5728\u80cc\u540e\u4e3a\u4f60\u52a0\u6cb9\uff0c\u4e3a\u81ea\u5df1\uff0c\u4e3a\u4ed6\u4eba\uff0c\u52c7\u6562\u7684\u8d70\u4e0b\u53bb\u3002\u5351\u9119\u80ae\u810f\u7684\u624b\u6bb5\uff0c\u4f60\u8ba9\u4eba\u6df1\u6076\u75db\u7edd\u7684\u60c5\u51b5\u4e0b\uff0c\u4f60\u5c45\u7136\u6d51\u7136\u4e0d\u77e5\uff0c\u53ef\u6068\uff0c\u53ef\u60b2\uff0c\u4ea6\u6216\u662f\u53ef\u601c\uff1f
\u6269\u5c55\u8d44\u6599\uff1a
\u5f90\u5fd7\u6469\u8bd7\u5b57\u53e5\u6e05\u65b0\uff0c\u97f5\u5f8b\u8c10\u548c\uff0c\u6bd4\u55bb\u65b0\u5947\uff0c\u60f3\u8c61\u4e30\u5bcc\uff0c\u610f\u5883\u4f18\u7f8e\uff0c\u795e\u601d\u98d8\u9038\uff0c\u5bcc\u4e8e\u53d8\u5316\uff0c\u5e76\u8ffd\u6c42\u827a\u672f\u5f62\u5f0f\u7684\u6574\u996c\u3001\u534e\u7f8e\uff0c\u5177\u6709\u9c9c\u660e\u7684\u827a\u672f\u4e2a\u6027\u3002
\u6563\u6587\u4e5f\u81ea\u6210\u4e00\u683c\uff0c\u53d6\u5f97\u4e86\u4e0d\u4e9a\u4e8e\u8bd7\u6b4c\u7684\u6210\u5c31\uff0c\u5176\u4e2d\u300a\u81ea\u5256\u300b\uff0c\u300a\u60f3\u98de\u300b\uff0c\u300a\u6211\u6240\u77e5\u9053\u7684\u5eb7\u6865\u300b\uff0c\u300a\u7fe1\u51b7\u7fe0\u5c71\u5c45\u95f2\u8bdd\u300b\u7b49\u90fd\u662f\u4f20\u4e16\u7684\u540d\u7bc7\u3002
\u4eba\u4eec\u770b\u5f85\u5f90\u5fd7\u6469\u53ca\u5176\u521b\u4f5c\u603b\u662f\u628a\u4ed6\u4e0e\u65b0\u6708\u6d3e\u8fde\u5728\u4e00\u8d77\u7684\uff0c\u8ba4\u5b9a\u4ed6\u4e3a\u65b0\u6708\u6d3e\u7684\u4ee3\u8868\u4f5c\u5bb6\uff0c\u79f0\u4ed6\u4e3a\u65b0\u6708\u6d3e\u7684\u201c\u76df\u4e3b\u201d\uff0c\u8fd9\u662f\u56e0\u4e3a\u65b0\u6708\u6d3e\u7684\u5f62\u6210\u76f4\u81f3\u6d88\u4ea1\uff0c\u90fd\u4e0e\u4ed6\u53d1\u751f\u7740\u5bc6\u5207\u7684\u5173\u7cfb\uff0c\u4ed6\u53c2\u4e0e\u4e86\u65b0\u6708\u6d3e\u7684\u6574\u4e2a\u6d3b\u52a8\uff0c\u4ed6\u7684\u521b\u4f5c\u4f53\u73b0\u4e86\u65b0\u6708\u6d41\u6d3e\u9c9c\u660e\u7279\u5f81\u3002
\u53c2\u8003\u8d44\u6599\u6765\u6e90\uff1a\u767e\u5ea6\u767e\u79d1\u2014\u2014\u8d70\u7740\u8d70\u7740\u5c31\u6563\u4e86\u56de\u5fc6\u90fd\u6de1\u4e86
\u53c2\u8003\u8d44\u6599\u6765\u6e90\uff1a\u767e\u5ea6\u767e\u79d1\u2014\u2014\u5f90\u5fd7\u6469
自 剖
徐志摩
我是个好动的人;每回我身体行动的时候,我的思想也仿佛就跟着跳荡。我做的诗,
不论它们是怎样的“无聊”,有不少是在行旅期中想起的。我爱动,爱看动的事物,爱
活泼的人,爱水,爱空中的飞鸟,爱车窗外掣过的田野山水。星光的闪动,草叶上露珠
的颤动,花须在微风中的摇动,雷雨时云空的变动,大海中波涛的汹涌,都是在在触动
我感兴的情景。是动,不论是什么性质,就是我的兴趣,我的灵感。是动就会催快我的
呼吸,加添我的生命。
近来却大大的变样了。第一我自身的肢体,已不如原先灵活;我的心也同样的感受
了不知是年岁还是什么的拘絷。动的现象再不能给我欢喜,给我启示。先前我看着在阳
光中闪烁的余波,就仿佛看见了神仙宫阙——什么荒诞美丽的幻觉,不在我的脑中一闪
闪的掠过;现在不同了,阳光只是阳光,流波只是流波,任凭景色怎样的灿烂,再也照
不化我的呆木的心灵。我的思想,如其偶尔有,也只似岩石上的藤萝,贴着枯干的粗糙
的石面,极困难的蜒着;颜色是苍黑的,姿态是崛强的。
我自己也不懂得何以这变迁来得这样的兀突,这样的深彻。
原先我在人前自觉竟是一注的流泉,在在有飞沫,在在有闪光;现在这泉眼,如其
还在,仿佛是叫一块石板不留余隙的给镇住了。我再没有先前那样蓬勃的情趣,每回我
想说话的时候,就觉着那石块的重压,怎么也掀不动,怎么也推不开,结果只能自安沉
默!“你再不用想什么了,你再没有什么可想的了”;“你再不用开口了,你再没有什
么话可说的了,”
我常觉得我沉闷的心府里有这样半嘲讽半吊唁的谆嘱。
说来我思想上或经验上也并不曾经受什么过分剧烈的戟刺。我处境是向来顺的,现
在如其有不同,只是更顺了的。那么为什么这变迁?远的不说,就比如我年前到欧洲去
时的心境:啊!我那时还不是一只初长毛角的野鹿?什么颜色不激动我的视觉,什么香
味不奋兴我的嗅觉?我记得我在意大利写游记的时候,情绪是何等的活泼,兴趣何等的
醇厚,一路来眼见耳听心感的种种,哪一样不活栩栩的业集在我的笔端,争求充分的表
现!如今呢?我这次到南方去,来回也有一个多月的光景,这期内眼见耳听心感的事物
也该有不少。我未动身前,又何尝不自喜此去又可以有机会饱餐西湖的风色,邓尉的梅
香——单提一两件最合我脾胃的事。有好多朋友也曾期望我在这闲暇的假期中采集一点
江南风趣,归来时,至少也该带回一两篇爽口的诗文,给在北京泥土的空气中活命的朋
友们一些清醒的消遣。但在事实上不但在南中时我白瞪着大眼,看天亮换天昏,又闭上
了眼,拼天昏换天亮,一枝秃笔跟着我涉海去,又跟着我涉海回来,正如岩洞里的一根
石笋,压根儿就没一点摇动的消息;就在我回京后这十来天,任凭朋友们怎样的催促,
自己良心怎样的责备,我的笔尖上还是滴不出一点墨沈来。我也曾勉强想想,勉强想写,
但到底还是白费!可怕是这心灵骤然的呆顿。完全死了不成?我自己在疑惑。
说来是时局也许有关系。我到京几天就逢着空前的血案。五卅事件发生时我正在意
大利山中,采茉莉花编花篮儿玩,翡冷翠①山中只见明星与流萤的交唤,花香与山色的
温存,俗氛是吹不到的。直到七月间到了伦敦,我才理会国内风光的惨淡,等得我赶回
来时,设想中的激昂,又早变成了明日黄花,看得见的痕迹只有满城黄墙上墨彩斑斓的
“泣告”。
这回却不同。屠杀的事实不仅是在我住的城子里发见,我有时竟觉得是我自己的灵
府里的一个惨象。杀死的不仅是青年们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仿佛遭着了致命的打击,
比是国务院前的断脰残肢,再也不能回复生动与连贯。但这深刻的难受在我是无名的,
是不能完全解释的。这回事变的奇惨性引起愤慨与悲切是一件事,但同时我们也知道在
这根本起变态作用的社会里,什么怪诞的情形都是可能的。屠杀无辜,还不是年来最平
常的现象。自从内战纠结以来,在受战祸的区域内,哪一处村落不曾分到过遭奸污的女
性,屠残的骨肉,供牺牲的生命财产?这无非是给冤氛团结的地面上多添一团更集中更
鲜艳的怨毒。再说哪一个民族的解放史能不浓浓的染着Martyrs②的腔血?俄国革命的开
幕就是二十年前冬宫的血景。只要我们有识力认定,有胆量实行,我们理想中的革命,
这回羔羊的血就不会是白涂的。所以我个人的沉闷决不完全是这回惨案引起的感情作用。
爱和平是我的生性。在怨毒、猜忌、残杀的空气中,我的神经每每感受一种不可名
状的压迫。记得前年奉直战争时我过的那日子简直是一团黑漆,每晚更深时,独自抱着
脑壳伏在书桌上受罪,仿佛整个时代的沉闷盖在我的头顶——直到写下了“毒药”那几
首不成形的咒诅诗以后,我心头的紧张才渐渐的缓和下去。这回又有同样的情形;只觉
着烦,只觉着闷,感想来时只是破碎,笔头只是笨滞。结果身体也不舒畅,像是蜡油涂
抹住了全身毛窍似的难过,一天过去了又是一天,我这里又在重演更深独坐箍紧脑壳的
姿势,窗外皎洁的月光,分明是在嘲讽我内心的枯窘!
不,我还得往更深处挖。我不能叫这时局来替我思想骤然的呆顿负责,我得往我自
己生活的底里找去。
平常有几种原因可以影响我们的心灵活动。实际生活的牵掣可以劫去我们心灵所需
要的闲暇,积成一种压迫。在某种热烈的想望不曾得满足时,我们感觉精神上的烦闷与
焦躁,失望更是颠覆内心平衡的一个大原因;较剧烈的种类可以麻痹我们的灵智,淹没
我们的理性。但这些都合不上我的病源;因为我在实际生活里已经得到十分的幸运,我
的潜在意识里,我敢说不该有什么压着的欲望在作怪。
但是在实际上反过来看另有一种情形可以阻塞或是减少你心灵的活动。我们知道舒
服、健康、幸福,是人生的目标,我们因此推想我们痛苦的起点是在望见那些目标而得
不到的时候。我们常听人说“假如我像某人那样生活无忧我一定可以好好的做事,不比
现在整天的精神全花在琐碎的烦恼上。”我们又听说“我不能做事就为身体太坏,若是
精神来得,那就……”我们又常常设想幸福的境界,我们想“只要有一个意中人在跟前
那我一定奋发,什么事做不到?”但是不,在事实上,舒服、健康、幸福,不但不一定
是帮助或奖励心灵生活的条件,它们有时正得相反的效果。我们看不起有钱人,在社会
上得意人,肌肉过分发展的运动家,也正在此;至于年少人幻想中的美满幸福,我敢说
等得当真有了红袖添香,你的书也就读不出所以然来,且不说什么在学问上或艺术上更
认真的工作。
那末生活的满足是我的病源吗?
“在先前的日子”,一个真知我的朋友,就说:“正为是你生活不得平衡,正为你
有欲望不得满足,你的压在内里的Libido③就形成一种升华的现象,结果你就借文学来
发泄你生理上的郁结(你不常说你从事文学是一件不预期的事吗?)这情形又容易在你
的意识里形成一种虚幻的希望,因为你的写作得到一部分赞许,你就自以为确有相当创
作的天赋以及独立思想的能力。但你只是自冤自,实在你并没有什么超人一等的天赋,
你的设想多半是虚荣,你的以前的成绩只是升华的结果。所以现在等得你生活换了样,
感情上有了安顿,你就发见你向来写作的来源顿呈萎缩甚至枯竭的现象;而你又不愿意
承认这情形的实在,妄想到你身子以外去找你思想枯窘的原因,所以你就不由的感到深
刻的烦闷。你只是对你自己生气,不甘心承认你自己的本相。不,你原来并没有三头六
臂的!
“你对文艺并没有真兴趣,对学问并没有真热心。你本来没有什么更高的志愿,除
了相当合理的生活,你只配安分做一个平常人,享你命里铸定的‘幸福’;在事业界,
在文艺创作界,在学问界内,全没有你的位置,你真的没有那能耐。不信你只要自问在
你心里的心里有没有那无形的‘推力’,整天整夜的恼着你,逼着你,督着你,放开实
际生活的全部,单望着不可捉模的创作境界里去冒险?是的,顶明显的关键就是那无形
的推力或是冲动(The Impulse),没有它人类就没有科学,没有文学,没有艺术,没
有一切超越功利实用性质的创作。你知道在国外(国内当然也有,许没那样多)有多少
人被这无形的推力驱使着,在实际生活上变成一种离魂病性质的变态动物,不但人间所
有的虚荣永远沾不上他们的思想,就连维持生命的睡眠饮食,在他们都失了重要,他们
全部的心力只是在他们那无形的推力所指示的特殊方向上集中应用。怪不得有人说天才
是疯癫;我们在巴黎、伦敦不就到处碰得着这类怪人?如其他是一个美术家,恼着他的
就只怎样可以完全表现他那理想中的形体;一个线条的准确,某种色彩的调谐,在他会
得比他生身父母的生死与国家的存亡更重要,更迫切,更要求注意。我们知道专门学者
有终身掘坟墓的,研究蚊虫生理的,观察亿万万里外一个星的动定的。并且他们决不问
社会对于他们的劳力有否任何的认识,那就是虚荣的进路;他们是被一点无形的推力的
魔鬼盅定了的。
“这是关于文艺创作的话。你自问有没有这种情形。你也许经验过什么‘灵感’,
那也许有,但你却不要把刹那误认作永久的,虚幻认作真实。至于说思想与真实学问的
话,那也得背后有一种推力,方向许不同,性质还是不变。做学问你得有原动的好奇心,
得有天然热情的态度去做求知识的工夫。真思想家的准备,除了特强的理智,还得有一
种原动的信仰;信仰或寻求信仰,是一切思想的出发点:极端的怀疑派思想也只是期望
重新位置信仰的一种努力。从古来没有一个思想家不是宗教性的。在他们,各按各的倾
向,一切人生的和理智的问题是实在有的;神的有无,善与恶,本体问题,认识问题,
意志自由问题,在他们看来都是含逼迫性的现象,要求合理的解答——比山岭的崇高,
水的流动,爱的甜蜜更真,更实在,更耸动。他们的一点心灵,就永远在他们设想的一
种或多种问题的周围飞舞、旋绕,正如灯蛾之于火焰:牺牲自身来贯彻火焰中心的秘密,
是他们共有的决心。
“这种惨烈的情形,你怕也没有吧?我不说你的心幕上就没有思想的影子;但它们
怕只是虚影,像水面上的云影,云过影子就跟着消散,不是石上的溜痕越日久越深刻。
“这样说下来,你倒可以安心了!因为个人最大的悲剧是设想一个虚无的境界来谎
骗你自己;骗不到底的时候你就得忍受‘幻灭’的莫大的苦痛。与其那样,还不如及早
认清自己的深浅,不要把不必要的负担,放上支撑不住的肩背,压坏你自己,还难免旁
人的笑话!朋友,不要迷了,定下心来享你现成的福分吧;思想不是你的分,文艺创作
不是你的分,独立的事业更不是你的分!天生抗了重担来的那也没法想(哪一个天才不
是活受罪!)你是原来轻松的,这是多可羡慕,多可贺喜的一个发见!算了吧,朋友!”
三月二十五至四月一日
① 翡冷翠,通译佛罗伦萨。
② Martyrs,英文“殉难者”、“烈士”。
③ Libilo,通译里比多,心理学名词。
徐志摩——《想飞》
假如这时候窗子外有雪——街上,城墙上,屋脊上,都是雪,胡同口一家屋檐下偎着一个戴黑兜帽的巡警,半拢着睡眼,看棉团似的雪花在半空中跳着玩……假如这夜是一个深极了的啊,不是壁上挂钟的时针指示给我们看的深夜,这深就比是一个山洞的深,一个往下钻螺旋形的山洞的深……
假如我能有这样一个深夜,它那无底的阴森捻起我遍体的毫管;再能有窗子外不住往下筛的雪,筛淡了远近间飏动的市谣;筛泯了在泥道上挣扎的车轮;筛灭了脑壳中不妥协的潜流……
我要那深,我要那静。那在树荫浓密处躲着的夜鹰,轻易不敢在天光还在照亮时出来睁眼。思想:它也得等。
青天里有一点子黑的。正冲着太阳耀眼,望不真,你把手遮着眼,对着那两株树缝里瞧,黑的,有榧子来大,不,有桃子来大——嘿,又移着往西了!
我们吃了中饭出来到海边去。(这是英国康槐尔极南的一角,三面是大西洋)。勖丽丽的叫响从我们的脚底下匀匀的往上颤,齐着腰,到了肩高,过了头顶,高入了云,高出了云。啊!你能不能把一种急震的乐音想象成一阵光明的细雨,从蓝天里冲着这平铺着青绿的地面不住的下?不,那雨点都是跳舞的小脚,安琪儿的。云雀们也吃过了饭,离开了它们卑微的地巢飞往高处做工去。上帝给它们的工作,替上帝做的工作。瞧着,这儿一只,那边又起了两!一起就冲着天顶飞,小翅膀活动的多快活,圆圆的,不踌躇的飞,——它们就认识青天。一起就开口唱,小嗓子活动的多快活,一颗颗小精圆珠子直往外唾,亮亮的唾,脆脆的唾,——它们赞美的是青天。瞧着,这飞得多高,有豆子大,有芝麻大,黑刺刺的一屑,直顶着无底的天顶细细的摇,——这全看不见了,影子都没了!但这光明的细雨还是不住的下着……
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背负苍天,而莫之夭阏者;”那不容易见着。我们镇上东关厢外有一座黄泥山,山顶上有一座七层的塔,塔尖顶着天。塔院里常常打钟,钟声响动时,那在太阳西晒的时候多,一枝艳艳的大红花贴在西山的鬓边回照着塔山上的云彩,——钟声响动时,绕着塔顶尖,摩着塔顶天,穿着塔顶云,有一只两只,有时三只四只有时五只六只蜷着爪往地面瞧的“饿老鹰,”撑开了它们灰苍苍的大翅膀没挂恋似的在盘旋,在半空中浮着,在晚风中泅着,仿佛是按着塔院钟的波荡来练习圆舞似的。那是我做孩子时的“大鹏”。有时好天抬头不见一瓣云的时候听着猇忧忧的叫响,我们就知道那是宝塔上的饿老鹰寻食吃来了,这一想象半天里秃顶圆睛的英雄,我们背上的小翅膀骨上就仿佛豁出了一锉锉铁刷似的羽毛,摇起来呼呼响的,只一摆就冲出了书房门,钻入了玳瑁镶边的白云里玩儿去,谁耐烦站在先生书桌前晃着身子背早上上的多难背的书!啊飞!不是那在树枝上矮矮的跳着的麻雀儿的飞;不是那凑天黑从堂匾后背冲出来赶蚊子吃的蝙蝠的飞;也不是那软尾巴软嗓子做窠在堂檐上的燕子的飞。要飞就得满天飞,风拦不住云挡不住的飞,一翅膀就跳过一座山头,影子下来遮得阴二十亩稻田的飞,到天晚飞倦了就来绕着那塔顶尖顺着风向打圆圈做梦……听说饿老鹰会抓小鸡!
飞。人们原来都是会飞的。天使们有翅膀,会飞,我们初来时也有翅膀,会飞。我们最初来就是飞了来的,有的做完了事还是飞了去,他们是可羡慕的。但大多数人是忘了飞的,有的翅膀上掉了毛不长再也飞不起来,有的翅膀叫胶水给胶住了,再也拉不开,有的羽毛叫人给修短了像鸽子似的只会在地上跳,有的拿背上一对翅膀上当铺去典钱使过了期再也赎不回……真的,我们一过了做孩子的日子就掉了飞的本领。但没了翅膀或是翅膀坏了不能用是一件可怕的事。因为你再也飞不回去,你蹲在地上呆望着飞不上去的天,看旁人有福气的一程一程的在青云里逍遥,那多可怜。而且翅膀又不比是你脚上的鞋,穿烂了可以再问妈要一双去,翅膀可不成,折了一根毛就是一根,没法给补的。还有,单顾着你翅膀也还不定规到时候能飞,你这身子要是不谨慎养太肥了,翅膀力量小再也拖不起,也是一样难不是?一对小翅膀驮不起一个胖肚子,那情形多可笑!到时候你听人家高声的招呼说,朋友,回去吧,趁这天还有紫色的光,你听他们的翅膀在半空中沙沙的摇响,朵朵的春云跳过来拥着他们的肩背,望着最光明的来处翩翩的,冉冉的,轻烟似的化出了你的视域,像云雀似的只留下一泻光明的骤雨——“thou art unseen but yet i hear thy shrill delight”①——那你,独自在泥涂里淹着,够多难受,够多懊恼,够多寒伧!趁早留神你的翅膀,朋友?
是人没有不想飞的,老是在这地面上爬着够多厌烦,不说别的。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到云端里去,到云端里去!哪个心里不成天千百遍的这么想?飞上天空去浮着,看地球这弹丸在大空里滚着,从陆地看到海,从海再看回陆地。凌空去看一个明白——这才是做人的趣味,做人的权威,做人的交代。这皮囊要是太重挪不动,就掷了它,可能的话,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
人类初发明用石器的时候,已经想长翅膀。想飞。原人洞壁上画的四不像,它的背上掮着翅膀;拿着弓箭赶野兽的,他那肩背上也给安了翅膀。小爱神是有一对粉嫩的肉翅的。挨开拉斯②(icarus)是人类飞行史里第一个英雄,第一次牺牲。安琪儿(那是理想化的人)第一个标记是帮助他们飞行的翅膀。那也有沿革——你看西洋画上的表现。最初像是一对小精致的令旗,蝴蝶似的粘在安琪儿们的背上,像真的,不灵动的。渐渐的翅膀长大了,地位安准了,毛羽丰满了。画图上的天使们长上了真的可能的翅膀。人类初次实现了翅膀的观念,彻悟了飞行的意义。挨开拉斯闪不死的灵魂,回来投生又投生。人类最大的使命,是制造翅膀;最大的成功是飞!理想的极度,想象的止境,从人到神!诗是翅膀上出世的;哲理是在空中盘旋的。飞:超脱一切,笼盖一切,扫荡一切,吞吐一切。
你上那边山峰顶上试去,要是度不到这边山峰上,你就得到这万丈的深渊里去找你的葬身地!“这人形的鸟会有一天试他第一次的飞行,给这世界惊骇,使所有的著作赞美,给他所从来的栖息处永久的光荣。”啊 达文謇!
但是飞?自从挨开拉斯以来,人类的工作是制造翅膀,还是束缚翅膀?这翅膀,承上了文明的重量,还能飞吗?都是飞了来的,还都能飞了回去吗?钳住了,烙住了,压住了,——
这人形的鸟会有试他第一次飞行的一天吗?……
同时天上那一点子黑的已经迫近在我的头顶,形成了一架鸟形的机器,忽的机沿一侧,一球光直往下注,硼的一声炸响,——炸碎了我在飞行中的幻想,青天里平添了几堆破碎的浮云。
--------
①大意是“你无影无踪,但我仍听见你的尖声欢叫。”
②挨开拉斯,现通译伊卡罗斯,古希腊传说中能工巧匠代达洛斯(daedalus)的儿子。他们父子用蜂蜡粘贴羽毛做成双翼,腾空飞行。由于伊卡罗斯飞得太高,太阳把蜂蜡晒化,使他坠海而死。
【原文】
自 剖
徐志摩
我是个好动的人;每回我身体行动的时候,我的思想也仿佛就跟着跳荡。我做的诗,
不论它们是怎样的“无聊”,有不少是在行旅期中想起的。我爱动,爱看动的事物,爱
活泼的人,爱水,爱空中的飞鸟,爱车窗外掣过的田野山水。星光的闪动,草叶上露珠
的颤动,花须在微风中的摇动,雷雨时云空的变动,大海中波涛的汹涌,都是在在触动
我感兴的情景。是动,不论是什么性质,就是我的兴趣,我的灵感。是动就会催快我的
呼吸,加添我的生命。
近来却大大的变样了。第一我自身的肢体,已不如原先灵活;我的心也同样的感受
了不知是年岁还是什么的拘絷。动的现象再不能给我欢喜,给我启示。先前我看着在阳
光中闪烁的余波,就仿佛看见了神仙宫阙——什么荒诞美丽的幻觉,不在我的脑中一闪
闪的掠过;现在不同了,阳光只是阳光,流波只是流波,任凭景色怎样的灿烂,再也照
不化我的呆木的心灵。我的思想,如其偶尔有,也只似岩石上的藤萝,贴着枯干的粗糙
的石面,极困难的蜒着;颜色是苍黑的,姿态是崛强的。
我自己也不懂得何以这变迁来得这样的兀突,这样的深彻。
原先我在人前自觉竟是一注的流泉,在在有飞沫,在在有闪光;现在这泉眼,如其
还在,仿佛是叫一块石板不留余隙的给镇住了。我再没有先前那样蓬勃的情趣,每回我
想说话的时候,就觉着那石块的重压,怎么也掀不动,怎么也推不开,结果只能自安沉
默!“你再不用想什么了,你再没有什么可想的了”;“你再不用开口了,你再没有什
么话可说的了,”
我常觉得我沉闷的心府里有这样半嘲讽半吊唁的谆嘱。
说来我思想上或经验上也并不曾经受什么过分剧烈的戟刺。我处境是向来顺的,现
在如其有不同,只是更顺了的。那么为什么这变迁?远的不说,就比如我年前到欧洲去
时的心境:啊!我那时还不是一只初长毛角的野鹿?什么颜色不激动我的视觉,什么香
味不奋兴我的嗅觉?我记得我在意大利写游记的时候,情绪是何等的活泼,兴趣何等的
醇厚,一路来眼见耳听心感的种种,哪一样不活栩栩的业集在我的笔端,争求充分的表
现!如今呢?我这次到南方去,来回也有一个多月的光景,这期内眼见耳听心感的事物
也该有不少。我未动身前,又何尝不自喜此去又可以有机会饱餐西湖的风色,邓尉的梅
香——单提一两件最合我脾胃的事。有好多朋友也曾期望我在这闲暇的假期中采集一点
江南风趣,归来时,至少也该带回一两篇爽口的诗文,给在北京泥土的空气中活命的朋
友们一些清醒的消遣。但在事实上不但在南中时我白瞪着大眼,看天亮换天昏,又闭上
了眼,拼天昏换天亮,一枝秃笔跟着我涉海去,又跟着我涉海回来,正如岩洞里的一根
石笋,压根儿就没一点摇动的消息;就在我回京后这十来天,任凭朋友们怎样的催促,
自己良心怎样的责备,我的笔尖上还是滴不出一点墨沈来。我也曾勉强想想,勉强想写,
但到底还是白费!可怕是这心灵骤然的呆顿。完全死了不成?我自己在疑惑。
说来是时局也许有关系。我到京几天就逢着空前的血案。五卅事件发生时我正在意
大利山中,采茉莉花编花篮儿玩,翡冷翠①山中只见明星与流萤的交唤,花香与山色的
温存,俗氛是吹不到的。直到七月间到了伦敦,我才理会国内风光的惨淡,等得我赶回
来时,设想中的激昂,又早变成了明日黄花,看得见的痕迹只有满城黄墙上墨彩斑斓的
“泣告”。
这回却不同。屠杀的事实不仅是在我住的城子里发见,我有时竟觉得是我自己的灵
府里的一个惨象。杀死的不仅是青年们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仿佛遭着了致命的打击,
比是国务院前的断脰残肢,再也不能回复生动与连贯。但这深刻的难受在我是无名的,
是不能完全解释的。这回事变的奇惨性引起愤慨与悲切是一件事,但同时我们也知道在
这根本起变态作用的社会里,什么怪诞的情形都是可能的。屠杀无辜,还不是年来最平
常的现象。自从内战纠结以来,在受战祸的区域内,哪一处村落不曾分到过遭奸污的女
性,屠残的骨肉,供牺牲的生命财产?这无非是给冤氛团结的地面上多添一团更集中更
鲜艳的怨毒。再说哪一个民族的解放史能不浓浓的染着Martyrs②的腔血?俄国革命的开
幕就是二十年前冬宫的血景。只要我们有识力认定,有胆量实行,我们理想中的革命,
这回羔羊的血就不会是白涂的。所以我个人的沉闷决不完全是这回惨案引起的感情作用。
爱和平是我的生性。在怨毒、猜忌、残杀的空气中,我的神经每每感受一种不可名
状的压迫。记得前年奉直战争时我过的那日子简直是一团黑漆,每晚更深时,独自抱着
脑壳伏在书桌上受罪,仿佛整个时代的沉闷盖在我的头顶——直到写下了“毒药”那几
首不成形的咒诅诗以后,我心头的紧张才渐渐的缓和下去。这回又有同样的情形;只觉
着烦,只觉着闷,感想来时只是破碎,笔头只是笨滞。结果身体也不舒畅,像是蜡油涂
抹住了全身毛窍似的难过,一天过去了又是一天,我这里又在重演更深独坐箍紧脑壳的
姿势,窗外皎洁的月光,分明是在嘲讽我内心的枯窘!
不,我还得往更深处挖。我不能叫这时局来替我思想骤然的呆顿负责,我得往我自
己生活的底里找去。
平常有几种原因可以影响我们的心灵活动。实际生活的牵掣可以劫去我们心灵所需
要的闲暇,积成一种压迫。在某种热烈的想望不曾得满足时,我们感觉精神上的烦闷与
焦躁,失望更是颠覆内心平衡的一个大原因;较剧烈的种类可以麻痹我们的灵智,淹没
我们的理性。但这些都合不上我的病源;因为我在实际生活里已经得到十分的幸运,我
的潜在意识里,我敢说不该有什么压着的欲望在作怪。
但是在实际上反过来看另有一种情形可以阻塞或是减少你心灵的活动。我们知道舒
服、健康、幸福,是人生的目标,我们因此推想我们痛苦的起点是在望见那些目标而得
不到的时候。我们常听人说“假如我像某人那样生活无忧我一定可以好好的做事,不比
现在整天的精神全花在琐碎的烦恼上。”我们又听说“我不能做事就为身体太坏,若是
精神来得,那就……”我们又常常设想幸福的境界,我们想“只要有一个意中人在跟前
那我一定奋发,什么事做不到?”但是不,在事实上,舒服、健康、幸福,不但不一定
是帮助或奖励心灵生活的条件,它们有时正得相反的效果。我们看不起有钱人,在社会
上得意人,肌肉过分发展的运动家,也正在此;至于年少人幻想中的美满幸福,我敢说
等得当真有了红袖添香,你的书也就读不出所以然来,且不说什么在学问上或艺术上更
认真的工作。
那末生活的满足是我的病源吗?
“在先前的日子”,一个真知我的朋友,就说:“正为是你生活不得平衡,正为你
有欲望不得满足,你的压在内里的Libido③就形成一种升华的现象,结果你就借文学来
发泄你生理上的郁结(你不常说你从事文学是一件不预期的事吗?)这情形又容易在你
的意识里形成一种虚幻的希望,因为你的写作得到一部分赞许,你就自以为确有相当创
作的天赋以及独立思想的能力。但你只是自冤自,实在你并没有什么超人一等的天赋,
你的设想多半是虚荣,你的以前的成绩只是升华的结果。所以现在等得你生活换了样,
感情上有了安顿,你就发见你向来写作的来源顿呈萎缩甚至枯竭的现象;而你又不愿意
承认这情形的实在,妄想到你身子以外去找你思想枯窘的原因,所以你就不由的感到深
刻的烦闷。你只是对你自己生气,不甘心承认你自己的本相。不,你原来并没有三头六
臂的!
“你对文艺并没有真兴趣,对学问并没有真热心。你本来没有什么更高的志愿,除
了相当合理的生活,你只配安分做一个平常人,享你命里铸定的‘幸福’;在事业界,
在文艺创作界,在学问界内,全没有你的位置,你真的没有那能耐。不信你只要自问在
你心里的心里有没有那无形的‘推力’,整天整夜的恼着你,逼着你,督着你,放开实
际生活的全部,单望着不可捉模的创作境界里去冒险?是的,顶明显的关键就是那无形
的推力或是冲动(The Impulse),没有它人类就没有科学,没有文学,没有艺术,没
有一切超越功利实用性质的创作。你知道在国外(国内当然也有,许没那样多)有多少
人被这无形的推力驱使着,在实际生活上变成一种离魂病性质的变态动物,不但人间所
有的虚荣永远沾不上他们的思想,就连维持生命的睡眠饮食,在他们都失了重要,他们
全部的心力只是在他们那无形的推力所指示的特殊方向上集中应用。怪不得有人说天才
是疯癫;我们在巴黎、伦敦不就到处碰得着这类怪人?如其他是一个美术家,恼着他的
就只怎样可以完全表现他那理想中的形体;一个线条的准确,某种色彩的调谐,在他会
得比他生身父母的生死与国家的存亡更重要,更迫切,更要求注意。我们知道专门学者
有终身掘坟墓的,研究蚊虫生理的,观察亿万万里外一个星的动定的。并且他们决不问
社会对于他们的劳力有否任何的认识,那就是虚荣的进路;他们是被一点无形的推力的
魔鬼盅定了的。
“这是关于文艺创作的话。你自问有没有这种情形。你也许经验过什么‘灵感’,
那也许有,但你却不要把刹那误认作永久的,虚幻认作真实。至于说思想与真实学问的
话,那也得背后有一种推力,方向许不同,性质还是不变。做学问你得有原动的好奇心,
得有天然热情的态度去做求知识的工夫。真思想家的准备,除了特强的理智,还得有一
种原动的信仰;信仰或寻求信仰,是一切思想的出发点:极端的怀疑派思想也只是期望
重新位置信仰的一种努力。从古来没有一个思想家不是宗教性的。在他们,各按各的倾
向,一切人生的和理智的问题是实在有的;神的有无,善与恶,本体问题,认识问题,
意志自由问题,在他们看来都是含逼迫性的现象,要求合理的解答——比山岭的崇高,
水的流动,爱的甜蜜更真,更实在,更耸动。他们的一点心灵,就永远在他们设想的一
种或多种问题的周围飞舞、旋绕,正如灯蛾之于火焰:牺牲自身来贯彻火焰中心的秘密,
是他们共有的决心。
“这种惨烈的情形,你怕也没有吧?我不说你的心幕上就没有思想的影子;但它们
怕只是虚影,像水面上的云影,云过影子就跟着消散,不是石上的溜痕越日久越深刻。
“这样说下来,你倒可以安心了!因为个人最大的悲剧是设想一个虚无的境界来谎
骗你自己;骗不到底的时候你就得忍受‘幻灭’的莫大的苦痛。与其那样,还不如及早
认清自己的深浅,不要把不必要的负担,放上支撑不住的肩背,压坏你自己,还难免旁
人的笑话!朋友,不要迷了,定下心来享你现成的福分吧;思想不是你的分,文艺创作
不是你的分,独立的事业更不是你的分!天生抗了重担来的那也没法想(哪一个天才不
是活受罪!)你是原来轻松的,这是多可羡慕,多可贺喜的一个发见!算了吧,朋友!”
三月二十五至四月一日
① 翡冷翠,通译佛罗伦萨。
② Martyrs,英文“殉难者”、“烈士”。
③ Libilo,通译里比多,心理学名词。
《自剖》
我是个好动的人;每回我身体行动的时候,我的思想也仿佛就跟着跳
荡。我做的诗,不论它们是怎样的“无聊”,有不少是在行旅期中想起的。
我爱动,爱看动的事物,爱活泼的人,爱水,爱空中的飞鸟,爱车窗外
掣过的田野山水。星光的闪动,草叶上露珠的颤动,花须在微风中的摇
动,雷雨时云空的变动,大海中波涛的汹涌,都是在在触动我感兴的情
景。是动,不论是什么性质,就是我的兴趣,我的灵感。是动就会催快
我的呼吸,加添我的生命。
近来却大大的变样了。第一我自身的肢体,已不如原先灵活;我的
心也同样的感受了不知是年岁还是什么的拘絷。动的现象再不能给我欢
喜,给我启示。先前我看着在阳光中闪烁的余波,就仿佛看见了神仙宫
阙——什么荒诞美丽的幻觉,不在我的脑中一闪闪的掠过;现在不同了
,阳光只是阳光,流波只是流波,任凭景色怎样的灿烂,再也照不化我
的呆木的心灵。我的思想,如其偶尔有,也只似岩石上的藤萝,贴着枯
干的粗糙的石面,极困难的蜒着;颜色是苍黑的,姿态是崛强的。
我自己也不懂得何以这变迁来得这样的兀突,这样的深彻。
原先我在人前自觉竟是一注的流泉,在在有飞沫,在在有闪光;现
在这泉眼,如其还在,仿佛是叫一块石板不留余隙的给镇住了。我再没
有先前那样蓬勃的情趣,每回我想说话的时候,就觉着那石块的重压,
怎么也掀不动,怎么也推不开,结果只能自安沉默!“你再不用想什么
了,你再没有什么可想的了”;“你再不用开口了,你再没有什么话可
说的了,”
我常觉得我沉闷的心府里有这样半嘲讽半吊唁的谆嘱。
说来我思想上或经验上也并不曾经受什么过分剧烈的戟刺。我处境
是向来顺的,现在如其有不同,只是更顺了的。那么为什么这变迁?远
的不说,就比如我年前到欧洲去时的心境:啊!我那时还不是一只初长
毛角的野鹿?什么颜色不激动我的视觉,什么香味不奋兴我的嗅觉?我
记得我在意大利写游记的时候,情绪是何等的活泼,兴趣何等的醇厚,
一路来眼见耳听心感的种种,哪一样不活栩栩的业集在我的笔端,争求
充分的表现!如今呢?我这次到南方去,来回也有一个多月的光景,这
期内眼见耳听心感的事物也该有不少。我未动身前,又何尝不自喜此去
又可以有机会饱餐西湖的风色,邓尉的梅香——单提一两件最合我脾胃
的事。有好多朋友也曾期望我在这闲暇的假期中采集一点江南风趣,归
来时,至少也该带回一两篇爽口的诗文,给在北京泥土的空气中活命的
朋友们一些清醒的消遣。但在事实上不但在南中时我白瞪着大眼,看天
亮换天昏,又闭上了眼,拼天昏换天亮,一枝秃笔跟着我涉海去,又跟
着我涉海回来,正如岩洞里的一根石笋,压根儿就没一点摇动的消息;
就在我回京后这十来天,任凭朋友们怎样的催促,自己良心怎样的责备
,我的笔尖上还是滴不出一点墨沈来。我也曾勉强想想,勉强想写,但
到底还是白费!可怕是这心灵骤然的呆顿。完全死了不成?我自己在疑
惑。
说来是时局也许有关系。我到京几天就逢着空前的血案。五卅事件
发生时我正在意大利山中,采茉莉花编花篮儿玩,翡冷翠①山中只见明
星与流萤的交唤,花香与山色的温存,俗氛是吹不到的。直到七月间到
了伦敦,我才理会国内风光的惨淡,等得我赶回来时,设想中的激昂,
又早变成了明日黄花,看得见的痕迹只有满城黄墙上墨彩斑斓的“泣告”
。
这回却不同。屠杀的事实不仅是在我住的城子里发见,我有时竟觉
得是我自己的灵府里的一个惨象。杀死的不仅是青年们的生命,我自己
的思想也仿佛遭着了致命的打击,比是国务院前的断脰残肢,再也不能
回复生动与连贯。但这深刻的难受在我是无名的,是不能完全解释的。
这回事变的奇惨性引起愤慨与悲切是一件事,但同时我们也知道在这根
本起变态作用的社会里,什么怪诞的情形都是可能的。屠杀无辜,还不
是年来最平常的现象。自从内战纠结以来,在受战祸的区域内,哪一处
村落不曾分到过遭奸污的女性,屠残的骨肉,供牺牲的生命财产?这无
非是给冤氛团结的地面上多添一团更集中更鲜艳的怨毒。再说哪一个民
族的解放史能不浓浓的染着martyrs②的腔血?俄国革命的开幕就是二十
年前冬宫的血景。只要我们有识力认定,有胆量实行,我们理想中的革
命,这回羔羊的血就不会是白涂的。所以我个人的沉闷决不完全是这回
惨案引起的感情作用。
--------
①翡冷翠,通译佛罗伦萨。
②martyrs,英文“殉难者”、“烈士”(加s为复数)。
爱和平是我的生性。在怨毒、猜忌、残杀的空气中,我的神经每每
感受一种不可名状的压迫。记得前年奉直战争时我过的那日子简直是一
团黑漆,每晚更深时,独自抱着脑壳伏在书桌上受罪,仿佛整个时代的
沉闷盖在我的头顶——直到写下了“毒药”那几首不成形的咒诅诗以后,
我心头的紧张才渐渐的缓和下去。这回又有同样的情形;只觉着烦,只
觉着闷,感想来时只是破碎,笔头只是笨滞。结果身体也不舒畅,像是
蜡油涂抹住了全身毛窍似的难过,一天过去了又是一天,我这里又在重
演更深独坐箍紧脑壳的姿势,窗外皎洁的月光,分明是在嘲讽我内心的
枯窘!
不,我还得往更深处挖。我不能叫这时局来替我思想骤然的呆顿负
责,我得往我自己生活的底里找去。
平常有几种原因可以影响我们的心灵活动。实际生活的牵掣可以劫
去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闲暇,积成一种压迫。在某种热烈的想望不曾得满
足时,我们感觉精神上的烦闷与焦躁,失望
更是颠覆内心平衡的一个大原因;较剧烈的种类可以麻痹我们的灵智,
淹没我们的理性。但这些都合不上我的病源;因为我在实际生活里已经
得到十分的幸运,我的潜在意识里,我敢说不该有什么压着的欲望在作
怪。
但是在实际上反过来看另有一种情形可以阻塞或是减少你心灵的活
动。我们知道舒服、健康、幸福,是人生的目标,我们因此推想我们痛
苦的起点是在望见那些目标而得不到的时候。我们常听人说“假如我像
某人那样生活无忧我一定可以好好的做事,不比现在整天的精神全花在
琐碎的烦恼上。”我们又听说“我不能做事就为身体太坏,若是精神来
得,那就……”我们又常常设想幸福的境界,我们想“只要有一个意中
人在跟前那我一定奋发,什么事做不到?”但是不,在事实上,舒服、
健康、幸福,不但不一定是帮助或奖励心灵生活的条件,它们有时正得
相反的效果。我们看不起有钱人,在社会上得意人,肌肉过分发展的运
动家,也正在此;至于年少人幻想中的美满幸福,我敢说等得当真有了
红袖添香,你的书也就读不出所以然来,且不说什么在学问上或艺术上
更认真的工作。
那末生活的满足是我的病源吗?
“在先前的日子”,一个真知我的朋友,就说:“正为是你生活不
得平衡,正为你有欲望不得满足,你的压在内里的licbido①就形成一种
升华的现象,结果你就借文学来发泄你生理上的郁结(你不常说你从事
文学是一件不预期的事吗?)这情形又容易在你的意识里形成一种虚幻
的希望,因为你的写作得到一部分赞许,你就自以为确有相当创作的天
赋以及独立思想的能力。但你只是自冤自,实在你并没有什么超人一等
的天赋,你的设想多半是虚荣,你的以前的成绩只是升华的结果。所以
现在等得你生活换了样,感情上有了安顿,你就发见你向来写作的来源
顿呈萎缩甚至枯竭的现象;而你又不愿意承认这情形的实在,妄想到你
身子以外去找你思想枯窘的原因,所以你就不由的感到深刻的烦闷。你
只是对你自己生气,不甘心承认你自己的本相。不,你原来并没有三头
六臂的!
①libilo,通译里比多,心理学名词。
“你对文艺并没有真兴趣,对学问并没有真热心。你本来没有什么
更高的志愿,除了相当合理的生活,你只配安分做一个平常人,享你命
里铸定的‘幸福’;在事业界,在文艺创作界,在学问界内,全没有你
的位置,你真的没有那能耐。不信你只要自问在你心里的心里有没有那
无形的‘推力’,整天整夜的恼着你,逼着你,督着你,放开实际生活
的全部,单望着不可捉模的创作境界里去冒险?是的,顶明显的关键就
是那无形的推力或是冲动(the impulse),没有它人类就没有科学,
没有文学,没有艺术,没有一切超越功利实用性质的创作。你知道在国
外(国内当然也有,许没那样多)有多少人被这无形的推力驱使着,在
实际生活上变成一种离魂病性质的变态动物,不但人间所有的虚荣永远
沾不上他们的思想,就连维持生命的睡眠饮食,在他们都失了重要,他
们全部的心力只是在他们那无形的推力所指示的特殊方向上集中应用。
怪不得有人说天才是疯癫;我们在巴黎、伦敦不就到处碰得着这类怪人?
如其他是一个美术家,恼着他的就只怎样可以完全表现他那理想中的形
体;一个线条的准确,某种色彩的调谐,在他会得比他生身父母的生死
与国家的存亡更重要,更迫切,更要求注意。我们知道专门学者有终身
掘坟墓的,研究蚊虫生理的,观察亿万万里外一个星的动定的。并且他
们决不问社会对于他们的劳力有否任何的认识,那就是虚荣的进路;他
们是被一点无形的推力的魔鬼盅定了的。
“这是关于文艺创作的话。你自问有没有这种情形。你也许经验过
什么‘灵感’,那也许有,但你却不要把刹那误认作永久的,虚幻认作
真实。至于说思想与真实学问的话,那也得背后有一种推力,方向许不
同,性质还是不变。做学问你得有原动的好奇心,得有天然热情的态度
去做求知识的工夫。真思想家的准备,除了特强的理智,还得有一种原
动的信仰;信仰或寻求信仰,是一切思想的出发点:极端的怀疑派思想
也只是期望重新位置信仰的一种努力。从古来没有一个思想家不是宗教
性的。在他们,各按各的倾向,一切人生的和理智的问题是实在有的;
神的有无,善与恶,本体问题,认识问题,意志自由问题,在他们看来
都是含逼迫性的现象,要求合理的解答——比山岭的崇高,水的流动,
爱的甜蜜更真,更实在,更耸动。他们的一点心灵,就永远在他们设想
的一种或多种问题的周围飞舞、旋绕,正如灯蛾之于火焰:牺牲自身来
贯彻火焰中心的秘密,是他们共有的决心。
“这种惨烈的情形,你怕也没有吧?我不说你的心幕上就没有思想
的影子;但它们怕只是虚影,像水面上的云影,云过影子就跟着消散,
不是石上的溜痕越日久越深刻。
“这样说下来,你倒可以安心了!因为个人最大的悲剧是设想一个
虚无的境界来谎骗你自己;骗不到底的时候你就得忍受‘幻灭’的莫大
的苦痛。与其那样,还不如及早认清自己的深浅,不要把不必要的负担,
放上支撑不住的肩背,压坏你自己,还难免旁人的笑话!朋友,不要迷
了,定下心来享你现成的福分吧;思想不是你的分,文艺创作不是你的
分,独立的事业更不是你的分!天生抗了重担来的那也没法想(哪一个
天才不是活受罪!)你是原来轻松的,这是多可羡慕,多可贺喜的一个
发见!算了吧,朋友!”
三月二十五至四月一日
-------------------------------------------------------------------
《想飞》
假如这时候窗子外有雪——街上,城墙上,屋脊上,都是雪,胡同口一家屋檐下偎着一个戴黑兜帽的巡警,半拢着睡眼,看棉团似的雪花在半空中跳着玩……假如这夜是一个深极了的啊,不是壁上挂钟的时针指示给我们看的深夜,这深就比是一个山洞的深,一个往下钻螺旋形的山洞的深……
假如我能有这样一个深夜,它那无底的阴森捻起我遍体的毫管;再能有窗子外不住往下筛的雪,筛淡了远近间飏动的市谣;筛泯了在泥道上挣扎的车轮;筛灭了脑壳中不妥协的潜流……
我要那深,我要那静。那在树荫浓密处躲着的夜鹰,轻易不敢在天光还在照亮时出来睁眼。思想:它也得等。
青天里有一点子黑的。正冲着太阳耀眼,望不真,你把手遮着眼,对着那两株树缝里瞧,黑的,有榧子来大,不,有桃子来大——嘿,又移着往西了!
我们吃了中饭出来到海边去。(这是英国康槐尔极南的一角,三面是大西洋)。勖丽丽的叫响从我们的脚底下匀匀的往上颤,齐着腰,到了肩高,过了头顶,高入了云,高出了云。啊!你能不能把一种急震的乐音想象成一阵光明的细雨,从蓝天里冲着这平铺着青绿的地面不住的下?不,那雨点都是跳舞的小脚,安琪儿的。云雀们也吃过了饭,离开了它们卑微的地巢飞往高处做工去。上帝给它们的工作,替上帝做的工作。瞧着,这儿一只,那边又起了两!一起就冲着天顶飞,小翅膀活动的多快活,圆圆的,不踌躇的飞,——它们就认识青天。一起就开口唱,小嗓子活动的多快活,一颗颗小精圆珠子直往外唾,亮亮的唾,脆脆的唾,——它们赞美的是青天。瞧着,这飞得多高,有豆子大,有芝麻大,黑刺刺的一屑,直顶着无底的天顶细细的摇,——这全
看不见了,影子都没了!但这光明的细雨还是不住的下着……
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背负苍天,而莫之夭阏者;”那不容易见着。我们镇上东关厢外有一座黄泥山,山顶上有一座七层的塔,塔尖顶着天。塔院里常常打钟,钟声响动时,那在太阳西晒的时候多,一枝艳艳的大红花贴在西山的鬓边回照着塔山上的云彩,——钟声响动时,绕着塔顶尖,摩着塔顶天,穿着塔顶云,有一只两只,有时三只四只有时五只六只蜷着爪往地面瞧的“饿老鹰,”撑开了它们灰苍苍的大翅膀没挂恋似的在盘旋,在半空中浮着,在晚风中泅着,仿佛是按着塔院钟的波荡来练习圆舞似的。那是我做孩子时的“大鹏”。有时好天抬头不见一瓣云的时候听着猇忧忧的叫响,我们就知道那是宝塔上的饿老鹰寻食吃来了,这一想象半天里秃顶圆睛的英雄,我们背上的小翅膀骨上就仿佛豁出了一锉锉铁刷似的羽毛,摇起来呼呼响的,只一摆就冲出了书房门,钻入了玳瑁镶边的白云里玩儿去,谁耐烦站在先生书桌前晃着身子背早上上的多难背的书!啊飞!不是那在树枝上矮矮的跳着的麻雀儿的飞;不是那凑天黑从堂匾后背冲出来赶蚊子吃的蝙蝠的飞;也不是那软尾巴软嗓子做窠在堂檐上的燕子的飞。要飞就得满天飞,风拦不住云挡不住的飞,一翅膀就跳过一座山头,影子下来遮得阴二十亩稻田的飞,到天晚飞倦了就来绕着那塔顶尖顺着风向打圆圈做梦……听说饿老鹰会抓小鸡!
飞。人们原来都是会飞的。天使们有翅膀,会飞,我们初来时也有翅膀,会飞。我们最初来就是飞了来的,有的做完了事还是飞了去,他们是可羡慕的。但大多数人是忘了飞的,有的翅膀上掉了毛不长再也飞不起来,有的翅膀叫胶水给胶住了,再也拉不开,有的羽毛叫人给修短了像鸽子似的只会在地上跳,有的拿背上一对翅膀上当铺去典钱使过了期再也赎不回……真的,我们一过了做孩子的日子就掉了飞的本领。但没了翅膀或是翅膀坏了不能用是一件可怕的事。因为你再也飞不回去,你蹲在地上呆望着飞不上去的天,看旁人有福气的一程一程的在青云里逍遥,那多可怜。而且翅膀又不比是你脚上的鞋,穿烂了可以再问妈要一双去,翅膀可不成,折了一根毛就是一根,没法给补的。还有,单顾着你翅膀也还不定规到时候能飞,你这身子要是不谨慎养太肥了,翅膀力量小再也拖不起,也是一样难不是?一对小翅膀驮不起一个胖肚子,那情形多可笑!到时候你听人家高声的招呼说,朋友,回去吧,趁这天还有紫色的光,你听他们的翅膀在半空中沙沙的摇响,朵朵的春云跳过来拥着他们的肩背,望着最光明的来处翩翩的,冉冉的,轻烟似的化出了你的视域,像云雀似的只留下一泻光明的骤雨“——Thou art unseen but yet I hear thy shrill delight”①——那你,独自在泥涂里淹着,够多难受,够多懊恼,够多寒伧!趁早留神你的翅膀,朋友?
是人没有不想飞的,老是在这地面上爬着够多厌烦,不说别的。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到云端里去,到云端里去!哪个心里不成天千百遍的这么想?飞上天空去浮着,看地球这弹丸在大空里滚着,从陆地看到海,从海再看回陆地。凌空去看一个明白——这才是做人的趣味,做人的权威,做人的交代。这皮囊要是太重挪不动,就掷了它,可能的话,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
人类初发明用石器的时候,已经想长翅膀。想飞。原人洞壁上画的四不像,它的背上掮着翅膀;拿着弓箭赶野兽的,他那肩背上也给安了翅膀。小爱神是有一对粉嫩的肉翅的。挨开拉斯②(Icarus)是人类飞行史里第一个英雄,第一次牺牲。安琪儿(那是理想化的人)第一个标记是帮助他们飞行的翅膀。那也有沿革——你看西洋画上的表现。最初像是一对小精致的令旗,蝴蝶似的粘在安琪儿们的背上,像真的,不灵动的。渐渐的翅膀长大了,地位安准了,毛羽丰满了。画图上的天使们长上了真的可能的翅膀。人类初次实现了翅膀的观念,彻悟了飞行的意义。挨开拉斯闪不死的灵魂,回来投生又投生。人类最大的使命,是制造翅膀;最大的成功是飞!理想的极度,想象的止境,从人到神!诗是翅膀上出世的;哲理是在空中盘旋的。飞:超脱一切,笼盖一切,扫荡一切,吞吐一切。
你上那边山峰顶上试去,要是度不到这边山峰上,你就得到这万丈的深渊里去找你 的葬身地!“这人形的鸟会有一天试他第一次的飞行,给这世界惊骇,使所有的著作赞 美,给他所从来的栖息处永久的光荣。”啊达文謇!
但是飞?自从挨开拉斯以来,人类的工作是制造翅膀,还是束缚翅膀?这翅膀,承 上了文明的重量,还能飞吗?都是飞了来的,还都能飞了回去吗?钳住了,烙住了,压 住了,—— 这人形的鸟会有试他第一次飞行的一天吗?…… 同时天上那一点子黑的已经迫近在我的头顶,形成了一架鸟形的机器,忽的机沿一 侧,一球光直往下注,硼的一声炸响,——炸碎了我在飞行中的幻想,青天里平添了几 堆破碎的浮云。
①大意是“你无影无踪,但我仍听见你的尖声欢叫。”
②挨开拉斯,现通译伊卡罗斯,古希腊传说中能工巧匠代达洛斯(Daedalus)的儿
子。他们父子用蜂蜡粘贴羽毛做成双翼,腾空飞行。由于伊卡罗斯飞得太高,太阳把蜂
蜡晒化,使他坠海而死。
绛旓細濉旈櫌閲屽父甯告墦閽,閽熷0鍝嶅姩鏃,閭e湪澶槼瑗挎檼鐨勬椂鍊欏,涓鏋濊壋鑹崇殑澶х孩鑺辫创鍦ㄨタ灞辩殑楝撹竟鍥炵収鐫濉斿北涓婄殑浜戝僵,鈥斺旈挓澹板搷鍔ㄦ椂,缁曠潃濉旈《灏,鎽╃潃濉旈《澶,绌跨潃濉旈《浜,鏈変竴鍙袱鍙,鏈夋椂涓夊彧鍥涘彧鏈夋椂浜斿彧鍏彧铚风潃鐖線鍦伴潰鐬х殑鈥滈タ鑰侀拱,鈥濇拺寮浜嗗畠浠伆鑻嶈媿鐨勫ぇ缈呰唨娌℃寕鎭嬩技鐨勫湪鐩樻棆,鍦ㄥ崐绌轰腑娴潃,鍦ㄦ櫄椋庝腑娉呯潃,浠夸經鏄...
绛旓細3,寰愬織鎽╄瘲姝岀殑鍙h鑹烘湳 杩愮敤鍙h鑹烘湳杩欏湪寰愬織鎽╁叏閮ㄨ瘲浣滀腑鏄浉褰撶獊鍑虹殑,浣滀负涓涓姃鎯呮ф瀬寮虹殑璇椾汉,鑷繁鏈夋剰璇嗗湴鍦ㄨ瘲涓噰鐢ㄥ彛璇浐鐒舵湁鏃朵唬鐨勮儗鏅湪閲屽叧(濡傜櫧璇濇枃杩愬姩,寰愬織鎽╁姣斾笉閬椾綑鍔),浣嗚嚦灏戜篃璇存槑浠栨湁鎰忚瘑鍦版嫇瀹借嚜宸辩殑鑹烘湳鍒涗綔绌洪棿,濡傘婄伀杞︽搾浣忚建銆嬮噷"杩欐佸害涓嶉敊,鎰佹病涓簳"绾啛鏄彛璇叆璇,"杩欎笘鐣屽弽姝f槸...
绛旓細鍏堟皯璋佷笉姝汇傜煡鍛藉浣曞咖銆備簩楂樻爲澶氭偛椋庛傛捣姘存壃鍏舵尝銆傚埄鍓戜笉鍦ㄦ帉銆傜粨鍙嬩綍椤诲銆備笉瑙佺闂撮泙銆傝楣炶嚜鎶曠綏銆傜綏瀹跺緱闆鍠溿傚皯骞磋闆鎮层傛嫈鍓戞崕缃楃綉銆傞粍闆寰楅椋炪傞椋炴懇鑻嶅ぉ銆傛潵涓嬭阿灏戝勾銆 闂ㄦ湁涓囬噷瀹 闂ㄦ湁涓囬噷瀹傞棶鍚涗綍涔′汉銆傝ぐ瑁宠捣浠庝箣銆傛灉寰楀績鎵浜层傛尳瑁冲鎴戞常銆傚お鎭墠鑷檲銆傛湰鏄湐鏂瑰+銆備粖涓哄惔瓒婃皯...
绛旓細鏄殑銆傜涓鍙ャ婅禒鐧介┈鐜嬪姜銆嬩腑鐨勫彞銆傝禒鐧介┈鐜嬪姜 浣滆: 鏇规 搴忔洶锛氶粍鍒濆洓骞翠簲鏈堬紝鐧介┈鐜嬨佷换鍩庣帇涓庝綑淇辨湞浜笀锛屼細鑺傛皵銆傚埌娲涢槼锛屼换鍩庣帇钖ㄣ傝嚦涓冩湀涓庣櫧椹帇杩樺浗銆傚悗鏈夊徃浠ヤ簩鐜嬪綊钘╋紝閬撹矾瀹滃紓瀹挎銆傛剰姣掓仺涔嬨傜洊浠ュぇ鍒湪鏁版棩锛屾槸鐢ㄨ嚜鍓栵紝涓庣帇杈炵剦銆傛劋鑰屾垚绡囥傝皰甯濇壙鏄庡簮锛岄濆皢褰掓棫鐤嗐傛竻鏅...
绛旓細浠栫殑鏁f枃涔熻嚜鎴愪竴鏍,鍙栧緱浜嗕笉浜氫簬璇楁瓕鐨勬垚灏,鍏朵腑銆婅嚜鍓栥嬨併婃兂椋炪嬨併婃垜鎵鐭ラ亾鐨勫悍妗ャ嬨併婄俊鍐风繝灞卞眳闂茶瘽銆嬬瓑閮芥槸浼犱笘鐨勫悕绡囥 寰愬織鎽 1915骞存瘯涓氫簬鏉窞涓涓,鍏堝悗灏辫浜庝笂娴锋勃姹熷ぇ瀛︺佸ぉ娲ュ寳娲嬪ぇ瀛﹀拰鍖椾含澶у銆1918骞磋荡缇庡浗瀛︿範閾惰瀛︺1921骞磋荡鑻卞浗鐣欏,鍏ヤ鸡鏁﹀墤妗ュぇ瀛﹀綋鐗瑰埆鐢,鐮旂┒鏀挎不缁忔祹瀛︺傚湪鍓戞ˉ涓ゅ勾...
绛旓細鎰忔濇槸澶т笀澶織鍦ㄥ洓娴凤紝鍗充娇鐩搁殧涓囬噷涔熷ソ鍍忓氨鍦ㄨ韩杈逛竴鏍枫傚嚭鑷婅禒鐧介┈鐜嬪姜路骞跺簭銆鍏跺叚锛鍘熻瘲濡備笅锛氬績鎮插姩鎴戠锛屽純缃帿澶嶉檲銆備笀澶織鍥涙捣锛屼竾閲岀姽姣旈偦銆傛仼鐖辫嫙涓嶄簭锛屽湪杩滃垎鏃ヤ翰銆備綍蹇呭悓琛惧副锛岀劧鍚庡睍娈峰嫟銆傚咖鎬濇垚鐤剧枹锛屾棤涔冨効濂充粊銆備粨鍗掗鑲夋儏锛岃兘涓嶆鑻﹁緵锛熻瘧鏂囷細蹇冨鐨勬偛浼よЕ鍔ㄤ簡鎴戠殑褰㈢锛屾湜寮冪疆涓...
绛旓細鍘熻瘲锛氶潤濂冲叾濮濓紝淇熸垜浜庡煄闅呫傜埍鑰屼笉瑙侊紝鎼旈韪熻拱銆傞潤濂冲叾濞堬紝璐绘垜褰ょ銆傚饯绠℃湁鐐滐紝璇存垮コ缇庛傝嚜鐗у綊鑽戯紝娲电編涓斿紓銆傚尓濂充箣涓虹編锛岀編浜轰箣璐汇傝瘧鏂囷細濞撮潤濮戝鐪熸紓浜紝绾︽垜绛夊湪鍩庤鏃併傝绾块伄钄界湅涓嶈锛屾悢澶村緲寰婂績绱у紶銆傚ù闈欏濞樼湡濞囪壋锛岄佹垜涓鏋濈孩褰ょ銆傞矞绾㈠饯绠℃湁鍏夊僵锛岀埍瀹冮鑹茬湡椴滆壋銆傝繙鑷...
绛旓細瀹腑涔嬩汉,浜庡叾濮嬭嚦,瑙佸叾鏈夊菇闂茶礊闈欎箣寰,鏁呬綔鏄瘲銆傝█褰煎叧鍏崇劧涔嬮泿楦,鍒欑浉涓庡拰楦d簬娌虫床涔嬩笂鐭c傛绐堢獣涔嬫窇濂,鍒欏矀闈炲悰瀛愪箣鍠勫尮涔?瑷鍏剁浉涓庡拰涔愯屾伃鏁,浜﹁嫢闆庨笭涔嬫儏鎸氳屾湁鍒篃銆傗濇湵鐔逛互娣戝コ鎸囨枃鐜嬩箣濡冨お濮,璁や负銆婂叧闆庛嬫槸瀹腑涔嬩汉棰傜編濂瑰拰鏂囩帇鐩镐笌鍜屼箰鑰屾伃鏁殑鍏崇郴,杩欎笌姣涜瘲鐨勮娉曞ぇ鍚屽皬寮,浠嶇劧鏄竴鑴夌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