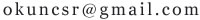长妈妈是谁?
长妈妈,也叫做阿长,是鲁迅的保姆。鲁迅写了一篇文章纪念她。长妈妈,已经说过,是一个一向带领着我的女工,说得阔气一点,就是我的保姆。我的 母亲和许多别的人都这样称呼她,似乎略带些客气的意思。只有祖母叫她阿长。我平时叫她 “阿妈”,连“长”字也不带;但到憎恶她的时候,——例如知道了谋死我那隐鼠的却是她 的时候,就叫她阿长。
我们那里没有姓长的;她生得黄胖而矮,“长”也不是形容她的形容词。又不是她的名字,记得 她自己说过,她的名字是叫作什么姑娘的。什么姑娘,我现在已经忘却了,总之不是长姑娘;也终于不知道她姓什么。记得她也曾告诉过我这个名称的来历:先前的先前,我家有一 个女工,身材生得很高大,这就是真阿长。后来她回去了,我那什么姑娘才来补她的缺,然 而大家因为叫惯了,没有再改口,于是她从此也就成为长妈妈了。
虽然背地里说人长短不是好事情,但倘使要我说句真心话,我可只得说:我实在不大佩 服她。最讨厌的是常喜欢切切察察,向人们低声絮说些什么事。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 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我的家里一有些小风波,不知怎的我总疑心和这 “切切察察”有些关系。又不许我走动,拔一株草,翻一块石头,就说我顽皮,要告诉我的 母亲去了。一到夏天,睡觉时她又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我没有 余地翻身,久睡在一角的席子上,又已经烤得那么热。推她呢,不动;叫她呢,也不闻。
“长妈妈生得那么胖,一定很怕热罢?晚上的睡相,怕不见得很好罢?……”
母亲听到我多回诉苦之后,曾经这样地问过她。我也知道这意思是要她多给我一些空 席。她不开口。但到夜里,我热得醒来的时候,却仍然看见满床摆着一个“大”字,一条臂 膊还搁在我的颈子上。我想,这实在是无法可想了。
但是她懂得许多规矩;这些规矩,也大概是我所不耐烦的。一年中最高兴的时节,自然 要数除夕了。辞岁之后,从长辈得到压岁钱,红纸包着,放在枕边,只要过一宵,便可以随 意使用。睡在枕上,看着红包,想到明天买来的小鼓、刀枪、泥人、糖菩萨……。然而她进 来,又将一个福橘放在床头了。
“哥儿,你牢牢记住!”她极其郑重地说。“明天是正月初一,清早一睁开眼睛,第一 句话就得对我说:‘阿妈,恭喜恭喜!’记得么?你要记着,这是一年的运气的事情。不许 说别的话!说过之后,还得吃一点福橘。”她又拿起那橘子来在我的眼前摇了两摇,“那 么,一年到头,顺顺流流……。”
梦里也记得元旦的,第二天醒得特别早,一醒,就要坐起来。她却立刻伸出臂膊,一把 将我按住。我惊异地看她时,只见她惶急地看着我。
她又有所要求似的,摇着我的肩。我忽而记得了——
“阿妈,恭喜……”
“恭喜恭喜!大家恭喜!真聪明!恭喜恭喜!”她于是十分欢喜似的,笑将起来,同时将 一点冰冷的东西,塞在我的嘴里。我大吃一惊之后,也就忽而记得,这就是所谓福橘,元旦辟头的磨难,总算已经受完,可以下床玩耍去了。
她教给我的道理还很多,例如说人死了,不该说死掉了,必须说“老掉了”、“谢世了”;死了人,生 了孩子的屋子里,不应该走进去;饭粒落在地上,必须拣起来,最好是吃下去;晒裤子用的 竹竿底下,是万不可钻过去的……。此外,现在大抵忘却了,只有元旦的古怪仪式记得最清 楚。总之:都是些烦琐之至,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非常麻烦的事情。
然而我有一时也对她发生过空前的敬意。她常常对我讲“长毛”。她之所谓“长毛” 者,不但洪秀全军,似乎连后来一切土匪强盗都在内,但除却革命党,因为那时还没有。她 说得长毛非常可怕,他们的话就听不懂。她说先前长毛进城的时候,我家全都逃到海边去 了,只留一个门房和年老的煮饭老妈子看家。后来长毛果然进门来了,那老妈子便叫他们 “大王”,——据说对长毛就应该这样叫,——诉说自己的饥饿。长毛笑道:“那么,这东 西就给你吃了罢!”将一个圆圆的东西掷了过来,还带着一条小辫子,正是那门房的头。煮 饭老妈子从此就骇破了胆,后来一提起,还是立刻面如土色,自己轻轻地拍着胸脯道:“阿 呀,骇死我了,骇死我了……。”
我那时似乎倒并不怕,因为我觉得这些事和我毫不相干的,我不是一个门房。但她大概 也即觉到了,说道:“象你似的小孩子,长毛也要掳的,掳去做小长毛。还有好看的姑娘, 也要掳。”
“那么,你是不要紧的。”我以为她一定最安全了,既不做门房,又不是小孩子,也生 得不好看,况且颈子上还有许多炙疮疤。
“那里的话?!”她严肃地说。“我们就没有用处?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 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 就炸了!”
这实在是出于我意想之外的,不能不惊异。我一向只以为她满肚子是麻烦的礼节罢了, 却不料她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从此对于她就有了特别的敬意,似乎实在深不可测;夜间的 伸开手脚,占领全床,那当然是情有可原的了,倒应该我退让。
这种敬意,虽然也逐渐淡薄起来,但完全消失,大概是在知道她谋害了我的隐鼠之后。 那时就极严重地诘问,而且当面叫她阿长。我想我又不真做小长毛,不去攻城,也不放炮, 更不怕炮炸,我惧惮她什么呢!
但当我哀悼隐鼠,给它复仇的时候,一面又在渴慕着绘图的《山海经》了。这渴慕是从 一个远房的叔祖惹起来的。他是一个胖胖的,和蔼的老人,爱种一点花木,如珠兰、茉莉之 类,还有极其少见的,据说从北边带回去的马缨花。他的太太却正相反,什么也莫名其妙, 曾将晒衣服的竹竿搁在珠兰的枝条上,枝折了,还要愤愤地咒骂道:“死尸!”这老人是个 寂寞者,因为无人可谈,就很爱和孩子们往来,有时简直称我们为“小友”。在我们聚族而 居的宅子里,只有他书多,而且特别。制艺和试帖诗,自然也是有的;但我却只在他的书斋 里,看见过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还有许多名目很生的书籍。我那时最爱看的是 《花镜》,上面有许多图。他说给我听,曾经有过一部绘图的《山海经》,画着人面的兽, 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可惜现在不知 道放在那里了。
很愿意看看这样的图画,但不好意思力逼他去寻找,他是很疏懒的。问别人呢,谁也不 肯真实地回答我。压岁钱还有几百文,买罢,又没有好机会。有书买的大街离我家远得很, 我一年中只能在正月间去玩一趟,那时候,两家书店都紧紧地关着门。
玩的时候倒是没有什么的,但一坐下,我就记得绘图的《山海经》。
大概是太过于念念不忘了,连阿长也来问《山海经》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我向来没有和 她说过的,我知道她并非学者,说了也无益;但既然来问,也就都对她说了。
过了十多天,或者一个月罢,我还记得,是她告假回家以后的四五天,她穿着新的蓝布 衫回来了,一见面,就将一包书递给我,高兴地说道:——“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 我给你买来了!”
我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悚起来;赶紧去接过来,打开纸包,是四本小小的书,略略一翻,人面的兽,九头的蛇,……果然都在内。
又使我发生新的敬意了,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够做成功。她确有伟大的 神力。谋害隐鼠的怨恨,从此完全消灭了。
这四本书,乃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
书的模样,到现在还在眼前。可是从还在眼前的模样来说,却是一部刻印都十分粗拙的 本子。纸张很黄;图象也很坏,甚至于几乎全用直线凑合,连动物的眼睛也都是长方形的。 但那是我最为心爱的宝书,看起来,确是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袋子似的帝江; 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还要“执干戚而舞”的刑天。
此后我就更其搜集绘图的书,于是有了石印的《尔雅音图》和《毛诗品物图考》,又有 了《点石斋丛画》和《诗画舫》。《山海经》也另买了一部石印的,每卷都有图赞,绿色的 画,字是红的,比那木刻的精致得多了。这一部直到前年还在,是缩印的郝懿行疏。木刻的 却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失掉了。
我的保姆,长妈妈即阿长,辞了这人世,大概也有了三十年了罢。我终于不知道她的姓名,她的经历;仅知道有一个过继的儿子,她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孀。
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
绛旓細闃块暱锛1860鈥1899锛夛紝椴佽繀绉板ス涓洪暱濡堝锛屾禉姹熺粛鍏翠笢娴﹀ぇ闂ㄤ汉銆傚ス鏄瞾杩呭効鏃剁殑淇濆銆備腑鏂囧悕闃块暱 鍒 鍚嶉暱濡堝 鍥 绫嶄腑鍥 姘 鏃忔眽鏃 鍑虹敓鍦版禉姹熺粛鍏翠笢娴﹀ぇ闂 閫濅笘鏃ユ湡1899骞 鑱 涓氫繚濮 鐩稿叧浜虹墿椴佽繀 鐩稿叧浣滃搧銆婃湞鑺卞鎷俱
绛旓細1銆侀樋闀匡紝椴佽繀绉板ス涓洪暱濡堝,2銆佷笁鍛充功灞嬶紙鏅氭竻缁嶅叴搴滃煄鍐呰憲鍚嶇濉撅級闃块暱锛屾眽鏃忎汉锛岀敓骞翠笉璇︼紝娴欐睙缁嶅叴涓滄郸澶ч棬婧囦汉銆傛槸椴佽繀鍎挎椂鐨勪繚濮嗭紝椴佽繀绉板ス涓衡滈樋濡堚濓紝浣嗘啂鎭跺ス鏃跺氨鍙滈樋闀库濄備粠闀垮濡堢殑韬笂锛屾垜浠湅鍒颁簡椴佽繀瀵瑰簳灞傚姵鍔ㄤ汉姘戠殑鍚屾儏锛氭瓕棰備粬浠韩涓婄編濂藉杽鑹殑涓闈
绛旓細闃块暱锛屾眽鏃忎汉锛1860骞村嚭鐢熶簬娴欐睙缁嶅叴涓滄郸澶ч棬锛椴佽繀绉板ス涓洪暱濡堝锛屾槸娴欐睙缁嶅叴涓滄郸澶ч棬浜恒傚ス鏄瞾杩呭効鏃剁殑淇濆銆備粠闀垮濡堢殑韬笂锛屾垜浠湅鍒颁簡椴佽繀瀵瑰簳灞傚姵鍔ㄤ汉姘戠殑鎰熸儏锛屼粬鏃㈡彮绀轰粬浠韩涓婃剼鏄ч夯鏈ㄧ殑涓闈紝涔熸瓕棰備粬浠韩涓婄編濂藉杽鑹殑涓闈傞暱濡堝鍦ㄣ婃湞鑺卞鎷俱嬪垎绡囥婇樋闀夸笌灞辨捣缁忋嬩腑鍑虹幇銆傝绡囪杩颁綔鑰呭効鏃朵笌...
绛旓細闀垮濡,涔熷彨鍋氶樋闀,鏄瞾杩呯殑淇濆銆傞瞾杩呭啓浜嗕竴绡囨枃绔犵邯蹇靛ス銆傞暱濡堝,宸茬粡璇磋繃,鏄竴涓竴鍚戝甫棰嗙潃鎴戠殑濂冲伐,璇村緱闃旀皵涓鐐,灏辨槸鎴戠殑淇濆銆傛垜鐨 姣嶄翰鍜岃澶氬埆鐨勪汉閮借繖鏍风О鍛煎ス,浼间箮鐣ュ甫浜涘姘旂殑鎰忔濄傚彧鏈夌姣嶅彨濂归樋闀裤傛垜骞虫椂鍙ス 鈥滈樋濡堚,杩炩滈暱鈥濆瓧涔熶笉甯;浣嗗埌鎲庢伓濂圭殑鏃跺,鈥斺斾緥濡傜煡閬撲簡璋嬫鎴戦偅闅愰紶鐨勫嵈鏄...
绛旓細闀垮濡堟槸椴佽繀瀹朵腑鐨勫コ宸锛屾槸涓撻棬璐熻矗鐓х湅椴佽繀鐨勪繚濮嗭紝瀹朵腑鐨勪汉閮藉敜濂逛负闃块暱鎴栭暱濡堛傚叾瀹炲ス鐨勭湡鍚嶅苟涓嶅彨闃块暱锛屽ス闀垮緱涔熷苟涓嶉珮澶э紝鍙嶈屽張鐭張鑳栥傝嚦浜庝负浠涔堥兘鍙ス涓洪樋闀匡紝鏄洜涓哄師鏉ョ殑淇濆鍙樋闀匡紝鍚庢潵鐪熸鐨勯樋闀跨寮鍚庡洜涓轰範鎯墍鑷村ぇ瀹跺彨鏂版潵鐨勪繚濮嗕篃涓洪樋闀夸簡銆傞暱濡堝铏界劧骞虫椂澶уぇ鍜у挧锛屼絾涔熸湁鏋佸叾蹇冪粏...
绛旓細闀跨殑璇婚煶鏄痗h谩ng銆闀垮濡涓鑸寚闃块暱銆傞樋闀匡紙锛熲1899锛夛紝姹夋棌浜猴紝娴欐睙缁嶅叴涓滄郸澶ч棬婧囦汉銆傛槸椴佽繀鍎挎椂鐨勪繚濮嗭紝椴佽繀绉板ス涓衡滈樋濡堚濓紝浣嗘啂鎭跺ス鏃跺氨鍙滈樋闀库濄備粠闀垮濡堢殑韬笂锛屾垜浠湅鍒颁簡椴佽繀瀵瑰簳灞傚姵鍔ㄤ汉姘戠殑鍚屾儏锛氭瓕棰備粬浠韩涓婄編濂藉杽鑹殑涓闈傞渶鐭ワ細瀵归暱濡堝杩欎釜浜虹墿鐨勬弿鍙欐湰韬潵鐪嬶紝椴佽繀骞朵笉鍥犱负瀵瑰ス鐨...
绛旓細闃块暱鏄椴佽繀鍎挎椂鐨勪繚濮嗐傞暱濡堝鐨勫か瀹跺浣欙紝鏈変竴涓繃缁х殑鍎垮瓙鍙簲涔濓紝鏄仛瑁佺紳鐨勶紝濂规湁涓涓コ鍎匡紝鍚庢潵鎷涜繘浜嗕竴涓コ濠裤傗滈暱濡堝鍙槸璁稿鏃у紡濂充汉涓殑涓涓紝鍋氫簡涓杈堝瓙鐨勮佸瀛愶紙涔′笅鍙仛鈥樺仛濡堝鈥欙級锛屽钩鏃朵篃涓嶅洖瀹跺幓锛岀洿鍒颁复姝汇傗濋暱濡堝鎮f湁缇婄櫕鐤紝1899骞4鏈堚滃垵鍏棩闆ㄤ腑鏀捐垷鑷冲ぇ鏍戞腐鐪嬫垙锛岄缚瀵...
绛旓細闀垮濡鍏朵汉 闀垮濡堬紙?-1899)锛屾禉姹熺粛鍏翠笢娴﹀ぇ闂ㄦ簢浜恒傚ス鏄瞾杩呭効鏃剁殑淇濆銆傞暱濡堝鐨勫か瀹跺浣欙紝鏈変竴涓繃缁х殑鍎垮瓙鍙簲涔濓紝鏄仛瑁佺紳鐨勩傗滈暱濡堝鍙槸璁稿鏃у紡濂充汉涓殑涓涓紝鍋氫簡涓杈堝瓙鐨勮佸瀛愶紙涔′笅鍙綔鈥樺仛濡堝')锛屽钩鏃朵篃涓嶅洖瀹跺幓锛岀洿鍒颁复姝汇傗濋暱濡堝鎮f湁缇婄櫕鐥咃紝1899骞村啘鍘嗗洓鏈堚滃垵鍏棩闆ㄤ腑鏀捐垷...
绛旓細闃块暱(?鈥1899),椴佽繀绉板ス涓洪暱濡堝,娴欐睙缁嶅叴涓滄郸澶ч棬浜恒傚ス鏄瞾杩呭効鏃剁殑淇濆銆傞暱濡堝鐨勫か瀹跺浣,鏈変竴涓繃缁х殑鍎垮瓙鍙簲涔,鏄仛瑁佺紳鐨,濂规湁涓涓コ鍎,鍚庢潵鎷涜繘浜嗕竴涓コ濠裤傗滈暱濡堝鍙槸璁稿鏃у紡濂充汉涓殑涓涓,鍋氫簡涓杈堝瓙鐨勮佸瀛(涔′笅鍙仛鈥樺仛濡堝鈥),骞虫椂涔熶笉鍥炲鍘,鐩村埌涓存銆傗 (涓) 闃块暱鏄瞾杩呯骞寸敓娲讳腑涓...
绛旓細銆婃湞鑺卞鎷俱嬩腑鈥滃ス鐢熺殑榛勮儢鏉ュ父鍠滄鍒囧垏瀵熷療杩樼珫璧风浜屼釜鎵嬫寚鍦ㄧ┖涓笂涓嬫憞鍔,鎴栬呯偣鐫瀵规墜鈥濇槸闃块暱锛屽嚭鑷婃湞鑺卞鎷俱嬩腑鐨勩婇樋闀夸笌灞辨捣缁忋嬨傚師鏂囨槸锛氬ス鐢熷緱榛勮儢鑰岀煯锛岃璇濇椂鍠滄鍒囧垏瀵熷療锛岃繕绔栬捣绗簩涓墜鎸囷紝鍦ㄧ┖涓笂涓嬫憞鍔紝鎴栬呯偣鐫瀵规墜鎴栬嚜宸辩殑榧诲皷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