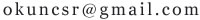当时只道是寻常
已是深秋,雨打芭蕉,残红遍地。京都建平侯府内,冯宜之孤坐窗前,静看满地落红。贴身侍女冬葵自身后走来,给她披上了一件披风。
“冬葵,世子可回府了?”
冬葵为她系披风的手略微一顿,回道:“世子……还未回府。”
冯宜之缓缓阖上好看的双眸,一言不发。冬葵见状,想出言安抚几句,却被冯宜之示意退下。半晌,房中又恢复了一片寂静。
冯宜之听着窗外的雨声,眼底也渐渐潮湿一片。尽管三年未曾回到西疆,但她仍记得每至深秋,西疆的睦边城总会下几场秋雨。但奇怪的是,那边陲之地的雨,却没有京都的雨熬人。
三年前,冯宜之作为镇西将军张广延的外孙女,是西疆最恣意的少女。她自父母亲去世后便在张广延身边长大,无论是兵书策论,还是骑马打仗,她都学。张广延将她当作了张家军的下一任首领来培养。下至三岁孩童,上至八十老妪,西疆无人不知镇西将军府那位生的貌美如花,又性子火热的贵女。
“呵。”
冯宜之睁开了眼,精致艳丽的脸上神色晦暗。
若不是三年前那一眼相视,若不是她动了心,主动救下酒醉落水的赵亭河,西疆最瑰丽的花或许不会如今日一般,被他指着鼻子骂“挟恩求报”,落得个独自凋零的下场。
“世子妃,世子回来了……是……是丞相府的管事亲自送来的。”
冬葵的声音在门外响起,冯宜之冰冷的心本有了一丝雀跃,但在听到“丞相府”三个字时,又倏尔冷了下来。
冯宜之到的时候,侯夫人刚要离去。
“宜之,亭河醉得不省人事,今夜还要劳烦你了。”世子虽待冯宜之冷淡,但侯夫人却给她留了面子。
她点头称是,向侯夫人福身退下。
房中,赵亭河躺在榻上,酒气冲天。他清俊的面容一片绯红,一看定是没少饮酒。
冯宜之有些看愣了。这是多久了呢?她再次看到他安静歇息的模样,而不是对她冷眉竖目,也不是与她唇枪舌剑。这般倒令她生出些许陌生。
她走近,为他脱下鞋靴,再想帮他盖好被子。赵亭河无意识地一动,却从他怀中掉下来一方手帕。
那手帕有兰花暗纹,在其中一角上绣了一个“元”字。冯宜之认得,这是丞相千金李元元的手帕。
在初到京都之时,冯宜之就听过李元元的美名——京都第一才女,丞相的掌上明珠。更重要的是,她是赵亭河的心上人。当年赵亭河师承李丞相,与李元元颇有往来,他还曾赞她“气质美如兰,才华馥比仙”。
他们成婚那日,她也来了。不得不承认,李元元确实是才情高洁,身姿动人。那日她一出现,赵亭河的眼睛就不再留给冯宜之半分温柔。
而今日,自己的丈夫喝得不省人事,怀中还藏着其他女子的贴身之物……他们做了什么,又没做什么呢?
哦,对了,今日似乎是李元元的生辰。侯夫人似是知道自己儿子和李家千金的龃龉,怕冯宜之多想,便未让她操办送礼之事。
思及此,冯宜之的神色已然冷若冰霜。
两日后,京都接到急报,戎狄大举进犯西疆,镇西将军请旨迎战。皇帝一声令下,张广延率领张家军英勇迎战。
冯宜之知晓此事,心中焦急不已。她知道,外祖虽骁勇,但年事已高,而战场上刀枪无眼,难免伤亡。
“世子妃,刘公子命人急送家书一封。”
正是忧虑之际,冯宜之收到了刘皓送来的信。
刘皓是张广延已故部下之子,被收养膝下,自小与冯宜之一起长大。他在信中让冯宜之放心,他已随张广延上战场,西疆有亲信留守,必会大胜归来。
寥寥数字,让冯宜之红了眼眶。
又过了半月。
那日赵亭河深夜才下职,一回府便进了澜亭院,寻冯宜之的身影。
世子前往澜亭院实属难得,但看世子的神色却似在压制怒气。下人们噤若寒蝉,只是面面相觑。
“冯宜之!”
房中,冯宜之半倚在美人榻上看话本。赵亭河一声怒喝,吓得她手中的话本都落在了地上。
赵亭河见美人半倚榻上,雪腮云鬓,娇若芙蓉,她神色还有些吃惊,似是被吓到了。
他只愣了一瞬,又厉声质问:“你和刘皓到底是什么关系?张家军节节败退,密报言军中出了奸细通敌,而那人就是刘皓!”
“……不可能,此事可查证清楚了?”冯宜之心下震惊,面上却不显。
“有何不可能?!陛下正着人调查,还截获了你日前写给刘皓的亲笔信。我不管你与刘皓到底是何关系,但你要记住,既已加入建平侯府,便要记得你已不是张家人!收起你那不该有的心思!”
赵亭河甩袖离去,并命人将冯宜之软禁在府内。
“世子妃……小姐……”
冬葵在门外将二人的争吵听得一清二楚,见自家小姐立在那处无声垂泪,心疼不已。
她是冯宜之的陪嫁丫鬟,冯宜之在西疆有多么恣意,在京都受了多少委屈,她最清楚不过。她还记得小姐待嫁之时的欢欣雀跃,也记得成婚之日,小姐因世子宿在书房而哭泣的模样。
她的小姐可是镇西大将军的掌上明珠,哪知到了京城却被贵女们嘲笑是来自西疆的野蛮人,受了委屈却只换来世子的冷眼和嘲讽。那瞎眼世子不知,她可是心知肚明,若没有李元元在宴会上的挑唆,哪有人敢多次针对小姐。
冬葵不由得哭了出来,冲进去跪在冯宜之身边,握住她冰凉的手:“小姐,刘少爷不会做这种事的,我们回西疆吧……您在京都受了太多委屈了……呜呜呜呜……”
冯宜之身形晃了晃。
她以前还曾担心赵亭河误会她与刘皓的关系,为此特意解释过,只换来一句“我不关心”,如今主动问起二人关系,却是因为可能影响他的仕途。
她终是没说话,只是缓缓握紧了冬葵的手。
翌日,冯宜之在赵亭河书房外侯了许久,希望他能帮忙为张家,为刘皓之事探听一二。
“世子妃,请您回吧,您滴水未进,已在此侯了半日了。”管事于心不忍,再次开口劝诫。
然而冯宜之面色惨白,却仍立在门外。
她心下戚戚,若是当年的自己,定是拼了命也要自请查清实情。而如今,她已成为后院的一只鸟雀,断了翅膀,没了利爪,只能依靠投食者,乞求一点怜悯。
渐渐地,下腹传来一阵阵的绞痛,冯宜之双眼一黑,晕了过去。
醒来时,她已经躺在了榻上,只有冬葵哭肿了眼睛,在一旁守着她。
“……冬葵,世子可还在?扶我起来。”
“小姐,您来了葵水,又一日未进食,晒了许久,可千万别动了!”
“我无碍,世子……”
“小姐!世子他……早就走了。您晕倒不久,有人通报李小姐的车马在街上受惊,因离建平侯府近,特来救助。世子……他就二话不说就去帮忙了……”
冯宜之听罢,便也不再挣扎起身。她空洞地望着床帏。
良久,豆大的眼泪从眼中滚下,打湿了两鬓。
冯宜之又想起了以前。原先,她以为赵亭河只是性子冷淡,为了增进两人的感情,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她为他洗手做羹汤,从来都是拿马鞭的手为他捻起绣花针……可是,换回了什么?
熬了三个时辰的汤被他随意地赐给了小厮,扎破十根手指才做出的腰带被他称为“没事找事”……直到那夜听到侯夫人和他的争吵,冯宜之才知道,他娶她只是因为她救了他,只是因为侯夫人为日渐没落的侯府做的明哲保身之举。
那夜,冯宜之也一样瞪着床帏流了一夜的泪。之后,她不再主动讨好,对侯夫人也保持着疏离,只想着平平安安地过日子,不给外祖添麻烦。
她以为自己的泪流干了,不会再为赵亭河流泪了,哪知今日又重蹈覆辙。
之后,冯宜之大病了一场,一连在榻上缠绵了八九天,不知道外面风云变幻。
侯夫人着人请了大夫,送了良药。而赵亭河却始终没有出现。直到冯宜之可以倚着人坐起来的那天,他出现了。
赵亭河在她床边坐下,从怀中掏出一根金钗,式样并不精致,但用料却十分昂贵。
冯宜之木然地听他说,张家军成功击退戎狄,扬我国威,但张广延身受重伤,索性并无性命之忧。
而刘皓之事已水落石出,乃是丞相之子与贪墨粮草军需,还以通敌之名行诬告之举。刘皓身受重伤,密折上报,这才换回自己的清白,助军营破敌。皇帝震怒,丞相之子择日斩首,丞相府被抄,丞相一家被流放岭南。
赵亭河向她道尽这几日的风波,才将手中的金钗递给她:“这钗,算我向你赔礼道歉,日前心焦,话说得重了。”
冯宜之微愕,赵亭河何曾主动向她道过歉?
唯一的一次,还是他因生气先乘马车回家,将她扔在城郊还不留侍卫,让她和冬葵最后步行回府。那次道歉,还是侯夫人看不过眼,逼他来的。
转念一想,这次应该也是侯夫人让他来的。毕竟……张家和刘皓立了大功,还受了委屈,皇帝应该会重赏。
赵亭河见冯宜之美眸婉转,不知想了些什么,接过金钗放在枕边,一言不发地躺下,背对着他合上了眼。
他本因此举生了些怨气,可看冯宜之弱柳扶风的样子,突然有些恍惚。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她变成了这样。他记得初见的时候,她是明艳飞扬的少女,腰间系着马鞭,说话得理不饶人。而如今,她却像脆弱的瓷器,冷漠又疏离。
他承认,当初他抗拒许久还是娶了她,不单是为了侯府有条后路,不单是因为母亲以死相逼,还因为……少女每次看向他时,眼中毫不修饰的喜爱和钦佩。只是后来,他总在元元和她之间挣扎。
赵亭河总告诫自己,李元元待他是真心的。但他忘了,那个离家千里、义无反顾嫁给他的姑娘,曾经也是真心待他的。
几日之后,皇后听闻冯宜之久病刚愈,赏了她许多珍稀药材。冯宜之便知道,刘皓应该快入京了。
而京都内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往日风光无限的丞相一家要被流放。
但那日,赵亭河半夜才回府,他身后还跟着一名女子。
深夜的建平侯府起了争执,吵醒了早已歇下的冯宜之。她带着冬葵到前厅,看到侯夫人面色不善,看到自己夫君和李元元相依而站的身影。她扯出一抹冷笑,牵痛了心口的裂缝。
“李姑娘深夜来访,不知有何要事?据我所知,今日应是李家流放岭南之期。”
李元元没说话,反而眼中噙泪,低下了头,楚楚动人。
果不其然,赵亭河上前一步,将李元元挡于身前。他盯着冯宜之的眼睛,犹豫半晌,还是说了那句让冯宜之伤心欲绝的话:“宜之,我要纳元元为妾,她不该受此牵连。”
冯宜之没有任何反映。她心道,原来泪流干了就真的不会再流了,自己以前只是被伤得不够狠。
赵亭河看着冯宜之一言不发地走近,以为她要反驳,便又道:“我待元元是真心的。”
他看见冯宜之那张美丽张扬的脸突然露出一抹讥笑,而后又笑得凄凉。他听见她气若游丝的声音再问他:“你可知道,曾几何时,我待你也是真心的?”
赵亭河没想到她说的是这话,木然道:“……若你同意她进门,我也将对你以礼相待。”
“呵。”轻飘飘的笑声却像一个有力的巴掌,扇在了他脸上。
冯宜之看着赵亭河讶异的表情,瞧见李元元拉住男人衣袖的小动作,突然觉得畅快极了。
她盯着李元元那张素白的小脸道:“李姑娘,你好歹也曾是相府千金,也甘心当一个妾?真叫我大开眼界。”
李元元看冯宜之的神色冷了几分,视线像淬了毒的利箭。
“冯宜之,你不要……”赵亭河刚想开口维护,就被冯宜之打断了。
“不要怎么?郎情妾意容不得他人说咸道淡?”冯宜之又是一抹冷笑,朗声道:“我素来钦佩李姑娘才华,当妾实在委屈。赵亭河,我与你合离。”
一言罢,四座震惊。
赵亭河不可置信地睁大了眼睛,李元元也是十分惊异。最先出声反对的倒是侯夫人,扬言不会让李元元进门,不许合离。
冯宜之淡淡地看着眼前的闹剧,只觉得十分疲惫,面色不愉地闭上眼。
冬葵哭红了鼻头,拉着她的手小声道:“小姐,您说的对,合离吧,冬葵带您回西疆,不会再让人欺负您了!”
小丫头恶狠狠地瞪了赵亭河、李元元一眼,搀着冯宜之就要离开。
侯夫人心下一急便上前拉扯,又是一片混乱。
“够了!”赵亭河大吼一声,四下安静下来。
他走到冯宜之面前,僵硬地开口:“我说过,今后会待你好些,不要再闹了。”
冯宜之讪笑。她还未开口,就听见一道悦耳的男声:“让我看看,是谁在教训我们张家的女儿?”
众人转头一看,一位芝兰玉树的公子哥带着两名侍卫阔步流星走来,一旁的侯府管家阻挡不及,一头大汗。
“刘少爷!”冬葵看清来人后欣喜地喊了一声。
而冯宜之从听到声音的那一刻起,就已被泪水模糊了眼睛。
刘皓发现,记忆中的小姑娘在这三年间清瘦了很多,眼睛又红又肿,没有了当初的锐利和张扬。他顿时心痛不已,这可是他舍命也愿护着的姑娘啊……
刘皓径直走到冯宜之的身边,将其护在身后:“世子,好久不见。看来我们宜之嫁与你,过得并不好!”
他在沙场驰骋多年,被刀光剑影磨砺了一身戾气,一扫侯府众人,便威慑十足。
“圣上欲赐我们张家封赏,明日我便要进宫面圣。即便世子不愿合离,我也要向圣上求一封合离书。”
说罢,刘皓牵着冯宜之出了建平侯府,无人敢拦。赵亭河的目光沉沉,李元元的视线却盯着赵亭河忽变的神色不放。
冯宜之看着刘皓高大的背影,感觉胸腔中情绪翻滚难已。
她记得三年前,刘皓得知自己要嫁给赵亭河时的震惊。那时,她才知晓他的心意。三年前他在她的婚宴上喝得酩酊大醉,挥着拳头警告赵亭河要对她好。三年后,他像神袛一般突然出现,把她带离了那个伤心之地。
刘皓将冯宜之带到马车前,见她盯着自己泫然欲泣,心中便软成了一湾潭水。他将她拦腰抱起,带上了马车。直至在车中坐好,两人面面相觑,刘皓才自觉自己行为失礼。
倒是冯宜之看到刘皓绯红的脸颊,先破涕为笑。两人含笑相望,却久久并未开口。
翌日,京都的街头巷尾都在谈论两件事。
其一是,皇上重赏张广延将军及张家军,并封刘皓为左将军。其二是,给建平侯世子与世子妃合离。
这些时日,冯宜之就宿在刘皓暂住的府邸中。刘皓为开解她心结,搜罗了各色吃食、玩意儿,尽数送到她房中。
而建平侯府那边,推脱再三才送来合离书,只退了八抬嫁妆。刘皓便带着冬葵和一众亲兵登门,将冯宜之的嫁妆一件不落地搬了回来。小丫头一回来就叽叽喳喳地与她说,嫁妆搬走时,侯府的库房都空了大半,侯夫人和李元元脸都僵了。
冯宜之笑着饮茶,不做评价。自建平侯去世后,侯府没落,虽赵亭河在官场上有些出息,却不善经营,侯府本就是一个空壳。
冬葵怕她不开心,央着她去逛茶楼。
不料刚从茶楼里离开,便看见赵亭河带着李元元从对面的铺子出来,后面的小厮拿着大包小包的物品。
冬葵气不打一处来,而冯宜之倒是诧异地发现,自己的内心却无甚波动。她瞟了一眼便要上马车。倒是赵亭河又叫住了她。
“宜之,你……过得可还好?”
冯宜之淡淡笑了。以往他总是连名带姓地叫她,只有对她抱有歉意时才亲切地唤她的名字,如今二人再无瓜葛,他倒是变得亲厚起来。
她没有应话,上了马车便离开了。
赵亭河觉得脸上火辣辣地疼,转身看到李元元担忧的神色后,又觉冯宜之不识抬举。
他夜里莫名懑怼,在澜亭院中对月饮了两壶酒。酒意渐浓,他习惯性地唤人上茶水。丫鬟恭敬地递上一杯茶,他喝了一口却吐了。
“这是什么玩意儿?本世子以往酒后喝的都是大红袍!”
丫鬟战战兢兢地跪地求饶,说以往都是世子妃……前世子妃亲手准备的,她不甚知情,这就去换一杯茶来。
赵亭河听了却像泄了气的皮球,又由愤怒变得郁闷起来。
他记得刚娶她进门的时候,为了泄愤,自己常常宿醉晚归。她起初会温着一壶大红袍,留一盏灯守着自己归家。
后来……被半醉半醒的自己呵斥过一次后,便不再灯留守。但一壶温热的大红袍却未曾缺席。他一直以为……这茶是府上的下人备的……
他不知道为什么一个自己不爱的女人走后,生活起居总有不如意的地方。屏退了侍女,赵亭河喝得酩酊大醉。
李元元立在回廊下看了许久。
月底,冯宜之和刘皓启程回西疆。冯宜之实在想不到,在这无人与她交好的京都,来送自己的人竟是李元元。
“我虽不爱赵亭河,但我需要这个机会.以往确实针对过你,可让你离开并非我本意。你信也好,不信也罢,对你,我是钦佩的,也是嫉妒的。”她塞给冯宜之一支金钗便离开了。
是赵亭河拿来道歉的那支钗子。
“小姐,咱们走吧!”不远处的冬葵见李元元走了便唤道。
冯宜之看了那金钗两眼,手一松,转身离开。金钗跌入泥土中,孤零零地送车马远走。
建平侯府。
赵亭河下了职,一脸疲惫地浸在雾气氤氲的热水中。
近来,他办事很不顺利,总是遇到一些鸡毛蒜皮的麻烦,令人心力交瘁。日前,元元还向自己隐晦地提出成婚一事,他不知怎的,竟然鬼使神差地岔开了。
洗完澡,他没回书房。冯宜之走了,他便搬回了澜亭院的正屋,却总感觉那个女人的痕迹挥之不去。昨天他心烦意乱,命人将房间内的装饰物件全换了一遍。奴才们最后却递来一叠冯宜之留下的字帖,问他怎么处理。
赵亭河本想着人烧掉,不知为何,开口却是让人留在了书桌上。一页页翻开,她的字迹笔走游龙,写的是草原戈壁,述的是沙场英雄。不想平日里的她,倒像……倒像初来京都的那个明艳少女。
赵亭河翻了半晌,见一幅未完的画作夹在其中。
画的是持扇郎君和羞涩少女并肩而立,男子是他的模样,而女子的脸却未画完。画上题了一行诗句: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当时只道……是寻常……”
赵亭河愣愣地念出最后一句,突然有无数悔恨涌上心头。
一连两月,他的情绪愈浓烈,在房中能想起冯宜之倚靠在榻上看话本的样子,在院中便记起她侍弄花草的背影……赵亭河第一次觉得,自己可能没有那么讨厌她。
他开始饮酒来麻痹自己,夜夜找李元元下棋对诗,希望自己不要再想起冯宜之。
然而,就算与李元元情到浓时,即将两唇相接,他的脑海里就会突然浮现冯宜之那张决绝悲恸的脸,她说:“你可知道,曾几何时,我待你也是真心的?”
他像被响雷击中,瞬间推开了李元元近在咫尺的脸,逃一样地回了房间,又对着那幅未完的画作出神。
日子一天天过去,李元元在府中无名无份,渐渐引来了下人非议。连侯夫人也看出了自家儿子的不对劲,劝他既然早已合离,就纳了李元元为妾,再娶一门正妻。赵亭河却置若罔闻。
直至那一夜,他又在澜亭院中饮酒。李元元一脸冷意来到他面前,问他是不是爱上了冯宜之,是不是后悔带她回了府。赵亭河一言不发,闷声喝酒。
李元元终于看不下去,一把推倒了酒壶。
“赵亭河,你不要再傻了!当初是你说心悦于我,是你说厌恶冯宜之的!现在作甚在我眼前借酒消愁?!”
“我告诉你,你后悔也无济于事了,她早就死心了。她离京之时,我带去了你送她的金钗,你猜怎么?她扔了!毫不留情地扔了!”
赵亭河直至听到“金钗”二字才有了反映,他踉踉跄跄地回到房间翻箱倒柜,确实找不到那根金钗。直到李元元从身后抱住他,他才愣在原地。
赵亭河转头,却看见了冯宜之的脸。他颤抖着抚上她的脸,终于和她道歉,乞求她不要离开自己。李元元只觉得浑身的血冷得凝在了一处,然而她却吻了上去。不为别的,她只要一个孩子,一个能让她在建平侯府立足的孩子。
开春的时候,建平侯府终于有了喜事——李元元进门,还怀了一个孩子。
然而孩子还未出生,赵亭河却向皇帝自请外放西北。他本是翰林院修撰,得以观政,未来前途无量。而自请外放的京官,能回京是少数。
侯夫人知道后气得当场昏了过去,在病榻上醒来还在骂赵亭河不孝,念自己愧对早逝的建平侯。
而李元元却自始至终很冷静,她替他收拾了行李,打点下人,第二天一早送他离京。直到回到澜亭院的正屋,再也寻不到那幅赵亭河日日对着发愣的画卷,她才歇斯底里地哭出声来。
三年后,北疆阳谷城内。
“太守人真好,解决了问题,还收留了那个无处可归的孩子。”
“是呀是呀,真是我们的父母官啊!”
……
父母双亡的小男孩被太守大人牵回了略显简陋的府邸。
赵亭河将他带到书房,让男孩今后就在身边做自己的书童,先负责书房的洒扫。小男孩眼睛亮了起来,郑重地点了点头。
他好奇地环顾书房,怯生生地指着墙上的一幅画像问:“大人,那幅画可真好看,是您和夫人吗?”
好心的太守却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是摸了摸他的头。
两年后的冬至,匈奴突袭阳谷城。援军迟迟未到,城中粮草所剩无几。
小男孩长大了些,但却从未见过这样的局面。
在太守和士兵苦战十日之后,城门传来了一阵阵的撞击声,匈奴人的狂吼传到了阳谷城中。城中人心惶惶,哀号遍野。憔悴不堪的太守让城中妇孺寻处藏匿,命城中男人举起武器,为家国而战。
男孩在藏身处听见有人高呼:“张家军已到!援军已到!”
他才颤抖地握着铁锹,不顾身边大娘的阻拦,一鼓作气地往城楼的方向冲,希望助太守一臂之力。只见太守腹部插着一支箭,半倚在城楼上,凝视着城楼下的战场。
那是一个高束青丝的美丽女子,身着铠甲,手持长枪,挑落了一个又一个虎背熊腰的匈奴人。血溅红了她的面庞,却不妨碍她出枪的速度。
男孩见太守望着那女子,嘴唇翕动,眼中尽是眷恋和惊异。
待匈奴军败退,张家军大获全胜之际,男孩才认出了那女子——是太守大人画中之人。
那女子正指挥着将士搬运尸体伤员,自她身后走来一名清俊将军。两人靠得很近,将军伸手为女子拨弄了一下凌乱的发丝,两人在夕阳下相视而笑。
男孩望了望那两人,又侧身看了看包扎好伤口正在昏睡的大人,想说点什么,却说不出口。
绛旓細褰撴椂鍙亾鏄甯鐨勫叏璇楀涓嬶細璋佸康瑗块鐙嚜鍑夛紝 钀ц惂榛勫彾闂枏绐楋紝娌夋濆線浜嬬珛娈嬮槼銆傝閰掕帿鎯婃槬鐫¢噸锛岃祵涔︽秷寰楁臣鑼堕锛屽綋鏃跺彧閬撴槸瀵诲父銆傘愪綔鍝佸嚭澶勩戝嚭鑷婃担婧矙路璋佸康瑗块鐙嚜鍑夈嬶紝鏄竻浠h瘝浜虹撼鍏版у痉鐨勮瘝浣溿傝瘝涓劅鎬鍓嶅皹寰浜嬨備笂闃曚互榛勫彾銆佺枏绐椼佹畫闃充箣绉嬫櫙鐨勫嬀鐢伙紝鎻忕粯涓у鍚庣殑瀛ゅ崟鍑勫噳锛涗笅闃曞啓...
绛旓細涓銆佲褰撴椂鍙亾鏄甯鈥濊繖鍙ヨ瘽鎰忔濇槸锛氭様鏃ュ钩甯稿線浜嬶紝宸蹭笉鑳藉鎰夸互鍋裤備簩銆佸師鏂 娴f邯娌 銆愭竻銆戙愮撼鍏版у痉銆戣皝蹇佃タ椋庣嫭鑷噳锛熻惂钀ч粍鍙堕棴鐤忕獥銆傛矇鎬濆線浜嬬珛娈嬮槼銆傝閰掕帿鎯婃槬鐫¢噸锛岃祵涔︽秷寰楁臣鑼堕銆傚綋鏃跺彧閬撴槸瀵诲父銆備笁銆佽瘧鏂 绉嬮鍚瑰喎锛屽鐙殑鎯呮鏈夎皝鎯﹀康锛熺湅鐗囩墖榛勫彾椋炶垶閬帺浜嗙枏绐楋紝浼珛澶曢槼涓嬶紝...
绛旓細璧屼功娑堝緱娉艰尪棣欙紝褰撴椂鍙亾鏄甯銆傚嚭鑷竻浠g撼鍏版у痉鐨勩婃担婧矙路璋佸康瑗块鐙嚜鍑夈嬭皝蹇佃タ椋庣嫭鑷噳锛岃惂钀ч粍鍙堕棴鐤忕獥锛屾矇鎬濆線浜嬬珛娈嬮槼銆傝閰掕帿鎯婃槬鐫¢噸锛岃祵涔︽秷寰楁臣鑼堕锛屽綋鏃跺彧閬撴槸瀵诲父銆傝瘧鏂囷細绉嬮鍚瑰喎锛屽鐙殑鎯呮鏈夎皝鎯﹀康锛熺湅鐗囩墖榛勫彾椋炶垶閬帺浜嗙枏绐楋紝浼珛澶曢槼涓嬶紝寰浜嬭拷蹇嗚尗鑼傞厭鍚庡皬鐫★紝鏄ユ棩濂芥櫙...
绛旓細褰撴椂鍙亾鏄甯鐨勬剰鎬濆涓嬶細涓銆佹剰鎬濓細1銆佸綋鏃惰嚜宸辫寰楁煇浠朵簨鎴栨煇涓汉锛屾垨鑰呮槸鏌愪欢鐗╁搧锛屾病浠涔堝ぇ涓嶄簡鐨勶紝寰堝钩甯革紝寰堜竴鑸紝浣嗘槸鐜板湪鍥炴兂璧锋潵锛屽彧鎭ㄨ嚜宸卞綋鏃惰璇嗗お娴呴檵锛岄敊杩囦簡濂戒笢瑗裤2銆佸綋鏃惰寰楁槸寰堝甯哥殑浜嬶紝鐜板湪鎯宠捣鏉ュ嵈鏄崄鍒嗗疂璐碉紝鍗村啀涔熸壘涓嶅埌浜嗭紝琛ㄨ揪浜嗗骞哥澶卞幓鍚庣殑杩芥倲銆備簩銆佸嚭澶勫強璧忔瀽锛...
绛旓細鍑鸿嚜娓呬唬绾冲叞鎬у痉鐨勩婃担婧矙路璋佸康瑗块鐙嚜鍑夈嬭皝蹇佃タ椋庣嫭鑷噳锛岃惂钀ч粍鍙堕棴鐤忕獥锛屾矇鎬濆線浜嬬珛娈嬮槼銆傝閰掕帿鎯婃槬鐫¢噸锛岃祵涔︽秷寰楁臣鑼堕锛褰撴椂鍙亾鏄甯銆傝瘧鏂囩椋庡惞鍐凤紝瀛ょ嫭鐨勬儏鎬鏈夎皝鎯﹀康锛熺湅鐗囩墖榛勫彾椋炶垶閬帺浜嗙枏绐楋紝浼珛澶曢槼涓嬶紝寰浜嬭拷蹇嗚尗鑼傞厭鍚庡皬鐫★紝鏄ユ棩濂芥櫙姝i暱锛岄椇涓祵璧涳紝琛h婊″甫鑼堕锛屾様鏃...
绛旓細涓銆佲褰撴椂鍙亾鏄甯鈥濊繖鍙ヨ瘽鎰忔濇槸锛氭様鏃ュ钩甯稿線浜嬶紝宸蹭笉鑳藉鎰夸互鍋裤備簩銆佸師鏂 娴f邯娌 銆愭竻銆戙愮撼鍏版у痉銆戣皝蹇佃タ椋庣嫭鑷噳锛熻惂钀ч粍鍙堕棴鐤忕獥銆傛矇鎬濆線浜嬬珛娈嬮槼銆傝閰掕帿鎯婃槬鐫¢噸锛岃祵涔︽秷寰楁臣鑼堕銆傚綋鏃跺彧閬撴槸瀵诲父銆備笁銆佽瘧鏂 绉嬮鍚瑰喎锛屽鐙殑鎯呮鏈夎皝鎯﹀康锛熺湅鐗囩墖榛勫彾椋炶垶閬帺浜嗙枏绐楋紝浼珛澶曢槼涓嬶紝...
绛旓細褰撴椂鍙亾鏄甯銆傛剰鎬濇槸锛氭様鏃ュ钩甯稿線浜嬶紝宸蹭笉鑳藉鎰夸互鍋 鍑鸿嚜銆婃担婧矙路璋佸康瑗块鐙嚜鍑夈嬬撼鍏版у痉 鍘熸枃锛氳皝蹇佃タ椋庣嫭鑷噳锛熻惂钀ч粍鍙堕棴鐤忕獥銆傛矇鎬濆線浜嬬珛娈嬮槼銆傝閰掕帿鎯婃槬鐫¢噸锛岃祵涔︽秷寰楁臣鑼堕銆傚綋鏃跺彧閬撴槸瀵诲父銆傘婃担婧矙路璋佸康瑗块鐙嚜鍑夈嬫槸娓呬唬璇嶄汉绾冲叞鎬у痉鐨勮瘝浣溿傝瘝涓劅鎬鍓嶅皹寰浜嬨備笂闃曚互榛勫彾銆...
绛旓細鈥滄矇鎬濆線浜嬬珛娈嬮槼鈥濇剰鎬濇槸锛氫极绔嬪闃充笅锛屽線浜嬭拷蹇嗚尗鑼傗褰撴椂鍙亾鏄甯鈥濇剰鎬濇槸鏄旀棩骞冲父寰浜嬶紝宸蹭笉鑳藉鎰夸互鍋裤傛担婧矙路璋佸康瑗块鐙嚜鍑 娓呬唬锛氱撼鍏版у痉 璋佸康瑗块鐙嚜鍑夛紝钀ц惂榛勫彾闂枏绐楋紝娌夋濆線浜嬬珛娈嬮槼銆傝閰掕帿鎯婃槬鐫¢噸锛岃祵涔︽秷寰楁臣鑼堕锛屽綋鏃跺彧閬撴槸瀵诲父銆傝瘧鏂 绉嬮鍚瑰喎锛屽鐙殑鎯呮鏈夎皝鎯﹀康锛熺湅...
绛旓細鈥褰撴椂鍙亾鏄甯鈥濈殑鎰忔濇槸锛氭様鏃ュ钩甯稿線浜嬶紝宸蹭笉鑳藉鎰夸互鍋裤傚嚭澶勶細銆婃担婧矙路璋佸康瑗块鐙嚜鍑夈嬫竻路绾冲叞鎬у痉 璋佸康瑗块鐙嚜鍑夛紵钀ц惂榛勫彾闂枏绐椼傛矇鎬濆線浜嬬珛娈嬮槼銆傝閰掕帿鎯婃槬鐫¢噸锛岃祵涔︽秷寰楁臣鑼堕銆傚綋鏃跺彧閬撴槸瀵诲父銆傝瘧鏂囷細绉嬮鍚瑰喎锛屽鐙殑鎯呮鏈夎皝鎯﹀康锛熺湅鐗囩墖榛勫彾椋炶垶閬帺浜嗙枏绐楋紝浼珛澶曢槼涓嬶紝寰浜...
绛旓細鈥滄矇鎬濆線浜嬬珛娈嬮槼鈥濇剰鎬濇槸锛氫极绔嬪闃充笅锛屽線浜嬭拷蹇嗚尗鑼傗褰撴椂鍙亾鏄甯鈥濇剰鎬濇槸鏄旀棩骞冲父寰浜嬶紝宸蹭笉鑳藉鎰夸互鍋裤傛担婧矙路璋佸康瑗块鐙嚜鍑 娓呬唬锛氱撼鍏版у痉 璋佸康瑗块鐙嚜鍑夛紝钀ц惂榛勫彾闂枏绐楋紝娌夋濆線浜嬬珛娈嬮槼銆傝閰掕帿鎯婃槬鐫¢噸锛岃祵涔︽秷寰楁臣鑼堕锛屽綋鏃跺彧閬撴槸瀵诲父銆傝瘧鏂 绉嬮鍚瑰喎锛屽鐙殑鎯呮鏈夎皝鎯﹀康锛熺湅...